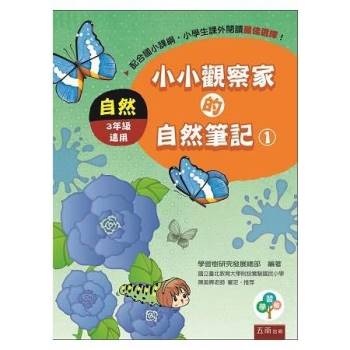故事主要描寫一個年輕的已婚女性康妮,她上層階級的丈夫克利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傷癱瘓而導致終身陽痿。性生活無法滿足的挫折使她開始邂逅一名獵場看守人梅樂士。在故事的最後兩人開始同居,並各自向他們原先的配偶提出離婚訴訟,以求兩人能合法的生活在一起。
這個故事中描述查泰萊夫人和她情人間的肉體關係,其中露骨的性愛描寫、和在當時屬禁忌的猥褻用詞引來許多評論家的非議,或許也是因為此書描寫的主角是勞動階級男性與資產階級女性間的關係。
本書是西方現代心理小說開創者之一。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對人性的摧殘和扭曲,對當時英國的病態社會與病態心理作了細緻的刻畫,並用佛洛伊德的觀點描寫男女情愛,在世界文壇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在勞倫斯的作品中,《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應是最受爭議的作品了!
本書出版的幾年間,一直居於色情與文學的熱門討論話題!
今天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來審視「她」,色情意味已蕩然無存!而這部作品在六十年後的現今,所迸射出來的光芒並未遜色,相反地,在歷經歲月的千錘百鍊下,更形閃耀著無與倫比的魅力……
女人對愛情、對情慾的看法,並非男人或第三者能理解的,與其說作者在本書中所要表達的是一個嫁給殘廢丈夫的妻子的靈慾掙扎,不如說是他想藉由康妮這個女子,來表達對整個人類社會之病態的一種控訴!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世界古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英美文學 |
$ 270 |
世界古典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歐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