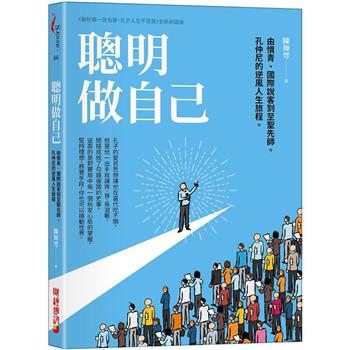雨夜聽鬼,彼岸花開;
心生哀憐,子不語,應是有愛。
心生哀憐,子不語,應是有愛。
聊齋風格之鬼系抒情,血玫瑰讓我們發現世間女子的愛瞋癡狂!
愛情,如此誘人,也如此折磨!
鬼,為死為殺。亡命,為愁為恨。
在奪命背後,訴諸著綿絕的癡傻愛戀。
輪迴轉生,再見他一面,了卻萬劫孽緣。
鬼魅自述淒然情愛成《聽鬼》,血色浸染癡心,腥味包覆執念。
沾滿血腥的雙手,捧著一顆殘破支離的眷愛真心。
千載傳世的鬼魅故事,在血玫瑰筆下,透著愛恨嗔癡的醇厚陳香。
情動了,寧降凡塵,以肉身證明愛情。
情滅了,一縷幽魂卻是不捨。
因愛而生,為愛入死。
七情六慾熬成了孟婆湯。一滴女兒淚,卻是難忘。
……我不想忘,哪怕得粉身碎骨,哪怕過往已殘缺不堪,我仍不想忘……
雨夜,荒煙漫草間的碧玉堂,帶著繡有「子皿」二字手絹的女孩;
陰曹地府、枉死城、黃泉路、彼岸花、三生石、孟婆亭、忘川、六道輪迴──隱約中,她發現自己再不如原先所想是個局外旁觀者,每個故事都觸動著她的心弦,好像曾經參與其中……
一步一徘徊,一念一凝眉,數滴相思淚,半碗忘情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