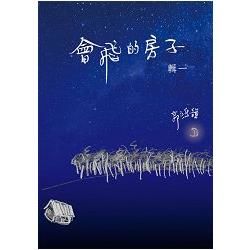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會飛的房子( 輯一 )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32 |
中文現代文學 |
$ 357 |
小說/文學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現代散文 |
$ 378 |
現代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會飛的房子( 輯一 )
內容簡介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生命產生了質變,我勤於讀書、寫作,我把寫作視為編織夢想,我織的夢可能穿梭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生命,也可能幽深曲折,尋不著門,也沒有路徑可循。我每織好一個夢,便把他撒在雲端,我願它化為和風、小雨、細雪、雷電,或化為野花、溪流、蟲鳴、鳥音,或化為一杯濃香的咖啡,或化為哲人的囈語,或化為夜深時照臨大地的月光,或崩裂為宇宙中的微塵……。
序
序一
在茫茫人海中,我總是在尋找人。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練就了一套本領,我可以穿透人的表層,直接看到藏在內裡的靈魂─
有的靈魂很冷,冷得讓我顫慄;
有的靈魂很熱,它總有辦法把週遭的一切都化為灰燼;
有的靈魂很薄,比一張白紙還薄;
有的靈魂很利,它喜歡東咬西啄,毫不留情;
有的靈魂很細很小,幾乎發覺不到它的存在;
有的靈魂乾扁縐縮,像一塊老於世故的菜瓜布;
…………………………
都不是我要尋找的靈魂。
直到有一天,我因跌斷了手而坐困家中,天氣極冷且苦雨不止,為排遣愁緒,我寫了一篇短文「苦雨」─
「……粗茶一杯,淵明餅舖水蒸蛋糕一塊,揮筆臨寫一通寒食帖,惜無僮僕備集文房,只能品讀。遙想千古風流蘇東坡如何在窮促中愈為奮進─」
此文貼上臉書不久,一位時空旅人從雲端翩然而至,與我如是唱和著─
「煮了咖啡一杯,配上Godiva黑巧克力一塊,遙想和鴻韻在台一嚐酒釀湯圓,也不亦樂乎!」
「咖啡加糖否?〈說明:我慣常加糖,我喜歡苦中作樂。〉」
「加糖否?今天沒加,若無巧克力,就加一點糖苦中作樂,我也喜苦中作樂,或樂中有一點傷感,我還無百分之百快樂的經驗。」
「是啊,若無苦,就不知樂之為樂了。〈若為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苦,則另當別論了。〉我與你同感,快樂時總有揮之不去的悲傷,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嗎?」
「呵呵呵……不嚴重,不嚴重,是melancholy的本質。」
我們,像是在暗夜中相遇的親人,半是悲傷,半是欣喜,傾談著生命中的苦與樂。
十天之後,我又在臉書貼上一張照片─〝鷺鷥高踞樹梢、憑空遠眺〞,並為之題記─
牠獨立於蒼茫之巔,
遠眺著朝陽的昇起─
稍一思考,又不免多事地加上了第三行─"Zarathustra?"。
那個附加的問號,意思是:
「誰會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呢?」
我悲傷地想,悲傷得幾近於絕望,在絕望中我睡著了。
一小時之後醒來,發現時空旅人留下了一則訊息─
〝The higher we soar the smaller we appear to those who can not fly.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讀著這則訊息,我好似被一道強烈的電流擊中了,一陣頭暈目眩,我得用手扶著桌子才能穩住自己。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生命產生了質變,我勤於讀書、寫作,我把寫作視為編織夢想,我織的夢可能穿梭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生命,也可能幽深曲折,尋不著門,也沒有路徑可循。我每織好一個夢,便把它撒在雲端,我願它化為和風、小雨、細雪、雷電,或化為野花、溪流、蟲鳴、鳥音,或化為一杯濃香的咖啡,或化為哲人的囈語,或化為夜深時照臨大地的月光,或崩裂為宇宙中的微塵……。
我把這一年半中所編織的158個夢,收攏在這本書裡。
這本書要獻給Claire─雲端上的時空旅人。
Claire,是我的大學同窗,大學時代的我是一個書呆子,一個實足的笨蛋,哪裡知道靈魂的事?所以在那個時空中,我們錯失了彼此。直到三十八年之後,在歷經了人生的滄桑之後,我們在另一個時空重新相遇了,驚覺兩個靈魂竟是如此的熟識而且契合,因此─
這本書開始於〝苦雨〞,以紀念兩個靈魂的重逢;
這本書結束於〝會飛的房子〞─
因為靈魂一直想要飛,現在終於飛了起來!
而我們的旅程才要開始─
序二
鴻韻與我雖是舊識,但在大學同窗、同宿舍的四年中,僅有偶然的四目相視,未曾作過深度的交談;大學畢業後,各自走入滾滾世塵,消失在茫茫人海,直到三十八年之後,才藉由網路之便捷,重逢在雲端。
在一年半的雲端交流中,我驚訝於其人靈魂之多重,誠如在本書〈一棵樹的靈魂〉中所揭示的,有時如一位歷經風霜的老人,有著一份洞察世事的寧靜,有時又像青少年,鼓動著一顆追求理想的熾熱的心,而更多的時候是以孩童般好奇且浪漫的眼光,去打量這個世界。
鴻韻眼中的世界,既不同於一般人眼中紛繁的塵世,亦完全摒去了綑綁一般人的世俗價值,其精靈般的妙筆,往往把生活與生命中的感悟,一一點化為極簡、凝鍊且具神祕氣息的散文,或是清新而朦朧的詩,有些則若哲人的冥想。
其行文,既築基於東方古典文哲的深厚底蘊,又能自在穿梭於西方文學、藝術與審美的趣味。不過,我也發現了鴻韻的〝善變〞,在〈別了,查拉圖斯特拉〉一文中,鴻韻宣稱要作別尼采─〝因我的靈魂是東方式的,我要與陶潛約至田園。〞但沒過多久,又再度被尼采所吸引。
雖然善變,但變中仍有那永遠不變的。
在〈與撒旦的交易〉中,如此寫道:〝我把靈魂扣押給祂,而我得到一對翅膀。〞既不同於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亦不同於林布蘭特畫中的浮士德,鴻韻與撒旦交易的,是一對自由遨翔於宇宙的翅翼。
我想:這是我的朋友永恆不變的追求吧!
鴻韻的手指上,似戴著一只〝所羅門王的指環〞,所以能與萬物同情,與花草樹木昆蟲鳥雀對談無礙,如〈老羅家與老陳家〉中的鵝、〈海邊之歌〉中的狗,至於在〈問小灰蝶〉中的蝶,令我低迴惆悵,竟入了我的夢境,也令我想起了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èry,1900-1944〉書中的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與狐狸。
郭式的機智與幽默也展現在〈怎一個〝妙〞字了得?〉一文中,從黃山谷、千利休、日蓮上人所書之「妙」字,歸結為空間之美、時間之美與境界之美,但文末突地跳躍到一隻貓─
"This is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養隻貓吧,牠會妙~妙~妙地唱著〞
其語境一轉一折,如此妙筆令我驚喜莞爾。
在〈細雪〉一文裡,我看見的是冷凝與熱情並肩之美─
周先生手持一塊乳酪,一把刨刀,於是片片雪花自天際輕柔地飄落─這時,我還是想起了谷崎潤一郎的《細雪》,多麼美,連哀愁也變得輕盈了,它無聲地融化在意大利式的熱情裡。
在〈會飛的房子〉一文裡,漫無邊際的想像力,讓房子飛了起來─
但是,小房子待在地面太久了,它長出了根。小房子的根緊緊地抓住它,不讓小房子飛走。「快啊!快啊!想想辦法吧!」西風催促著。小房子很聰明,它抓了一根曬衣服的竹竿。朝向地面用力一撐,「卡」的一聲,根斷了!
簡而凝鍊的文字,或只有三言兩語,往往令我翩翩起舞,或有時神傷,或瞬間滿溢感動;至於曲折幽深的長文,也令我不自覺地走入寧謐的月光森林,或牽引著我飛行在漫天白雪中……。
其詩、其文,如教堂鐘聲響起,餘韻悠長。
現在,鐘聲響了,吾不復多言─
---------張書勤
在茫茫人海中,我總是在尋找人。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練就了一套本領,我可以穿透人的表層,直接看到藏在內裡的靈魂─
有的靈魂很冷,冷得讓我顫慄;
有的靈魂很熱,它總有辦法把週遭的一切都化為灰燼;
有的靈魂很薄,比一張白紙還薄;
有的靈魂很利,它喜歡東咬西啄,毫不留情;
有的靈魂很細很小,幾乎發覺不到它的存在;
有的靈魂乾扁縐縮,像一塊老於世故的菜瓜布;
…………………………
都不是我要尋找的靈魂。
直到有一天,我因跌斷了手而坐困家中,天氣極冷且苦雨不止,為排遣愁緒,我寫了一篇短文「苦雨」─
「……粗茶一杯,淵明餅舖水蒸蛋糕一塊,揮筆臨寫一通寒食帖,惜無僮僕備集文房,只能品讀。遙想千古風流蘇東坡如何在窮促中愈為奮進─」
此文貼上臉書不久,一位時空旅人從雲端翩然而至,與我如是唱和著─
「煮了咖啡一杯,配上Godiva黑巧克力一塊,遙想和鴻韻在台一嚐酒釀湯圓,也不亦樂乎!」
「咖啡加糖否?〈說明:我慣常加糖,我喜歡苦中作樂。〉」
「加糖否?今天沒加,若無巧克力,就加一點糖苦中作樂,我也喜苦中作樂,或樂中有一點傷感,我還無百分之百快樂的經驗。」
「是啊,若無苦,就不知樂之為樂了。〈若為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苦,則另當別論了。〉我與你同感,快樂時總有揮之不去的悲傷,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嗎?」
「呵呵呵……不嚴重,不嚴重,是melancholy的本質。」
我們,像是在暗夜中相遇的親人,半是悲傷,半是欣喜,傾談著生命中的苦與樂。
十天之後,我又在臉書貼上一張照片─〝鷺鷥高踞樹梢、憑空遠眺〞,並為之題記─
牠獨立於蒼茫之巔,
遠眺著朝陽的昇起─
稍一思考,又不免多事地加上了第三行─"Zarathustra?"。
那個附加的問號,意思是:
「誰會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呢?」
我悲傷地想,悲傷得幾近於絕望,在絕望中我睡著了。
一小時之後醒來,發現時空旅人留下了一則訊息─
〝The higher we soar the smaller we appear to those who can not fly.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讀著這則訊息,我好似被一道強烈的電流擊中了,一陣頭暈目眩,我得用手扶著桌子才能穩住自己。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生命產生了質變,我勤於讀書、寫作,我把寫作視為編織夢想,我織的夢可能穿梭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生命,也可能幽深曲折,尋不著門,也沒有路徑可循。我每織好一個夢,便把它撒在雲端,我願它化為和風、小雨、細雪、雷電,或化為野花、溪流、蟲鳴、鳥音,或化為一杯濃香的咖啡,或化為哲人的囈語,或化為夜深時照臨大地的月光,或崩裂為宇宙中的微塵……。
我把這一年半中所編織的158個夢,收攏在這本書裡。
這本書要獻給Claire─雲端上的時空旅人。
Claire,是我的大學同窗,大學時代的我是一個書呆子,一個實足的笨蛋,哪裡知道靈魂的事?所以在那個時空中,我們錯失了彼此。直到三十八年之後,在歷經了人生的滄桑之後,我們在另一個時空重新相遇了,驚覺兩個靈魂竟是如此的熟識而且契合,因此─
這本書開始於〝苦雨〞,以紀念兩個靈魂的重逢;
這本書結束於〝會飛的房子〞─
因為靈魂一直想要飛,現在終於飛了起來!
而我們的旅程才要開始─
----------郭鴻韻
序二
鴻韻與我雖是舊識,但在大學同窗、同宿舍的四年中,僅有偶然的四目相視,未曾作過深度的交談;大學畢業後,各自走入滾滾世塵,消失在茫茫人海,直到三十八年之後,才藉由網路之便捷,重逢在雲端。
在一年半的雲端交流中,我驚訝於其人靈魂之多重,誠如在本書〈一棵樹的靈魂〉中所揭示的,有時如一位歷經風霜的老人,有著一份洞察世事的寧靜,有時又像青少年,鼓動著一顆追求理想的熾熱的心,而更多的時候是以孩童般好奇且浪漫的眼光,去打量這個世界。
鴻韻眼中的世界,既不同於一般人眼中紛繁的塵世,亦完全摒去了綑綁一般人的世俗價值,其精靈般的妙筆,往往把生活與生命中的感悟,一一點化為極簡、凝鍊且具神祕氣息的散文,或是清新而朦朧的詩,有些則若哲人的冥想。
其行文,既築基於東方古典文哲的深厚底蘊,又能自在穿梭於西方文學、藝術與審美的趣味。不過,我也發現了鴻韻的〝善變〞,在〈別了,查拉圖斯特拉〉一文中,鴻韻宣稱要作別尼采─〝因我的靈魂是東方式的,我要與陶潛約至田園。〞但沒過多久,又再度被尼采所吸引。
雖然善變,但變中仍有那永遠不變的。
在〈與撒旦的交易〉中,如此寫道:〝我把靈魂扣押給祂,而我得到一對翅膀。〞既不同於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亦不同於林布蘭特畫中的浮士德,鴻韻與撒旦交易的,是一對自由遨翔於宇宙的翅翼。
我想:這是我的朋友永恆不變的追求吧!
鴻韻的手指上,似戴著一只〝所羅門王的指環〞,所以能與萬物同情,與花草樹木昆蟲鳥雀對談無礙,如〈老羅家與老陳家〉中的鵝、〈海邊之歌〉中的狗,至於在〈問小灰蝶〉中的蝶,令我低迴惆悵,竟入了我的夢境,也令我想起了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èry,1900-1944〉書中的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與狐狸。
郭式的機智與幽默也展現在〈怎一個〝妙〞字了得?〉一文中,從黃山谷、千利休、日蓮上人所書之「妙」字,歸結為空間之美、時間之美與境界之美,但文末突地跳躍到一隻貓─
"This is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養隻貓吧,牠會妙~妙~妙地唱著〞
其語境一轉一折,如此妙筆令我驚喜莞爾。
在〈細雪〉一文裡,我看見的是冷凝與熱情並肩之美─
周先生手持一塊乳酪,一把刨刀,於是片片雪花自天際輕柔地飄落─這時,我還是想起了谷崎潤一郎的《細雪》,多麼美,連哀愁也變得輕盈了,它無聲地融化在意大利式的熱情裡。
在〈會飛的房子〉一文裡,漫無邊際的想像力,讓房子飛了起來─
但是,小房子待在地面太久了,它長出了根。小房子的根緊緊地抓住它,不讓小房子飛走。「快啊!快啊!想想辦法吧!」西風催促著。小房子很聰明,它抓了一根曬衣服的竹竿。朝向地面用力一撐,「卡」的一聲,根斷了!
簡而凝鍊的文字,或只有三言兩語,往往令我翩翩起舞,或有時神傷,或瞬間滿溢感動;至於曲折幽深的長文,也令我不自覺地走入寧謐的月光森林,或牽引著我飛行在漫天白雪中……。
其詩、其文,如教堂鐘聲響起,餘韻悠長。
現在,鐘聲響了,吾不復多言─
---------張書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