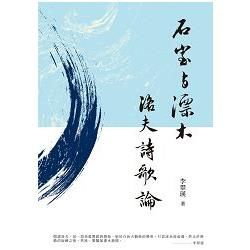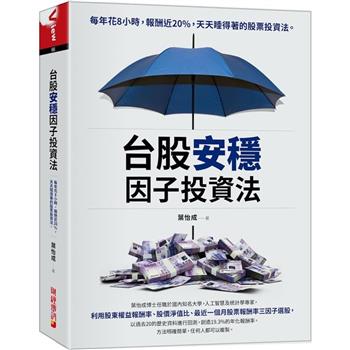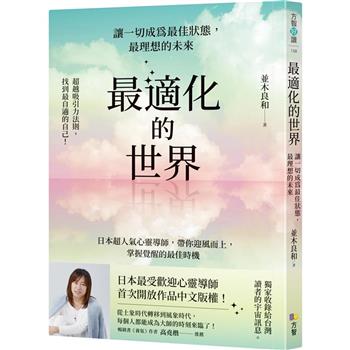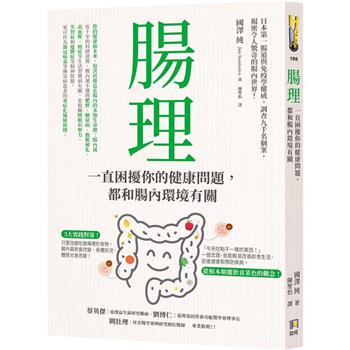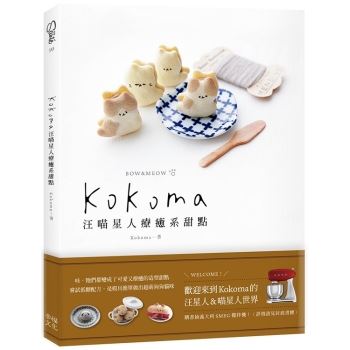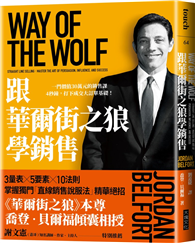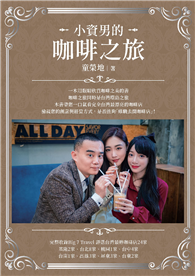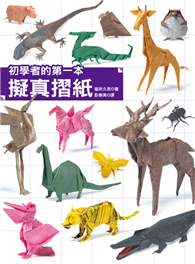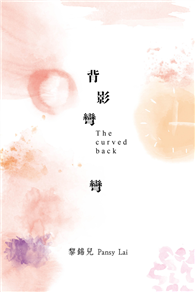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石室與漂木──洛夫詩歌論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現代詩 |
$ 315 |
文學 |
$ 42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石室與漂木──洛夫詩歌論
洛夫──超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近乎魔幻,從石室到漂木,長詩的形式形成一種自我呼應,一是年少的超現實主義,詩壇中無人媲美並駕的「詩魔」。
本書從洛夫創作分期、詩觀與語言的融合切入,探討石室之死亡與漂木長詩的縱軸,比較與其生命哲學;剖析詩中雪意象、詩歌意象的轉換、禪詩的表現形式等細部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