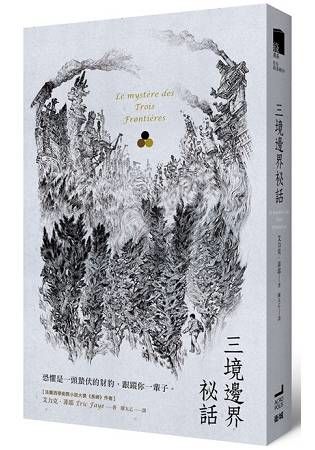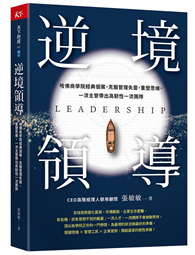序
在奈米科技和地球村的時代,古代神話還能告訴我們些什麼?九○年代,我以阿特雷斯家族(les Atrides) [注1],巴別塔,亞特蘭提斯或德國傳說為中心構思故事,短篇或比短篇長一點的小說;寫筆記時,我念茲在茲的就是這件事。
在歐洲,幾乎到處顯露神話的蹤跡;而歐洲這個名字本身就來自一位進入了希臘神廟的腓尼基公主。無論科技如何日新月異,社會如何轉變,各國神話已開枝散葉,綿延至今。神話中確有令人不安之處,因為,多多少少,它們都正視了所有問題。它們是人類恆常持久的心靈,甚至,是一部「占卜書」,可透視我們的現在並預感未來。我們何必跟樂趣過不去:神話可當作很棒的解讀工具,作家經常喜歡搶來套用。
不過,該從哪方面著手,且無限次數一再運用?在書寫《三境邊界祕話》那段時期,我曾經用天文望遠鏡瞄準那些以古代神明命名的星球,如土星 (Saturne,農神),還有木星(Jupiter,朱比特)——它的衛星個個都有一個神話故事的名稱,在此僅舉幾個為例:歐羅巴(Europe),依歐(Io),和卡里斯托(Callisto)……這些星系的元素透過引力「膠性」(glu)互相連結,在我看來,這個特性也可以轉移到文學上。我於是有了個想法:在同一本集子裡,混合互相有關聯,長短不一的故事,讓每一篇互相感染某種神祕的東西——或許就是企業經營者自以為發創的「綜效」(synergie)。在寫《祕話》的前一年,在我的第一本小說集《我是守燈塔的人》(Je suis le gardien du phare)裡,我已經採取過同樣的手法……一篇主要的故事衍伸出十幾個小衛星,討論同一個題材。後來,我把這種設定模式繼續運用在《化石光》(Les Lumières fossiles),這本小說集的主題是消失。最近一點的小說,探討自我追尋以及「遙不可及的星星」的《化為不朽,然後死去》(Devenir immortel, et puis mourir)也採用了這個模式。
《三境邊界祕話》明顯地再度採用同樣的結構,除了將主要的篇章套上小說的型態,固然很短,但仍是小說;且附帶八則短篇小說載入它周圍的軌道。從第一頁起,即見一個男人為憂鬱所苦,逃離他的城市,去到位於一座遼闊森林邊緣的民宿尋求休憩。他後來愛上去森林裡散步。最初,在林間小徑上,他以為找回了寧靜。然而,這座森林裡(想像出的地理位置)其實上演著許多不正常的事件。男人展開調查,拼命地走,在森林裡繞「圈子」,在雪地上處處留下蹤跡,以致精疲力盡,茫然迷失,直到結尾最終的出路。
奇幻色彩照亮了這部小說,有些人因而視森林為敘事者大腦之變形投射,敘事者極力瞭解,試圖藉此治癒自己的不安與恐懼。所以故事中安排那些健行,極為辛苦累人,卻也能提振精神;而陰暗的區域和那座森林之謎,其實正是藏在自我追尋之路上的處處驚奇,邊界則是區隔已知與未知,理智與瘋狂,甚或生命與死亡的界線。最靠近民宿那座小城名叫尼芙海姆(Niflheim);這個名字源自北歐神話,指的是冰冷的亡魂國度。
這是一種可能的解讀。在此之外,我始終看見森林在某些人生時刻對我們的呼喚。我們或認真回應,或裝聾作啞,但怎可能捕捉不到那一聲聲召喚?我在利穆贊(Limousin)森林附近長大,我人生最初的幾年在一個叫森林新堡〔Châteauneuf-la-Forêt〕的小鎮度過)。那塊區域從最初就出現在我的創作中,從比《三境邊界祕話》早三年的小說《孤獨將軍》(Le Général Solitude)開始。在這部小說裡,叢林上方的神祕之火與三境邊界的森林一樣來自於想像。《祕話》中有一個人物闡述著一個觀念:當森林不斷擴張,傳說與人類的幻想也同樣不斷增長。相反的,若森林退縮,推進的則是文明與「理性」。後來,在短篇小說《Kompétitivnoié》裡,我讓森林擔任避難所的角色,任那些摒棄城市現有體制,組織反抗行動的人使用 (同樣的,在《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那些把世界文學所有指標性作品背得滾瓜爛熟的「書人」也藏身於森林深處)。在形式方面,我當時希望把《三境邊界祕話》寫成一部「開放性」的小說,謎樣的結局或許意味著人不可能認識「自己」,抵達「自己」的極限 (或克服自己的恐懼,因為,在我的想法裡,這是一部關於恐懼的小說),而這樣的結局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詮釋空間。
至於搭配主題小說的短篇則有一個共同點:重新檢視某些神話的某些面向。不過每一篇的語氣不同:輕挑可笑的 (〈宙斯家的晚餐〉),悲劇的(〈一個動作〉),荒謬的(〈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浪漫的(亞特蘭提斯〉),或形而上學的(〈廢除原罪〉)。因為,回到序言最初所闡述的觀念,我覺得,神話反映了生活的每一面,以至於,從神話中,我們可以看見人類的「黑盒子」。
最後再提一點:與這本小說集同名篇章裡的地理想像是漫長健行得出的成果。我不分冬夏,一年四季,在德國的森林裡散策健行,特別是位於一座古老山脈的山脊,從畢勒菲爾德(Bielefeld)延伸到帕德伯恩(Paderborn)之間的條頓堡森林(Teutoburg)。在這些樹林裡,有時,人們或許會以為聽見一段帕西菲爾(Parsifal)或唐懷瑟(Tannhäuser)[注2] 的旋律從山毛櫸林間傳來。我在此度過了許許多多快樂的日子。當時,我只是把這片森林加以延伸,布置得陰沉黑暗,淨空道路,除去稀少的人煙,然後整座遷移到他方——一個可以想像成位於冷戰時期的東德、西德與捷克交界之他方——,就得出了遼闊的三境邊界。接下來,只要完成書寫就行了。
艾力克.菲耶於二○一一年十月
注1阿特雷斯(Atrides)是邁錫尼國王,阿特雷斯的父親是波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比薩國王,阿特雷斯與其孿生兄弟因殺害同父異母兄弟而被驅逐,兩人跑到邁錫尼尋求庇護,阿特雷斯後取代成為邁錫尼國王,其兒子就是後來特洛伊戰爭中有名的阿格曼儂國王。這個家族的神話充滿著家族悲劇,不是爸爸殺小孩,就是妻子殺丈夫,或兒子殺媽媽,是一個被詛咒的家族。
注2兩者皆為華格納的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