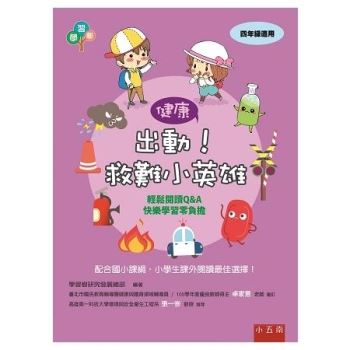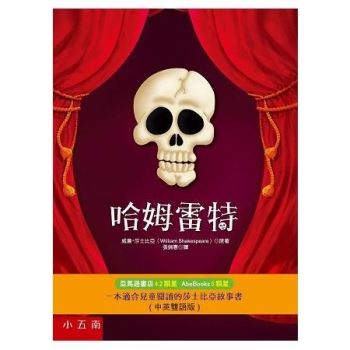圖書名稱:面向新世界
林碧炤老師是國內國際關係的權威,不只在學術上影響重大,更深入參與國家在外交事務和政策上的訂定。作育英才無數,學術界和政界的人脈豐富。
本書廣獲各校國際關係科系、外交系老師選用,作為學生指定用書或參考書。
國際關係學科的成立於2015年已屆滿一百年。
面對全球化與資訊化的衝擊,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研究需要宏觀的新視野與新方法,來因應不斷滋生的新問題。
本書從「復古與創新」的途徑著手,重點有三:
1.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討東西文明的哲學思維,作為了解當前國際問題源起的基礎;
2.援引自然科學、企業管理和公共行政等學理,以跨領域的視野,解析當前多層次國際問題的因應之道。
3.作者從東亞歷史的角度重新定義國際關係的概念與意涵,重建外交史的新史觀,不只為長期偏重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研究指引新的方向,也為關注國際關係發展的讀者提供新的思考架構。
作者簡介
林碧炤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英國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曾任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政大副校長,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總統府副秘書長等職。
現任總統府秘書長、政大外交系兼任教授。
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兩岸政策。
著有《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等學術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