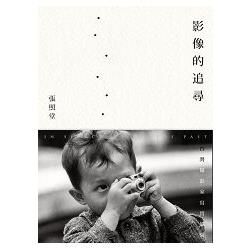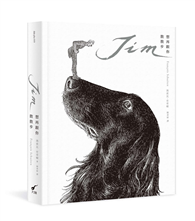再版序
《影像的追尋》這套書自一九八八年出版後,在市面上銷聲匿跡已久,其後雖多次再版,但至今須以高價才能在二手書店或購書網站上罕見地標購取得。
這套介紹四○到六○年代本土紀實攝影家的書,二十七年前在臺灣能夠出版,算一個異數。一九八七年國民政府剛宣布解嚴,施政上仍以政治擴權與經濟建設掛帥,對教育、文化不甚重視。當時臺灣主體意識還沒那麼強烈,本土精神剛萌芽,但談及攝影的專欄與書籍寥寥可數,更別談前輩攝影家的專輯了。為了梳理臺灣攝影的脈絡和資深攝影家的時代足跡,我開始四處訪談、撰寫,系列性的在《光華》雜誌上發表。三年之間,這些滿載庶民生活、勞動、信仰的面容與身影能在政府刊物上大幅連載刊登,在當時也算一個突破和起步。過去,如果這些照片曾經帶給我們「鄉愁」與「懷舊」的慰藉和抒解,今天的再現應不僅於此,更該是一種「理解」與「認同」的召喚和肯定,這些照片,讓我們認同我們是甚麼人,理解我們怎麼走過來的。
《影像的追尋》在撰寫期間,由於資訊匱乏、時機閃失或時間、篇幅的限制,只涵蓋了三十三位資深寫實攝影家。許多重要前輩如林草、彭瑞麟、吳金淼、李火增、李鳴鵰、楊基炘、黃金樹、張新傳、李秀雲、邱德雲等人當時未被納入,是本書一大缺憾。但隨著憶舊與尋根的時代潮流,這些攝影家也陸續曝光、展覽並出書,他們的優異作品見證了台灣民間坎坷、豐沛的奮鬥史與生命力,從而彌補了臺灣攝影史料長久以來的隙縫與斷落。從一張張照片中,我們得以開始拼貼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va Rubinstein曾說:「拍一張照片就像在世界上某處找回一部分自己。」藉由這些歷久彌新的記憶回返,我們每個人也分別找回某些自己。
記得有一次訪談前輩攝影家張才,問起他的拍照哲學,他說:「沒什麼,把它拍下來再說。」是一種揶揄或謙遜,其實老攝影家們的理念與方向,在拍照時已了然於胸。他們儘早抓緊時機與快門,凝神、關注地將歲月刻劃在賽璐珞上。與數位時代的玩家、新秀相比,他們顯得更專心、更豁達,也更有人味。
《影像的追尋》的再版要感謝簡永彬的驅動與協助,以及遠足文化同仁的努力促成,當然更要對所有資深攝影家致意,他們這些珍貴的影像才是這本書的靈光所在。
「因為我們不時回頭看,所以才能無礙地往前看。」
是為序。
追尋與感念
回溯臺灣本土攝影家的蹤跡,應從二○年代陸續出現在民間各地的照相館開始去尋覓。當時,比較出名的,包括臺北的「太平寫真館」(曾桐梧)、「羅芳梅寫真館」、「亞圃廬寫真館」(彭瑞麟),基隆的「藍寫真館」、桃園的「徐寫真館」(徐淇淵)、臺中的「林寫真館」(林草)、新竹的施強、陳宇聰等等,他們的室內人像攝影,典雅而具韻味,既不流氣,也不顯得刻板模式化。當時所使用的玻璃底片及藥材都得用營業執照向特定的代理店才買得到,照明設備匱缺,只能利用傾斜屋頂及大型玻璃窗入射的自然光,在光源充分及適當時效內,將物像感光在櫻花、東方或伊爾富等二十五度以下的藥膜上,用長時間曝光以完成整個攝製過程。就是這麼嚴謹慎重的工作態度,使我們在今天重看曾桐梧的《自拍照》(一九二六),多少領會了那種技藝與經驗的密切結合,以及安詳、凝注的創作素質。一人二角的雙重曝光技法,是早期臺灣人像攝影的特色之一。
嘉義的張清言在當時是臺北帝大醫學部畢業的學生,他花了長時間在「立體攝影」的嘗試上,至今留存下來的一批人像攝影與生活記錄,融合了當時他對美術的認知與攝影的技藝,既傳達了寫實的基調和三度空間的真實感,也流露出攝影者的個性與氣度,十分巧妙、耐看。
三○年代的萌芽
三○年代的「南光寫真機店」(鄧南光)、「影心寫真館」(張才)、「林寫真館」(林壽鎰),經營者已漸能將攝影的角度從室內人像漸漸移轉到室外獵影速寫(Snap)上,他們都曾到過日本學習,在題材的選擇與技術的歷練上有較廣泛而深刻的心得,「記取寫實精神,著眼本土風情。」他們以這樣的意念活躍在三○年代至六○年代間的臺灣影壇上,持續有恆,令人敬佩。
《排灣族同胞》(一九四七)是張才早年為人類學家所做的田野檔案之一,他的「原住民面顏」系列,視角穩重、大方,光影與構圖簡潔有力,角色的精神與性格在紙上躍然欲出,四○年代四十年前的身手,張才真是為山地同胞逝去的那一段值得驕傲與自豪的日子,做了珍貴的見證。
從微粒顯影的肖像照到充滿現實動感的「跟蹤攝影」,林壽鎰的早年作品自我要求極高,他也能抓住現實中生動、感人的一刻。《玩笑》(一九六五)表達了少年生活的直率與活力,趣味盎然,令我們想起電影《童年往事》中的一幕,不過,現實中的人物顯得更自然,平實而真切。
五○年代的腳步
戰後初期,百廢待舉,攝影是一件奢侈的嗜好與消費,那時候攝影展覽極少,攝影團體也未形成,一直到四○年代末期,才漸漸有一些活動,譬如一九四八年「臺中外勤記者聯誼會」主辦的全省攝影比賽,以及稍後「臺灣旅行社」舉辦的「沙崙浴場攝影比賽」,開始吸引了一些攝影同好加入。「臺北市攝影會」(一九四九)、「聯合國文教處臺北攝影組」(一九五一)、「自由影展」(一九五四)、「新穗影展」(一九五五)的相繼成立,使得攝影人口逐漸增多起來。
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中國攝影學會」無疑地主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攝影趨勢,它所標榜、提倡的沙龍與畫意取向,的確也吸引了無數追求「唯美」與「意境」的初學者。但拍慣了「沙龍」情調的攝影家們,有時也會嘗試拍些寫實照,就像寫實攝影家有時也難免會「畫意抒情」一般。例如沙龍老將孔嘉的作品《原住民》(一九六一),就很貼切、傳神地記錄下一個民間顏容;不去刻意的設計擺飾,走向生活,將「生命」還給對象,不把它攝走或約制,這就是「寫實攝影」的一點基本堅持。
六○年代的風潮
進入六○年代,各地的攝影學會紛紛成立,本土攝影家對鄉情民事較有感情,他們以寫實記錄的風格來表達對周遭人物的關愛,以抗衡躲入象牙塔中的沙龍風格攝影。黃則修的「龍山寺」(一九五三-一九六一)以客觀、有恆的專業態度,第一個為早年的民間廟宇完成了建築、信仰、人文的影像報告。這些直陳民間休閒與信仰生活的照片,不矯飾、逃避或美化,今日看來格外動人,黃則修證明了龍山寺不是一座空洞、無味的廟宇,而是庶民生活與信仰的依賴所在,它過去不受注意只是攝影家不用心以及寫實精神的欠缺而已。
鄭桑溪也是六○初期衝勁十足的工作者。他花了長時間記錄的「基隆系列」、「九份系列」、「光影系列」、「飛禽系列」等,表現了鮮活的映象魅力,他運用自如的轉換鏡頭,壓縮或延伸現實時空,給與影像潛藏的觀測力。
張士賢、朱逸文、黃登可等人又是六○年代初活躍於日本攝影雜誌──《Photo Art》、《Nippon Camera》等月刊的投稿及積分得獎作家,稍後的謝震隆、許淵富也都在這些雜誌上享有佳譽。當時,他們因為作品的「寫實」風格常被拒於國內的沙龍評審制度門外,轉而投向日本,屢獲入選與得獎鼓勵,才持續影響了不少後來者,在寫實方向上努力。
張士賢是許多中南部攝影家亦師亦友的啟蒙者,許蒼澤、黃季瀛、劉安明等人曾受過他的鼓勵,對他的英哲早逝都深感懷念。張士賢的作風直率、俐落,他不刻意構圖,卻能抓住最自然、生動的一瞬,似乎是隨意取景,卻有一種敏銳的感應力與不慌不忙的氣度,作品的風格極為個人化。
「人類一家」的召喚
一九五五年Edward Steichen主辦的「人類一家」(The Family of Man)攝影展,其作品的精神多少影響了臺灣六○年代的攝影家。鹿港出生的許蒼澤、黃季瀛、林彰三,當時就不約而同地就各自喜好的題材,做了忠實而富人情味的記錄報導。
許蒼澤很早就養成「隨身拍」的習慣,有一陣子他身邊一直攜帶小相機,隨時在記錄人物鄉情。擦身而遇,信手拈來,那種偶遇中的淡然,心情既不十分接近,亦非遠離,保持一個「距離」去看,是他的慣用視角。
黃季瀛在鹿港文開國小做了二十幾年的教師,他對學童稚子的關心與興趣超過其他。由於長年的接觸,他似乎能窺伺出幼小心靈的喜怒哀樂,而在最準確地一瞬間不落痕跡地攝取了童年生活的種種回憶。
林彰三則對古風傳承與民俗祭儀特別有心,他用「生於斯、長於斯」的情感,拍下家鄉的大小點滴。《祭童之顏》(一九六二)巧妙地利用逆光剪影的效果,凝聚成一種心靈力量,生動、別致的線條與光影組合,使原本可能是單一刻板的表相,昇華成一種脫俗而具象徵意味的情境表白。
《進香》(一九六七)是臺中陳石岸的作品,那一對古稀老伴攙扶行進的姿顏,有著一種溫馨的感傷,「真」與「善」的追求,是陳石岸在寫實攝影生涯中所念念不忘的根本理念。
這些流露著動人情愫的感懷之作,承繼的精神是攝影最原初的本質──單純、直接、誠實的「觀察點」與「紀實眼」,它不賣弄形式或構圖,也不故步自封於保守的心態,在這些攝影家身上,我們也好像沒聽到「人道主義」的大聲吆喝,然而,我們在這些自然、委婉、摯樸的作品中,仍感受了「人」的素質與「生存」的哲學觀,以及對於生命個體,給與無限的尊嚴與懷念。面對這些饒富意義的省視片刻,我們勢必要給與珍惜及感謝的心意才是。
張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