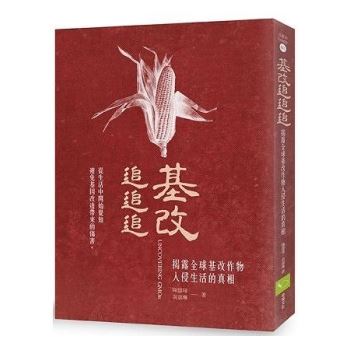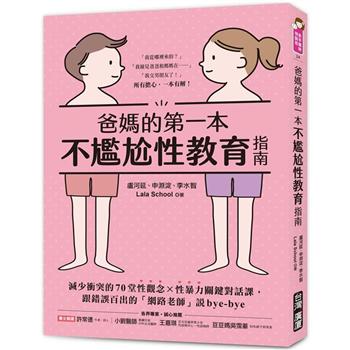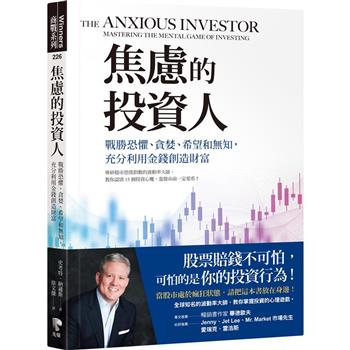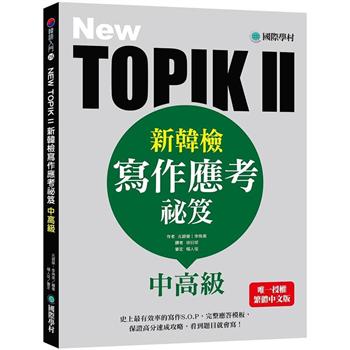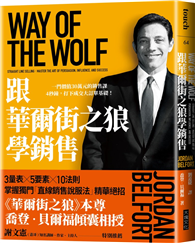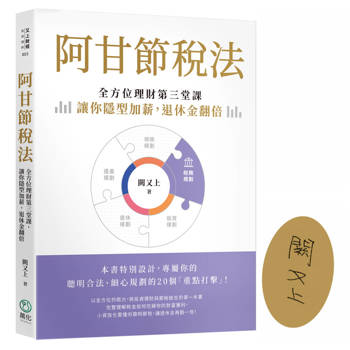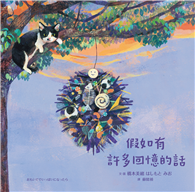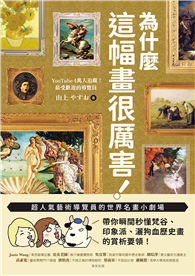【蘇聯政治體制的形成】
從列寧的建黨實踐來看,列寧在世的時候,蘇共就開始顯現出僵化的徵兆。列寧對這個問題是高度重視的,企圖通過建立黨的監察委員會等機構來健全黨內的權力平衡和糾錯機制。可是天不假年,他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史達林掌權後,逐步取消了黨的領導機構的權力制約和糾錯機制,政治體制逐漸僵化,給以後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在本章我們對列寧為建立新型政治體制所做的大膽探索及其局限性做了分析;對史達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產生、發展和定型的原因做了剖析,並分析了其社會和歷史根源。
一、列寧時期的探索
(一)列寧的建黨理論與實踐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離不開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十九世紀末二○世紀初的俄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農民暴動頻繁發生,學生運動聲勢浩大。形勢的發展一個激進的革命政黨提供一個奪取政權的契機。列寧敏銳地發現這一契機,他明確指出:「革命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唯一保證,是一條通向勝利的康莊大道。」從十九世紀九○年代中期開始,列寧就致力於在俄國建立一個不同於在資本主義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第二國際黨的新型政黨,以領導俄國的革命。
中國學者王堅紅認為列寧主張建立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與第二國際各國黨相比,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一是思想上必須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二是政治上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三是在組織上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筆者認為王堅紅的理解是準確的。
我們先看第一個特點,列寧指出:「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因為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它說明了革命的社會黨的真正任務……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領導這一鬥爭,而鬥爭的最終目的是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黨,因為革命理論能使一切社會黨人團結起來,他們從革命理論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們能運用革命理論來確定鬥爭方法和活動方式。」顯然,列寧所說的「革命理論」、「先進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當然這裡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列寧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另外,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單靠自身力量只能產生工聯主義意識,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意識,而社會主義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知識份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理論中成長起來的。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以便把它灌輸給工人階級。
我們來看第二個特點,列寧認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形成鞏固的思想統一,也就是在政治上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一八九九年和一九○二年,列寧曾先後為俄國黨提出過三個綱領草案,強調俄國黨必須堅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奪取政權和組織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他指出:「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是同《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特點,列寧認為新型的政黨必須是一個集中的、戰鬥的革命家組織。他指出:「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在流行由憲兵來進行有選擇的情況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相反,只要有了優良的革命品質就能保證比「民主制」更重要的東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這種更重要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在我們俄國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監督來代替它的」。因此,「革命家的組織應當包括的首先是並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這種組織必須是不很廣泛的和盡可能祕密的組織。」
一九○五年革命後,人民爭取到了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黨有了在黨內實行民主的條件,列寧對黨的組織建設的關注轉向認真地實行黨內民主,實行選舉制,一九○五年十二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列寧提議通過的決議中,確認「民主集中制原則是不容爭論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內容是:少數服從多數、部分服從整體、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各地方組織服從中央。列寧重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一九○六年五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寧指出:「現在留下的是一項重大的嚴肅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務。在黨組織中真正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進行頑強不懈的努力,是基層組織真正成為而不是在口頭上成為黨的基本組織細胞,使所有的高級機關都成為真正選舉產生的、要彙報工作的、可以撤換的機關。」
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中,列寧雖然強調少數服從多數,但沒有忽視對少數人民主權利的保護。他認為黨內少數派有權派代表參加代表大會並享有充分的「舌頭自由」,必須保證讓那些批評黨中央機關工作的黨的書刊能夠出版,甚至把允許出版不滿分子的著作的建議用黨章固定下來,以便使不滿情緒正當地表現出來。在列寧看來,正常的黨內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不致妨礙正常的工作。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但國內和國際的形勢都十分嚴峻。在這種情況下,黨總體上繼續沿用了十月革命前領導地下鬥爭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模式。列寧明確指出:「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近似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成為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黨員普遍信任的權威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列寧甚至強調:「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與國家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相適應,俄共本身也軍事化或半軍事化了。在黨內實行了「極端集中制」的領導體制和「戰鬥命令制」的工作方法:黨中央有權解散任何地方委員會;幹部的調配「全部由黨中央掌握」,「上級機關的一切決議下級機關必須絕對執行」;要求「在目前階段黨必須直接實行軍事紀律」等。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黨的八大上建立了黨的最高機關體系:選舉了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其任務是對政治工作實行總領導。為了領導黨的整個組織工作,通過了關於建立組織局的決定,並規定組織局每星期應舉行三次會議。列寧對兩個機構的相互關係作了準確地說明:組織局調配力量,政治局確定政策。它使集中和鐵的紀律的要求能夠很順利地變成具體的行動。
但是,在強調集中的同時,列寧並沒有忘記這種集中應當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他指出黨的各級組織「是民主地組織起來的」。「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列寧甚至提出了黨內監督的任務。一九二○年黨的九大決定成立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這樣,總的說來加強集中制是內戰時期建黨的主要方面,但是「列寧在採用這樣一些措施的同時,也明確強調其中大多數措施是與黨的本質相矛盾的,是應急的、只具臨時意義的,今後應當停止使用。」
在內戰時期俄共實行極端集中制雖然有其歷史合理性,但這種體制帶來的弊端也是明顯的。特別是內戰結束、新經濟政策實行後,極端集中制帶來的弊端就更加嚴重。一九二一年俄共(布)十大指出了戰時的集中制帶來的弊端,認為「集中發展了官僚主義化和脫離群眾的傾向;戰鬥命令制往往採取被歪曲和不必要的壓制形式,必要的特權變成了各種舞弊行為的憑藉;黨的機關必要的緊縮削弱了黨的精神生活……這一切引起了黨內的危機。」
面對危機,布哈林認為黨應適應新的和平條件,因為黨不再是「內戰的黨,而是國內和平的黨」。國家不再主要是「鎮壓的工具,相反,它為﹃合作﹄和社會統一創造必要的和平條件。」但是「列寧沒有考慮政變黨的體制和運作方式。他更多地把注意力傾注在完善政治機器上。……一是發展和擴大民主,二是繼續加強集中。」
從實際情況來看,發展和擴大民主的措施不得力,而加強集中的措施卻是實實在在的,之所以會如此,主要是因為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成是向資本主義的退卻。而要保證退卻不發生混亂,不變成逃跑,就必須強調集中和紀律。其具體措施是:禁止派別存在和任命制。
在俄國黨的歷史上,幾乎圍繞每一個重要的、有時甚至是不重要的問題,都出現過派別。經常性的派別活動,成為黨的一大特色。派別活動是表達黨內不同意見的有效形式之一,有利於保持黨的活力,防止黨的僵化。派別活動的消極作用在於它會破壞黨的統一和集中。有時派別之間的爭論和分歧會被敵人所利用,從而使黨的利益受到損害。
列寧更多地看到了派別活動的消極作用,所以才決心禁止派別活動。儘管他對派別所下的定義是嚴格的即有特別的綱領和紀律的組織才是派別,而且在實踐上他沒有把任何不同意見作為派別來處理。可問題在於,取消了派別活動,如何保持黨內不同意見表達管道的暢通?如果黨內不同意見不能表達,黨能避免僵化嗎?列寧雖然看到了這些危險,遺憾的是,他所找到的替代方案僅僅是建議設立《爭論之頁》這樣的出版物。事實證明,這樣的建議面對高度集中並迅速走向僵化的巨大的黨的機器,顯得脆弱無力。
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八大決議確定,「黨的工作人員的全部分配工作由黨中央委員會掌握。」在所有蘇維埃國家機關裡,都成立了最嚴格地服從黨的紀律的黨組。俄共(布)十大實際上把組織工作的大部分都交給了書記處,在一九二三年俄共(布)十二大上,史達林在代表中央作組織報告時強調黨的機構「必須毫無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門和黨賴以掌握我們的經濟機關並實現自己領導的全體工業指揮人員。」這實際上是代表中央發布了由黨任命而不是由選舉產生各級行政管理幹部的指示。
伴隨著任命制普遍推行,俄共中央委員會解散經選舉產生的地方黨組織,由委任的人另組班子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例如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俄共中央兩次解散了烏克蘭共產黨經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另行任命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
任命制窒息了黨內的民主生活,使官僚主義盛行同時也損害了黨員的基本權利,使他們失去了主人翁感,從心理上乃至政治中對黨產生異己感,最後疏遠離開這個黨。列寧越來越清醒地看到了這種「在特殊情況下」才「必要的」任命制的弊端,多次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選舉制來代替它,遺憾的是列寧的想法和黨的決議由於史達林的抵制而沒有落實,相反,一九二○年書記處建立的推行任命制的兩個主要部門―登記分配局和組織指導部恰恰是黨的十大提出要排除委任制後的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全面開展工作的。只是和以往的公開任命制稍有不同,地方委員會的選舉形式表面上得到了保留,任命制被稱為「推薦」。對此捷爾任斯基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中央會議上批評說:「黨的渙散、黨內生活的窒息和任命日益代替選舉導致了一場政治危機,並使黨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陷於癱瘓。」
在列寧生命的後期,集中制所帶來的弊端,比如官僚主義、個人專權都已顯現出來,憂心忡忡的列寧為了制止這個趨勢採取了如下措施:一是通過吸收第一線的工人把中央委員會擴大到五○―一○○人,以便減少官僚主義和防止個人專權。可是,被擴大進中央委員會的人並不是第一線的工人,而是由史達林主持的組織局和書記處挑選出來的基層幹部。當然即使是來自第一線的工人,也難以達到列寧所預期的目的。二是建議把掌握了「無限權力」的史達林調離總書記的崗位,換一個「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也較少任性的同志。」遺憾的是由於史達林等人的抵制,列寧的這一建議亦未被接受,問題在於,如果制度設計有缺陷,僅更換領導人並不能防止個人專權的弊端。應當指出的是,列寧對集中制的加強一直是心懷戒備的。他把高度集中制看作是受形勢所迫,不得已而採取的暫時性措施,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在有生之年沒有來得及為俄共設計出一個完整的監督和制衡機制,而且在理論在實踐上沒有完成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換句話說,沒有解決一個執政黨的權力來源問題或者說合法性的問題。因為對於革命黨來說它的任務是用暴力奪取政權,而作為執政黨它就必須解決它的權力來源問題,即獲得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和支持。而黨內外的任命制實際上使得民主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名存實亡,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難以很好地解決。這就為史達林時期建立的對國家、社會和意識形態進行全面控制的政黨模式留下了隱患。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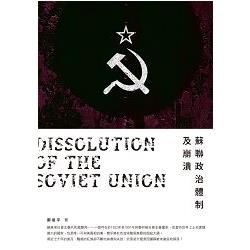 |
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6 |
社會哲思 |
$ 396 |
政治 |
$ 396 |
政治 |
$ 405 |
政體/政治制度 |
$ 405 |
社會人文 |
$ 405 |
政治 |
$ 408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450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
究竟是什麼,讓這個國家最終走向崩潰?
以美蘇對抗為背景精闢分析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原因!
本書以美蘇對抗為背景分析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研究和歸納蘇聯政治體制的特徵,對美蘇兩國的對抗歷史及其影響展開分析,從兩國之間的互動來揭示蘇聯政治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
共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對蘇聯僵化的政治體制的六個特徵及演變原因進行分析。運用當代著名社會學家杜爾克姆的社會團結理論和科塞及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對赫魯雪夫時期的改革與失敗、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停滯以及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與失敗作了探析。
下篇主要闡述了美蘇對抗蘇聯政治體制的負面影響——使蘇聯的政治體制得不到修復的時機,最終走向演變。首先分析美蘇從對抗到冷戰的過程,並對美蘇對抗的歷史和根源進行簡要地疏理。
作者簡介:
鄭易平,教授、博士生導師。1960年生,武漢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政治學理論等。現為南京航空航太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著有《21世紀的較量——美日歐俄四強的走勢與中國》,獲江蘇省第六屆哲社優秀成果獎;《冷戰的終結——20世紀超級大國政治體制特徵、穩定性及對抗研究》,首次從政治體制角度分析冷戰終結的原因;《大家精要•伯恩施坦》,首次從正面、客觀、公正角度研究其思想,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穩定性視角下的美英政治制度運行機理比較研究」。在核心期刊發表數十篇專業論文。
TOP
章節試閱
【蘇聯政治體制的形成】
從列寧的建黨實踐來看,列寧在世的時候,蘇共就開始顯現出僵化的徵兆。列寧對這個問題是高度重視的,企圖通過建立黨的監察委員會等機構來健全黨內的權力平衡和糾錯機制。可是天不假年,他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史達林掌權後,逐步取消了黨的領導機構的權力制約和糾錯機制,政治體制逐漸僵化,給以後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在本章我們對列寧為建立新型政治體制所做的大膽探索及其局限性做了分析;對史達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產生、發展和定型的原因做了剖析,並分析了其社會和歷史根源。
一、列寧時期的探索
(一)...
從列寧的建黨實踐來看,列寧在世的時候,蘇共就開始顯現出僵化的徵兆。列寧對這個問題是高度重視的,企圖通過建立黨的監察委員會等機構來健全黨內的權力平衡和糾錯機制。可是天不假年,他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史達林掌權後,逐步取消了黨的領導機構的權力制約和糾錯機制,政治體制逐漸僵化,給以後的改革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在本章我們對列寧為建立新型政治體制所做的大膽探索及其局限性做了分析;對史達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產生、發展和定型的原因做了剖析,並分析了其社會和歷史根源。
一、列寧時期的探索
(一)...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以美蘇對抗為背景】
蘇聯解體已有二十幾年了。學者們早已從最初的震驚或興奮中走了出來,投入到艱苦和細緻的研究中去,進行了多維度、深層次探索,發表了大量的有價值的論著,如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專家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大失控和大混亂》、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俄羅斯前總理普裡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前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大衛‧科茲等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利加喬夫的《警示》、戈巴契夫的《戈巴契夫的回憶錄》和著...
蘇聯解體已有二十幾年了。學者們早已從最初的震驚或興奮中走了出來,投入到艱苦和細緻的研究中去,進行了多維度、深層次探索,發表了大量的有價值的論著,如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專家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大失控和大混亂》、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俄羅斯前總理普裡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前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大衛‧科茲等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利加喬夫的《警示》、戈巴契夫的《戈巴契夫的回憶錄》和著...
»看全部
TOP
目錄
【以美蘇對抗為背景】
【上篇 蘇聯政治體制】
第一章 蘇聯政治體制的形成
第二章 史達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特徵及弊端
第三章 史達林模式下的國家與社會
【下篇 美蘇對抗與蘇聯政治體制的崩潰】
第四章 從對抗到冷戰:美蘇對抗的過程
第五章 對抗的後果:進一步僵化
第六章 走向崩潰:改革的嘗試及其失敗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上篇 蘇聯政治體制】
第一章 蘇聯政治體制的形成
第二章 史達林模式政治體制的特徵及弊端
第三章 史達林模式下的國家與社會
【下篇 美蘇對抗與蘇聯政治體制的崩潰】
第四章 從對抗到冷戰:美蘇對抗的過程
第五章 對抗的後果:進一步僵化
第六章 走向崩潰:改革的嘗試及其失敗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鄭易平
- 出版社: 獨立作家 出版日期:2016-01-20 ISBN/ISSN:9789869225700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358頁 開數:14.8x21 cm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