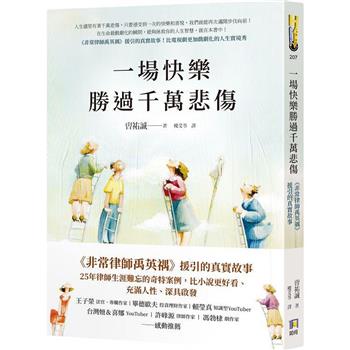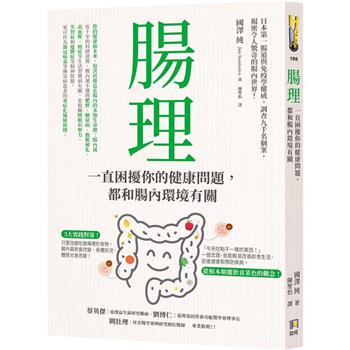一段吹不散的一九八○年代青春記憶,一個愛唱歌的女孩還沒唱完……
她不美麗,只是很努力地與自己的平庸和平共處。
她不美麗,只是很努力地與自己的平庸和平共處。
這是一部青春回憶,也是一課遲來的情感教育,由三十四篇散文、二十四首手寫詩與多幅插畫交織而成,透過一位平凡高中女生的日常想像,呈現台灣一九八○年代的單純校園生活,追憶北投復興高中那段難以忘懷的青春時光,回顧少女時期自我成長的心路歷程。
無論在北投山城小宇宙過得多麼詩意,也擺不平青春期荷爾蒙作祟的少女心事,這個愛唱歌的女孩怕寂寞,有花癡單戀的傾向,喜歡黏在閨密身邊,對宿舍室友惡作劇,對校園美女品頭論足,對社團學長崇拜迷戀,也對老師敬愛有加,然而,那時候的她搞不清楚舞會是致命的,懵懂中獻出了第一支舞,談了一場自以為是《傲慢與偏見》的初戀,畢業後各自分飛。
三十年後,少女蛻變成女人,但青春記憶仍窩在角落,不時出來騷擾著她,某個夢醒時分,她決定去找尋初戀情人,明知「即便覓得了他,青春再也無法回頭了」,還是一找再找,似乎不這樣就不會明白某些事,又彷彿不是她要找,而是青春的記憶召喚她回去面對什麼似的。
本書特色
◎台灣一九八○年代校園青春故事
◎全書穿插24首作者手寫詩與鋼筆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