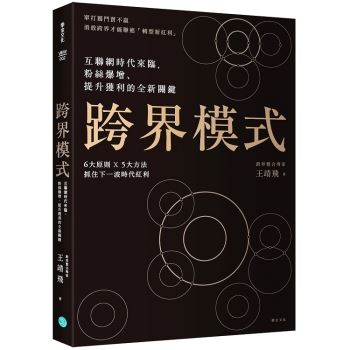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你需要這本書,我把它當成救命寶典。」
老化的過程中,有多少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又有多少是基因、命運或偶然所決定的?
老化是「自然的現象」,我們什麼都不能做。真的嗎?
我們可以讓老化停止嗎?或,至少讓它慢下來?
現在開始,一點小小的改變,可以決定你老後是臥病在床,或是能跑能跳!
★沒能殺死你的,會讓你活更久!★
人是老了才不能動,還是因為越來越不動所以變老?
健康挨餓法有效否?
施打成長激素真的可以回春嗎?
高碳水化合物或高蛋白飲食法,會觸發體內哪些老化或長壽基因分子?
偶爾來點極限運動或冬泳對身體有益?
壓力能讓身體的分子結構更健康?
一點點阿斯匹靈可保心血管健康?酒精,Why not?
★一場探尋永生的科學之旅!★
貼身專訪頂尖老化科學家和百歲的健康人瑞,一次搞懂所有似是而非的養生方法。就算遺傳到壞基因,只要知道一點關於長壽的知識,並從現在開始實踐,不用花大錢購買可疑的保健品或做手術,你也可以擁有健康的老後,而且看起來更年輕!
★用科學解開老化的祕密!★
長生不老,是全體人類最古老也最本能的願望。作者用幽默自嘲的口吻,帶領讀者踏上一場迷人的科學之旅,從明顯可見的皺紋和禿頭,到看不見的細胞及基因研究。
頂尖實驗室:尋訪各個頂尖生物實驗室,看看科學家如何一一破解老化過程。
百歲人瑞:貼身調查採訪百歲以上的健康人瑞,找出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異同。
保健食品:各種爆紅的保健品(例如白藜蘆醇、人類生長激素、紅酒藥丸、抗氧化劑等等)值得相信嗎?
體重管理:肥胖、運動、短期禁食,是否真的與老後健康有關?
最佳建議:揭開老化科學裡的騙局,給你健康長壽的最佳建議。
老化其實遠比我們想的更具可塑性,事實上,老化可以被「駭」。你的老年生活不需要像你的祖父一樣。老化的情況至少有一部分操之在己,老化的兩大疾病,心血管疾病與糖尿病,大多是可以被避免的,甚至在一些情況中是可逆的。第三大疾病,可怕的阿茲海默症,也可能有高達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是可避免的。
改變壽命的配方或許即將出現,但在那之前,有一個保證有效的方法,看完本書,你就會知道。
作者簡介:
比爾・吉福德(Bill Gifford)
《戶外探索》雜誌(Outside Magazine)特約編輯,也為《連線》雜誌(Wired)、《腳踏車》雜誌(Bicycling)、《男士健康》雜誌(Men’s Health)供稿。寫作主題廣泛,包含科技、運動、瘦身和健康類型等領域,文章曾獲選摘錄於《美國最佳體育寫作》(The Best American Sports Writing)。
第一本書《萊迪亞德》(Ledyard)主要描述十八世紀的美國探險家、作家和企業家。《老化,可以被駭》則是他的第二本著作,甫出版便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獲得媒體、讀者等各方好評。
現居美國紐約市及賓州中部,嗜好包括腳踏車、滑雪、跑步和美食。
雙親健朗,祖母朵莉斯(Doris)也年近百歲,這正是他努力達成的人生目標。
譯者簡介:
蔡世偉
台大外文系畢業,有時教書,有時翻譯,有時寫作,有時無所事事。著有《孩子們的南陽街與大人們的補習班》,譯有《麥可喬丹傳》與《公開:阿格西自傳》等書。
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Waynetsai1008/
個人信箱:waynetsai1984@gmail.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萬芳醫院家庭醫學科‧謝瀛華主任│專業審定
⚫你需要這本書,我把它當成救命寶典。——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天生就會跑》作者
⚫這本書是針對「我們為何會老化?」此一難題所寫成的傑作。——大衛‧博瑪特醫師(David Perlmutter, MD),《無麩質飲食,讓你不生病!》作者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人類壽命大幅延長,如何在變老時仍保持健康活力,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觀點。——史蒂芬.強森(Steven Johnson),《我們如何走到今天?》作者
⚫充滿啟發性,很棒的一本書。——華爾街日報
⚫許多病人迷信未經實證的抗老化藥物,本書提供了他們與我都需要的資訊,可以用來評估這些藥物的風險與療效。這是一本迷人、充滿資訊性又有趣的書。——內科醫生coastalon
⚫書中有許多振奮人心的科學研究,未來或許我們真的可以減慢或逆轉老化。作者文筆風趣幽默,讀來像小說一樣令人愛不釋手。我會推薦給每個人。——Antonia
⚫很棒的一本書,讀完後真的激勵我為了永保青春去運動。——Anthony H. Sutton
⚫作者在書中時常強調「使用它,不然就會失去它」,這一點確實可以活化生理和心理。——Mr. Joe
⚫如果你正在老化,你必須讀這本書。非常實用,研究很嚴謹,而且充滿娛樂性。——REH
名人推薦:萬芳醫院家庭醫學科‧謝瀛華主任│專業審定
⚫你需要這本書,我把它當成救命寶典。——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天生就會跑》作者
⚫這本書是針對「我們為何會老化?」此一難題所寫成的傑作。——大衛‧博瑪特醫師(David Perlmutter, MD),《無麩質飲食,讓你不生病!》作者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人類壽命大幅延長,如何在變老時仍保持健康活力,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觀點。——史蒂芬.強森(Steven Johnson),《我們如何走到今天?》作者
⚫充滿啟發性,很棒的一本書。——華爾街日報
⚫許多病人迷信未經實...
章節試閱
【前言】
要變年輕永遠不嫌老。
──梅.蕙絲(Mae West)
當那位年輕科學家癱倒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意識尚存的最後一刻,或許終於瞭解:為了實驗,將亮光漆塗滿全身可能不是個好主意。然而,他是一位科學家,而好奇心有時很危險。
他一直想要探究人類皮膚的功能,為何如此耐用卻又如此脆弱──對於陽光和火焰的燒燙那麼敏感,不使用銳利的手術刀也能輕易劃破。他想知道:如果把皮膚全部覆蓋起來,會發生什麼事?
於是,一八五三年春天,本該平淡無奇的維吉尼亞醫學院(the 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實驗室裡,夏爾-愛德華‧布朗-塞卡爾教授(Charles-Édouard Brown-Séquard)脫下所有衣物,拿著一把刷子和一桶高級亮光漆在自己身上施工。沒多久,他就將黏稠的液體塗滿全身每寸肌膚。
那個年代,科學家的白老鼠基本上就是自己。曾經有個實驗,三十六歲的布朗-塞卡爾為了取得消化液,把一塊海綿壓進自己的胃,導致餘生都得承受胃食道逆流之苦。就像他一位學生日後所憶述,這樣的做法使他成為「最獨具一格的教授」。
亮光漆事件讓他的傳奇再添一樁。這位教授縮在自己的實驗室一角,不停顫抖,顯然離死亡不遠。某個學生不小心被絆到,花了點時間才看出地上這一身棕色的人不是逃跑的奴隸。這位思緒敏捷的年輕人趕緊開始瘋狂地把褐色的油汙刮除,卻反被受害者劈頭痛罵,他很憤怒,因為「亮光漆讓他倒在一角,而某個莽撞的人把他從那個角落拖出來,正當他要喘最後一口氣時,惡意地把他身上的東西刮除。」
然而,多虧了那個機警的醫學院學生,布朗-塞卡爾才能繼續活下去,成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今天,他被視為內分泌學(也就是腺體與賀爾蒙的研究)之父。另外,在我們對於脊髓的瞭解上,他也做出極大的貢獻。有一種特定的癱瘓仍被稱作「布朗-塞卡爾症候群」。然而,他絕非一個象牙塔內的學究。在他的家鄉模里西斯,他曾經花了好幾個月對抗一種致命的霍亂傳染病。為了在自己身上試驗一種新療法,他吞下病患的嘔吐物,故意讓自己染病,也差點讓他歸西。
他在里奇蒙的教職沒能撐完那一年,因為南方首都受不了這個法國人古怪的作風與黝黑的膚色。於是,他搬回巴黎,在剩下的生涯中往返於法國與美國之間。算起來,他的人生有整整六年的時間待在海上,這會讓他已故的船長父親驕傲。然而,儘管他持續移動,他還是逃不過年老。六十歲時,布朗-塞卡爾再一次抵達巴黎,以法蘭西公學院教授的身分。他的朋友包括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也就是巴斯德殺菌法那個巴斯德,以及美國醫藥的開路者之一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這個出身遙遠模里西斯的貧窮孤兒在一八八○年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伴隨著一大堆其他獎項。最高的成就,是在一八八七年被選為生物學會的會長,確定了他在法國科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當時,他已經七十歲,而且總是很累。在這十年之中,他注意到身體出現一些改變,其中沒有一個是好的。以前他總是帶著狂熱的活力忙進忙出,在樓梯爬上爬下,一分鐘可以連珠砲講好多話,唯一停下來的時候,是要拿一張紙記下自己絕妙的想法,那些紙張往往消失在口袋裡。他一晚只睡四或五個小時,常常凌晨三點就在書桌前展開工作。他的傳記作家麥可.阿米納夫暗示,他可能患有躁鬱症。
但是,他那曾經無窮無盡的活力現在似乎拋棄他了。他有證據,因為一直以來,他追蹤著自己的身體,測量肌肉力量之類的東西,並且仔細記錄下來。四十幾歲的時候,他可以單臂舉起五十公斤。如今,他的極限是三十八公斤。他很容易累,卻又睡得很差,而且受便祕所苦。所以,身為一個科學家的他決定要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塞卡爾的不老藥
一八八九年六月一日,布朗-塞卡爾教授站在生物學會前面,發表了一篇演說,這篇演說將永遠改變他的生涯、聲譽,以及大眾對於老化的態度。在那次演說中,他報告了一個自己進行的驚人實驗,他把年輕的狗和天竺鼠的睪丸磨碎,製成一種液體,然後把這種液體注射進自己的身體裡。
他的想法很簡單,年輕動物體內的某種東西,更精確一點,牠們生殖器裡的某種東西,似乎提供牠們青春活力。不管那是什麼,他都想要。經過三週的注射循環之後,他宣稱:「讓我的助手們很驚訝的是,我可以站著做實驗好幾個小時,完全不覺得需要坐下。」
測試顯示他的力量似乎回來了,他現在可以舉起四十五公斤的重量,這個進步意義重大,他又可以書寫直到深夜,而不感覺疲憊。他甚至誇張到測量自己的「尿液射程」,發現比起注射之前,噴尿的距離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於便祕問題,他驕傲地記下:「我很久以前擁有的力量又回來了。」
聽他演講的同事們在驚恐與羞愧之間掙扎。狗睪丸的萃取液⋯⋯?他老後瘋了嗎?後來,其中一個同事攻訐說布朗-塞卡爾的古怪實驗只是證明了「七十歲教授退休的必要性」。
布朗-塞卡爾沒有受到嚇阻,他讓其他的醫生與科學家可以免費取得他的魔法化合物(現在由公牛的睪丸製成),希望他們可以重覆他的體驗,有一些人真的感受到了。然而,來自同儕的評價仍然尖銳。一位曼哈頓的醫學博士在波士頓環球報的頁面上抗議道:「這等於回歸中古世紀的醫療系統。」
然而,在學術的殿堂之外,布朗-塞卡爾立刻變成英雄。幾乎在一夜之間,郵購企業家開始販售「塞加爾的不老藥」,售價是二十五劑注射量,兩塊半。這藥使用這位醫生的名字卻跟他毫無關連。可想而知,報業樂翻了,至少它們可以把睪丸液這個詞印出來。匹茲堡一位職業棒球選手吉姆.葛爾文公開始用這種不老藥,希望可以讓自己對上波士頓時投得好一點,在當代的紀錄中,這是運動員第一次使用增強表現的物質。這位老教授甚至被流行歌曲傳頌:
最近轟動的是塞加爾的不老藥
那讓白髮蒼蒼的老人變成年輕小夥子
不用付大把銀子給醫生,也不用吞藥
更不用把人埋進教堂後面的院子
讓人傷心的是,事實證明,最後一行歌詞只是一廂情願,一八九四年四月二日,生物學院演說後五年,在他七十七歲生日的前六天,布朗-塞卡爾與世長辭。儘管名滿天下,但他沒有從不老藥上賺到半毛錢。他的同儕科學家終究做出結論,認為布朗-塞卡爾歸功於「睪丸液」的神奇回春效果,只不過是安慰劑效應,儘管如此,他仍開啟了一陣似乎讓最理性的男人與女人失心瘋的回春狂潮。
回春熱潮
下一個風潮是一種叫做「斯太納赫氏手術」的東西,這種手術承諾能修復男人的活力,但其實不過是普通的輸精管結紮術。儘管如此,這種手術在歐洲的男性知識分子圈裡大行其道,使用者包括詩人葉慈,六十九歲的他娶了一個二十七歲的妻子。甚至連熟知陽具崇拜的佛洛伊德都宣稱自己對這種手術的成果很滿意。
在美國,回春熱潮在一九二○年代引爆,當時一位名叫約翰.布林克利的專力醫藥業務讓一種手術大受歡迎。那種手術基本上就是把新鮮的山羊睪丸植入疲憊的中年男子的陰囊裡。早在一八七○年代,布朗-塞卡爾就曾經在狗身上嘗試類似的實驗,但是,連他都不敢嘗試跨物種的移植。布林克利沒有這種疑慮與不安,可能是因為他沒受過真正的醫學教育。然而,他確實擁有一座廣播電台,在卡特家族與年輕貓王的表演之間,他不間斷地廣播這種手術的神奇見證。
在這幾十年間,他幫數千名病患動手術,讓他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同時,幾十個人在他的手術檯上死去,還有幾百個人因為他拙劣的手術技巧跛足或殘廢。但全美疲憊的、力竭的、委頓的、無能的、老化的男人們,甚至還有一些迫切要再年輕一回的勇敢女人,仍繼續朝他湧去。
他們不知道的是,光是可以活下來,就已經很幸運了。
【前言】
要變年輕永遠不嫌老。
──梅.蕙絲(Mae West)
當那位年輕科學家癱倒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意識尚存的最後一刻,或許終於瞭解:為了實驗,將亮光漆塗滿全身可能不是個好主意。然而,他是一位科學家,而好奇心有時很危險。
他一直想要探究人類皮膚的功能,為何如此耐用卻又如此脆弱──對於陽光和火焰的燒燙那麼敏感,不使用銳利的手術刀也能輕易劃破。他想知道:如果把皮膚全部覆蓋起來,會發生什麼事?
於是,一八五三年春天,本該平淡無奇的維吉尼亞醫學院(the Medical College of Virginia)實驗室裡,夏爾-愛德華‧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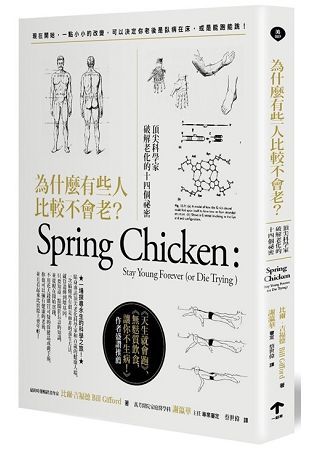
 2018/06/07
2018/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