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中三地的複雜糾葛,在黑紅交替的歷史舞台上,釀成了殺人慘劇。
而台灣島上的菩薩,究竟又為何而怒?
1946年3月,貨船「朝風丸」載著三百多名在日台灣人,從日本回到基隆港。楊輝銘和新婚妻子林彩琴,也搭著這艘船回到久違的家鄉。沒想到,在彩琴娘家菩薩庄附近,一位駐守兵舍等待遣返的日本軍官,竟在兩人回台當天遭到殺害。兩位警備司令部的中國軍人奉命進行調查。不久後,在猶如密室的菩薩山上又發生了另一樁案件,被捲入事件中的楊輝銘,開始了追兇的旅程……。
本書是陳舜臣唯一一本以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書中如實呈現了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樣貌,以及在歷史夾縫中求生存、努力適應政權交替的台灣人民的心聲。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無可奈何地深陷在時代洪流之中,五十年前先是被迫成為「日本人」,戰後又在一夕之間變成「中國人」,連「國語」都必須從頭學習。然而,到底何謂中國人呢?陳舜臣為所有對這份哀傷產生共鳴的人們,寫出了屬於他們的故事。
【本書特色】
★ 如實呈現戰後初期台灣的風土民情。
在基隆碼頭旁,可以看見穿著枯葉色軍服的中國士兵、解除武裝等待遣返的日本軍隊、開吉普車到處跑的美國大兵、拉人力車的苦力、大聲叫賣的台灣小販、在路上攬客的卡車司機,還有油的味道、南國水果的香味,以及懷念的故鄉話。
大稻埕小巷裡則上演著重新流行起來的布袋戲和傀儡戲,不時還會響起震耳欲聾的鑼鉦聲與鞭炮聲。街頭小販則在民房的「亭仔腳」下兜售商品。
菩薩庄的農家四周,圍繞著蒼翠茂盛的竹林、低矮的秧苗、甘蔗田與椪柑田。飄盪著茉莉花香的鄉間小路上,有坐在水窪戲水的水牛、氣急敗壞拿著樹枝趕牛的赤腳少年。而各種婚喪喜慶的民間習俗,以及佛儒道三教混合的寺廟,也讓人感受到濃厚的台灣鄉土味。
★ 鮮活細膩地描寫在大時代下受時勢左右的人物群像。
. 戰前被強行帶往日本的海軍工廠工作的少年徵召工,戰後流落日本街頭,數月後才得以返台。
. 戰前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偷偷潛入上海參加抗日組織,後來卻不幸在中國病逝。
. 日治時期因家裡有個抗日的「叛國賊」兒子,為了保全家人不得不積極協助日本當局的庄長,戰後卻被懷疑是「漢奸」,不得不辭去職務。
. 在八年抗戰中,被迫與家人分隔兩地的中國軍人,戰後又被國民政府派往台灣。
. 戰前辛苦學日語的17歲鄉村少年,戰後又得騎著腳踏車通學,到台北上夜間速成班重新學習「國語」。
. 從重慶回台,「因時得勢」前途無量的台灣人。
★ 親身經歷過戰爭與殖民統治的陳舜臣,在作品中描繪出所有台灣人都共同背負的身分認同掙扎與糾結心境,同時也展現了對於遭受苦難者的溫柔同理。
【真情推薦】
「身為六年級生,總覺得對台灣近代史的認識有個斷層,因為那裡充斥著教科書不肯說、老一輩人不敢說的敏感陰影。透過陳舜臣的筆,原本模糊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隨著扣人心弦的本格推理情節,我們彷彿也一起走過了那驚濤駭浪的年代。」
──天地無限(推理小說家)
「以閱讀者熟悉的日常經歷或聽聞過的往昔歷史作為敘事經緯,結合推理類型特有的線索埋設與串接,陳舜臣內斂的文字深處有困惑、有憤怒,亦有彷若預言的洞察針砭,即便在成書半世紀後來看,依然令人深思低迴不已,強烈感受到一位優異小說家的纖細心思與成熟智慧。」
──冬陽(推理評論人)
「見過空襲、看過二二八的陳舜臣,對歷史境遇有深刻感想,對時代的人性理解且同情。這種柔軟、悲憫且反戰的態度,存在『推理』這種類型創作中,形成獨特的魅力。《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台灣為背景的長篇推理小說,他揭開戰後台灣那段權力真空時期,這塊土地的經歷。也寫滿了他留台三年在鄉土上所體會的情感。」
──阿潑(文字工作者)
「若問我最近最想影像化的小說是哪本?我會斬釘截鐵地說:『《憤怒的菩薩》!』歷史小說巨匠陳舜臣先生從宏觀又獨特的歷史時間點切入,故事人物的情感幽微卻深刻,更有懸疑感十足的偵探元素和情節!這麼迷人的小說怎能讓讀者錯過呢?」
──曾英庭(《衣櫃裡的貓》、《椰仔》導演)
「誰用小說鉅細靡遺描繪了戰後的台灣?誰以那個兵荒馬亂、時代轉瞬為背景寫了推理小說?除了緊湊暢快的節奏和扣人心弦的情節,本書更顛覆了固有的『台灣視角』,以『在日台灣人』的獨特眼光,為台灣的特殊時刻留下彌足珍貴的社會素描,以及大量的信息。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為日本社會留下大量的戰後浮世繪;而台灣的戰後,幸虧有陳舜臣,幸好有《憤怒的菩薩》。台裔日本文豪陳舜臣的《憤怒的菩薩》,可說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推理小說,是被遺忘半個世紀的滄海遺珠。」
──譚端(偵探書屋店長)
游擊文化2016年出版「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
《憤怒的菩薩》(怒りの菩薩,1962)
陳舜臣唯一一本以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一窺戰後台灣社會與政治的詭譎氛圍。
《青雲之軸》(青雲の軸,1974)
陳舜臣自傳小說,娓娓道出一位小說家的青春畫像,與他身為殖民地人民所走過的大時代。
《半路上》(道半ば,2003)
陳舜臣前半生自傳,敘述自己於殖民母國的生活點滴及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沉痛哀傷。這些經過歲月沖刷而沉澱下來的文字,揭露了他埋藏心中最深的情感與記憶。
作者簡介:
陳舜臣
1924年2月18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人家庭。1941年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隔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此後兩人結為終生摯友),1943年因戰事提早畢業,留在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教,參與編纂印度語辭典的工作。1946年回到宛如異鄉的故──台灣,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並親眼見證戰後台灣的社會巨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他極大的衝擊與創傷,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便於1949年返回日本。
在家族事業從事貿易工作的十年間,陳舜臣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興起寫作的念頭。1961年,他以《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初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隨筆、評論等作品,並得到直木賞、推理作家協會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的推崇。1993年,NHK將歷史小說《琉球之風》改編為同名大河劇。
陳舜臣於1962年發表了以戰後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1974年,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揭述其生為在日台灣人所遭逢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成長故事。2003年發表自傳《半路上》,讓人一窺這位小說家動人的半生歲月與他走過的大時代。
日中建交後,陳舜臣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放棄中國籍,正式歸化日本籍。2015年1月21日,陳舜臣於最鍾愛的城市神戶辭世,留下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以及波瀾壯闊的一生。
【書系企劃團隊簡介】
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 POC)
由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譯者簡介:
游若琪
也敲鍵盤也拿畫筆,遊走於日文與圖畫之間的專職譯者。一邊翻譯著故事中爬山的片段,一邊想像八仙樓的雞捲到底是什麼味道。不時出現在故事中的台灣人事物,有一種既親切又遙遠的感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
章節試閱
朝風丸
船內的大合唱一旦開始便停不下來,少說要一小時後才會停止。
我和妻子彩琴一起來到甲板。
「好舒服喔!」
妻子深深將海風吸滿胸膛後說道。
我靜靜點頭附和。
兩千三百噸的「朝風丸」雖然是一艘老舊的貨船,卻也是一艘幸運的船。大有來頭的商船接二連三成為魚雷和轟炸機的目標,沉入太平洋海底;但朝風丸卻沒有絲毫損傷,幸運存活下來並成為忙碌的遣返船。
朝風丸駛離宇品港,朝台灣的基隆港前進。它承接了將在台日本軍民撤返日本的業務,去程則搭載了在日台灣人。這趟航程也有三百多名台灣人搭乘。由於它是貨船,沒有客房,將鋪有碎石的船底覆蓋後,便成了大通鋪。三百多人在這裡席地而睡的景象,煞是壯觀。而且,大部分的乘客都是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戰爭時期,他們被強行帶往日本,作為徵召工人在各地的工廠工作。
搭乘朝風丸的徵召工人來自海軍工廠,大約有兩百名。其餘是被遣返的一般人。他們人數眾多且年輕氣盛,彷彿整艘船的乘客只有他們似的。
一旦歌聲從這群人的某個角落傳出,隨即就會變成大合唱。最初,他們唱的是台灣民謠,不過沒多久就唱完了。他們受的是日本教育,熟悉的台灣歌曲不多。此外,他們在「皇民化運動」盛行時長大,甚至不能在大庭廣眾下用母語唱歌。
因此,母語歌曲唱完後,他們便開始唱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本軍歌。
唱台灣民謠時,明明懷著望鄉的思緒,一唱起軍歌,唱法就變得自暴自棄。唱得斷斷續續實在令人懊惱,導致他們忘記歌詞也硬要唱出聲。唱膩軍歌後,這群年輕人開始唱起他們在日本的「自由世界」度過的半年中,所學會的下流歌曲。
戰爭一結束,幾萬名台灣年輕人就這樣被野放到陌生的日本街頭。徵召他們的日本政府,早已毫無心力照顧他們。一般的日本徵召工人只要回家就好,但台灣籍的徵召工人要回家可不簡單。他們的故鄉在海的另一頭,海路交通中斷,不知何時才能恢復。但他們精力充沛,不但年輕,還有一大群同伴。在台灣,滿二十歲的男子有服兵役的義務,徵召工則多半是二十歲以下的少年。
「日本政府把我們帶來日本,既然他們不負責,父母給我們的寶貴生命,我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延續下去。」
因為這樣的理由,使得一無所有的他們被拋棄在「自由世界」時,過得非常荒唐。因年輕氣盛而失控的情況也不勝枚舉。理所當然的,世人的責難也全集中在他們身上。
彩琴會提議溜出船艙上甲板,正是因為他們開始唱起不入流的歌曲。年輕女性怎麼有辦法忍受聽那種歌。
「話說回來,他們還真是有精神。」
我這麼說。
「可是啊……。」
彩琴皺起眉頭。
對於他們的合唱,與其說下流,我反而感受到爽朗的力量。那是一股尚未成熟的青春能量。合唱中還參雜著高亢的尖叫聲。
「總之,有精神是好事。」
我一面說,一面傾聽從船艙飄出來的合唱聲。
「那群孩子回國後,不知道有什麼打算……。」
少部分人在日本的「自由世界」所上演的英勇事蹟,彩琴也聽到了。雖然有些加油添醋,但那些行為確實令人搖頭。不過我倒是很樂觀。畢竟胡鬧滋事的只有少數人,絕大部分都是老實的孩子。等到這群人解散,每個人都會各自發揮清新的力量,成為優秀的好青年。
「等他們回到台灣,各自回到自己的故鄉,都會成為村裡的模範青年,可靠得很呢!畢竟他們過過鹹水,還有工作經驗,眼光比較寬廣。將來一定會成為推動台灣進步的巨大力量。」
我為他們辯白道。
以往,離開島上的台灣人不多。這種人被稱為「過鹹水的」(有出國、留學經驗),身分特殊。「過鹹水的」也意指經驗豐富、不可小覷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經過千錘百鍊。不只是徵召工,加上雜務兵、軍隊雇員、志願兵等等,會突然冒出幾十萬個年輕的「過鹹水的」。想必他們會為台灣的將來,貢獻一己之力。
「哎呀,那麼低級的歌,你竟然聽得津津有味。」
彩琴嘲笑我,還帶有一絲責備的口吻。
我們才剛新婚。我們在終戰的隔月結婚,才剛過了半年。
大學畢業後,原本我打算立刻回鄉,父母卻捎信來要我別回去。理由是回台灣會被強制送去當兵,或者被徵召,於是我選擇留在東京就業。隨著戰爭結束,我任職的軍需用品公司也解散了。就在這時,我和女專畢業後無所事事的林彩琴結婚了。這麼做有點魯莽,但我想反正快要回台灣了,只要我們兩人同心協力,短期之內總會有辦法的。
實際上的確熬過來了。戰爭剛結束,物資缺乏。我們靠體力賺生活費,甚至可說是賺太多了。明明是新婚燕爾的夫妻,我們卻每天都非常忙碌。
「這算是我們的蜜月旅行!」
彩琴望著平靜的海面說道。我們曾經一起去鄉下採購糧食兼旅遊,但沒有真正的蜜月旅行,甚至很少有時間好好坐下來聊一聊。
「讓妳有一個貨物般的蜜月,真抱歉。」
我這麼說。聽著引擎的聲音,躺在貨船船艙睡覺,如此的蜜月旅行,肯定會成為難忘的回憶。
「不過,再過不久就會抵達台灣,今天之內就會到。」
彩琴說道。
朝風丸這艘老舊貨船,從宇品開往基隆需要六天的時間。而今天就是第六天。
「四年沒回台灣了。」我喃喃說道。
再過不久就能親眼看到故鄉。我闔上雙眼,試著回想它的模樣。我家位於台北的大稻埕,巷弄雖窄,但那一帶的建築物卻很寬敞。附近有媽祖廟,遇到廟會的日子就熱鬧滾滾。媽祖廟旁邊有間名叫「八仙樓」的餐廳,是四層樓的紅磚建築物。父親時常在那裡招待客戶,我偶爾也會作陪。戰時及戰後的日本,吃不到什麼營養的食物;對故鄉的回憶首先就聯想到食物,說來真是丟臉。回憶起八仙樓的料理,我不由得吞了吞口水。
「我三年沒回去了。」
彩琴說道。三年前,她曾冒著被魚雷轟炸的危險回去台灣一次。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著食物,但她率先提到家鄉的山,想必不像我如此丟人現眼。
「再過不久,就能看見菩薩山了。」
她的娘家位於從台北搭公車約二十分鐘車程的「菩薩庄」,一個座落於菩薩山山腳的村莊。
從我台北的家,可以越過屋頂眺望菩薩山,我也曾搭公車經過菩薩庄好幾次。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將來會和庄長的女兒結婚。
「我想吃八仙樓的雞捲。」
「哇,你一直在想吃的?你真的很貪吃耶!」
「我也在想媽祖廟的廟會。」
「你想的是廟會小吃攤的炸豆沙包吧?」
後來,我們開始聊起故鄉。由於我們在日本結婚,並不認識對方的家庭。彩琴身為媳婦,經常詢問關於我家人的細節,很努力要了解我的家人。至於我,也非常想知道妻子從小到少女時代,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成長。
朝風丸的船頭將海水劃開,激起白色的浪花,然後接二連三將泡沫往後推。我撕開麵包的包裝紙,揉成一團扔進海裡。紙球被風一吹,朝後方橫向飛去。背後是日本,眼前是台灣。我忽然想到,這個無意間的行為是否象徵著什麼,內心忐忑不安。
我聽見了夾雜在船艙合唱歌聲中的引擎聲。
我倚著船舷的扶手,雙眼望向大海,耳朵聽著妻子說話。
彩琴聊到自己的家人時,看起來總是相當開心。由此可以得知,她在一個開朗的家庭中長大。
她的娘家是菩薩庄的富翁,也是大地主。在台灣,只有少數家庭才供得起女兒到東京留學。菩薩庄除了林家,還有姓陸的富人家。陸家也是地主,但規模不如林家那麼大。與其說是富翁,不如說是望族。他們從清朝就開設了「啟志書院」,教導附近孩童念書,陸家代代都是經營私塾。雖然如今私塾早已消失,但陸家主人陸樞堂是畢業於日本大學的知識分子,不愧為文人世家的後代。
林陸兩家因為某個因素,這十幾年來處得不太和睦。然而彩琴卻對陸家人很有好感。從她的談吐中可以得知,她對陸樞堂似乎非常尊敬。我經常聽她提起這號人物。他是一名瘦削高挑的老紳士,乍看很像學者,據說也擅長武術。聽說他每天都會揮舞繫上長繩子的鎖鏈,鎖鏈上還掛著砝碼。
陸樞堂的女兒陸杏和彩琴同年,兩人從小感情就不錯。
「你們兩家人不和睦,假如杏是男人,又和妳湊成一對,就形同羅密歐與茱麗葉了。」
我曾經半開玩笑說過這種話。
結果,彩琴頓時變得一臉嚴肅。
「杏的哥哥和我姊姊就是這樣。」她回答道。
林陸兩家稱不上是反目成仇,而是變得比十年前疏遠。在那之前,同為地方仕紳的兩家人,交流非常頻繁。會變成現在這樣,有個非常明確的原因。
陸家的兒子陸宙從旁慫恿,把當時在東京念大學的彩琴哥哥林景維帶到大陸去。而且,傳言指出他們兩人和上海一帶的抗日組織有密切關係。
由於當時的時空背景,兩名青年成了叛國賊。不只如此,在日軍占領南京後不久,林景維就病死了。這消息一開始只是傳言,但林景維的遺書不曉得用什麼方式轉寄到林家,最後成了不爭的事實。
林景維是長子。家人悲傷欲絕,尤其是母親,傷心到有陣子連家人都束手無策。照彩琴的記憶,她說平常寡言的母親,竟在眾人面前扯開嗓子大喊,有好幾次還說了詛咒陸家的話。
她母親的怒罵,從兒子「被教唆」變成「被殺害」。不用說,兇手當然是陸家的兒子陸宙。「阿宙不如也死了算了!」彩琴的母親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一定是因為她有更年期障礙的關係。」
彩琴說了莫名奇妙的話,為母親辯解。
「應該是遺傳吧?」
我用嘲笑的口吻說道。
「好過分!我有像那樣發過神經嗎?」
彩琴瞪著我。
「沒有,我剛才是開玩笑。」我立刻收回剛才那句話。
「最可憐的是我姊姊珠英。」彩琴摩挲著扶手繼續說,「她喜歡宙哥,結果他不但跑去大陸,還被媽說成殺人犯――我想她一定很難過。姊姊本來就比較內向,不會說出內心的想法……。」
「妳姊姊現在幾歲了?」
「二十七。」
「十年前,就是十七歲吧?」
「對呀。」
「看來早熟也是林家的血統?」
「討厭!」
彩琴又瞪了我。只不過,她這次瞪我的方式,帶有一絲溫柔。
「不過,事情變成這樣,陸宙或許也會回台灣呢!」
我這麼說。
戰爭結束了,台灣回歸中國。過去的謀反者,這下子全成了英雄。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領土,陸宙很有可能會回來。
「如果真是這樣就好了。」彩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水平線,「可是,不曉得宙哥還是不是單身?他應該已經三十三或三十四歲了……珠英還沒結婚就是了。」
船艙的合唱終於結束了,只聽見引擎和浪花的聲音。
「戰爭這玩意兒……。」
我不由得嘟囔道,但話說到一半就停下了。戰爭殘酷地玩弄了人類的命運,在船艙裡的兩百名年輕人,不也是戰爭的犧牲者之一嗎?
戰爭摧毀了好幾百萬人的愛,傷口仍在隱隱作痛。若是能夠癒合的傷口,那還算慶幸。但有些傷口是永遠敞開的,再也無法痊癒……溫熱的鮮血,不斷自傷口淌出――想到這裡,此刻的心情無法言喻。
我沉浸在傷感當中,彩琴似乎在這時說了什麼話,而我沒有專心聽。
「呃?妳說什麼?」
我問道。妻子發現她特地向我搭話,我卻沒有聽進去,頓時露出不悅的表情。
「我說珠英人不可貌相,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
「哦,原來是這樣。」我答腔,「妳好像很崇拜姊姊。不曉得她是怎樣的人,將來總有機會和她碰面,我很期待。」
表面上,我完全不認識妻子的家人,其實我知道彩琴姊姊林珠英這號人物。她和我同年,我就讀中學時,她也在台北的女校念書。據說她是個大美女,說到林珠英這個名字,在台北中學生之間可是赫赫有名。知道歸知道,也不過是她走在路上時,頑皮的朋友小聲對我說:「你看,那人就是X高女的林珠英喔!」因此我記得她的長相,如此而已。她果然是個如假包換的美人胚子,我在內心讚嘆不已。
直到結婚後,我才知道妻子是林珠英的妹妹。妻子給我看照片,指著上頭的女性說這是她的姊姊,我才認出對方就是當年那個X高女的林珠英。
當然,林珠英不可能認識我,因此我也沒有對妻子提過這件事。過去我曾經偷看妳的姊姊,讚嘆她的美貌,向妻子坦白這些事是否妥當?我們才剛結婚,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拿捏分寸。
「我好喜歡姊姊。」
彩琴說道。
「看照片的印象,她好像是個美女。」
我不經意地提起這件事。
「對呀!」彩琴亢奮地說,「有數不清的人來說媒,姊姊全都回絕了。媽哭著哀求她結婚,可是珠英說什麼也不肯聽話,所以我才說她很堅貞。」
「不過,二十七歲的女人,也算是有一點年紀了。」
「我想她一定是忘不了宙哥。」
「問題是已經過了十年耶?」
「十年……。」
說到這裡,彩琴嘆了一口氣。
十年真的是一段漫長的歲月。
「假如陸宙從重慶回台,那就皆大歡喜了。」
我回應道。
「是啊……但是問題在媽身上。在媽看來,宙哥就是殺了兒子的凶手啊……。」
「好棘手啊。」
「真的很棘手。況且,宙哥是男人,不太可能還是單身吧……。」
彩琴按著被風吹亂的頭髮,表情非常嚴肅。有句話說西施顰眉人更美,彩琴也是愈憂愁愈凸顯她的美貌。
之後,我們聊了很多。我有事先寫信回家,但戰後郵務尚未步上正軌,恐怕還沒有寄達台灣。忽然跑回家,大家一定會很驚訝――我們就是在聊這些。
我彷彿可以看到父母露出又驚又喜的表情,尤其是母親,肯定會喜極而泣吧?彩琴似乎也想著類似的事。只不過,出現在我腦海裡的,是大稻埕後面狹窄髒亂的小巷子,而她想的肯定是菩薩庄充滿綠意的田園景色。
理所當然的,我們夫妻會先回我家。我明白彩琴很想趕快回菩薩庄的娘家,於是我們商量,不如在抵達的隔天,兩人一起回去。
「畢竟吉田太太還委託我們辦事。」
我這麼說。
我們在東京的鄰居吉田太太,託我們帶信回台灣。吉田太太的親哥哥是一位姓川崎的陸軍少佐,人在台灣。她在復員省打聽到,終戰時川崎少佐人在林尾飛行場的部隊,而林尾就在菩薩庄附近。說不定川崎少佐早已被遣返回國,我們有可能與他擦身而過。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還是必須跑這一趟……。
甲板上還有許多年輕的徵召工。過了一會兒,他們那裡忽然響起了歡呼聲。
「是台灣!看見台灣了!」
我凝視著大海遙遠的另一端。可惜我近視很深,什麼也看不見。
「看得見嗎?」
我問了妻子,她的視力很好。
「水平線上面,隱約可以看見淺灰色的點。」妻子答道。
船駛進基隆港前,靠近我的前方似乎有座小島。水平線上的那點灰色到底是小島,還是台灣本島的影子?我分辨不出。總歸一句話,那確實是和「我的故鄉」相連的東西。
甲板響起的歡呼聲引來了人群。眼看右舷已經擠滿了人,且幾乎都是年輕的同胞。我們夫妻在年輕人體味的包圍下,不由得緊握住對方的手。
「台灣!是台灣!」
不久,他們互相摟住彼此的肩膀,開始唱起台灣具代表性的民謠《雨夜花》。
連我也看見了灰色的點。顏色愈變愈深,體積愈變愈大。我注視著那個點,久久無法將視線移開。
「啊,吹來的風已經聞不到海潮味,而是台灣的味道……。」
彩琴在我耳邊輕聲說道。
朝風丸
船內的大合唱一旦開始便停不下來,少說要一小時後才會停止。
我和妻子彩琴一起來到甲板。
「好舒服喔!」
妻子深深將海風吸滿胸膛後說道。
我靜靜點頭附和。
兩千三百噸的「朝風丸」雖然是一艘老舊的貨船,卻也是一艘幸運的船。大有來頭的商船接二連三成為魚雷和轟炸機的目標,沉入太平洋海底;但朝風丸卻沒有絲毫損傷,幸運存活下來並成為忙碌的遣返船。
朝風丸駛離宇品港,朝台灣的基隆港前進。它承接了將在台日本軍民撤返日本的業務,去程則搭載了在日台灣人。這趟航程也有三百多名台灣人搭乘。由於它是貨船,沒有客房,...
推薦序
再見陳舜臣——概論陳舜臣推理文學
路那(推理評論家)
所謂記憶,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本人認為是最古老的回憶,很有可能出乎意料的新。而你認為是後來發生的事,反而很有可能是舊的回憶。——陳舜臣,《青雲之軸》,29頁。
記憶的形成,若非出於反覆的回想,便是源於事件所帶來的、讓人難以忘懷的體驗。陳舜臣爬上神桌,對著神明喃喃自語的「神桌」事件,即是兩者兼具,但若只源於其中一種,記憶時常只剩下「啊……那時候好像有這件事。」
對於「陳舜臣」這個名字,我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已經記不得我讀的第一部陳舜臣作品,到底是屬於歷史小說的《諸葛孔明》,亦或是屬於推理小說的《枯草之根》了。我只記得,當年看完《諸葛孔明》所受的衝擊——我深深地著迷於這個作家的人物塑造、敘事手法、解釋事物的方式,甚至是標點符號的使用。之後,我有好一陣子很努力地到處找他的作品來看。然而小學生不耐久候,而且當年的我實在很害怕像是「鴉片戰爭」、「甲午戰爭」這種聽起來就充滿了國仇家恨、血淚歷史的字眼。於是一眨眼,二十多年過去了。陳舜臣的小說就這樣,一直放在我的書架上。直到某日我進了偵探書屋,和譚端、思宇認識,這才回過頭來仔細地端詳書架上的小說。然後開始疑惑,過去的二十幾年間,我為什麼沒有早點發現陳舜臣原來是這麼有趣的一個人呢?
Who is 陳舜臣?
生於1924年的陳舜臣,與我奶奶是同輩的人。雖然祖籍在新莊,但父親和祖父在他出生之前已然移居神戶,他是在神戶出生的。
陳舜臣的祖父,不消說是成長於清朝。透過熟習漢學的祖父,陳舜臣接受了以台語為載體的漢學教育。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地籍的內地居留者,陳舜臣與當時的本島青年一樣,勢必得進入現代化的教育系統。身處台日兩種文化的夾縫中,在接受文化精華之餘,也不免對自身的認同抱持著疑問。從祖父被歧視的「花店事件」,到令陳舜臣不再貪看船艦的「閱兵事件」,隨著他人差別目光的浮現,陳舜臣逐步意識到箇中意義,「認同」此一看似飄渺無依的名詞,遂緩緩地轉化為實存的情境。
正是在這樣的煩惱下,陳舜臣進入了大阪外國語學校(今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的印度語學科就學。雖然本人曾開玩笑般地說過念印度語是因為「比較好考」的關係,但大阪外國語學校也設有中文科,若純以難易度來考量,對華僑子弟陳舜臣而言,中文科應該是最簡單的。因此,比起「好考」,我想,「會中文又會印度文的話,就能和世界上一半的人溝通了」以及「同為殖民地人,想了解印度人的觀點」這兩個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貨真價實地出現在青年陳舜臣的思考中的。而構成此一理由的基礎,並非偉人傳記中常見的矯飾,而是青年面對該將己身立於世間何種位置的切身苦惱。
對青年陳舜臣來說,不幸的是,本已在學術中找到位置的自己,在命運的操弄下,又被拋回苦惱之中。二戰結束後,保住了性命的陳舜臣,因為身為殖民地出身的台灣人,面臨國籍轉換的問題,最終失去了在日本從事學術工作的機會。以此為契機,陳舜臣曾在1946年與弟弟敏臣短暫地返回新莊。陳舜臣在新莊初級中學擔任英文老師,而陳敏臣則考取公費到大陸留學。從《半路上》的記述中,可看出陳舜臣不是沒有想過在台灣繼續他的研究。然而,命運再次地反臉無情。隨著中國內戰不止,以及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兄弟倆最終仍雙雙回到了神戶。
正是這樣的經歷,讓陳舜臣無法停止對於認同問題的思索。我是誰?我要往何處去?此一青年時期個體必然遭遇的大哉問,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初初萌芽時期曾經發出的稚嫩呼喊,即便到了此時,依然不存在一個最終的解答。
約莫十年後,蝴蝶破蛹而出。在看護生病女兒的過程中,陳舜臣因讀了《錢形平次捕物帖》,而和S.S.范達因(S. S. Van Dine)、克勞夫茲(Freeman Wills Crofts)這些不幸曾因臥病在床而大量閱讀推理小說的推理作家,有了類似的感想——「這種程度的作品,我自己應該也能寫得出來吧。」
於是,我們有了講述放高利貸華僑之死的推理小說《枯草之根》,以及風格獨樹一幟的華僑偵探陶展文。寫於1961年的《枯草之根》為第七屆江戶川亂步賞得獎作品,當時被木木高太郎譽為「即便在歷屆的亂步賞作品中,都是第一的佳作」,此作也入圍了隔年的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雖然最終止步於候補階段,但也隱然顯現了此一新銳作家的驚人氣勢。而從此部作品中,亦可窺見陳舜臣對他從童年時期就不斷遭遇到的認同課題所給出的回答——懷抱著高度地方意識的同時,從亞細亞出發、以世界主義為胸懷。這樣的思想,可說幾乎貫穿了他日後的所有創作。
新苗破土而出:創作之路
在以《枯草之根》出道後,陳舜臣陸續發表了《三色之家》、《憤怒的菩薩》、《托月之海》、《黑色喜瑪拉雅》(黒いヒマラヤ)、《逝去的桃花源》(桃源遥かなり)、《神戶這個城市》(神戸というまち)、《焚畫》(炎に絵を)等作品。從這批早期作品中,其實就能窺見陳舜臣「從神戶到亞洲」、「化歷史為謎團」,以及轉化自身生活經驗的書寫姿態。
1969年,陳舜臣以《青玉獅子香爐》獲得第六十回的直木賞,為繼邱永漢後第二個獲得此獎的在日台灣人作家。獲得直木賞的隔年,陳舜臣以《再見玉嶺》和《孔雀之道》兩作並列獲獎的形式,終於在第五次入圍時奪得了第二十三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在拿到「推理作家協會賞」後,陳舜臣摘下了「三冠王」的稱呼。在1970年創下的此一成就,在當時的文壇可說前無古人。一直要到桐野夏生在1999年、東野圭吾在2005年獲得直木賞,才有第二位與第三位「三冠王」的誕生。此後,他獲獎無數。1971年以《鴉片戰爭》獲「每日出版文化賞」、1974年獲神戶市文化獎、1976年以《敦煌之旅》獲以獎勵散文為主的「大佛次郎賞」……。最終,在1992年,日本政府有鑑於陳舜臣的文藝成就,頒給他勳三等瑞寶章。
綜觀陳舜臣的各類作品,可以發現其創作的幾個特點。最明顯的,應該就是異族雜居、戰爭與貿易等元素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參照作家的人生經歷,則不難明白根源從何而來。此點也表現在其歷史小說創作的面向上。從諸葛孔明到馬可孛羅,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戰爭、貿易與流動均為小說家關注的焦點。然而,有異於普遍將「流動」直接視為「流離」的觀點,陳舜臣通常是以「此心安處是吾鄉」、「日久他鄉是故鄉」的角度,正面地看待這些流動經驗,讓角色從這些經驗中獲得立身之所。同樣地,陳舜臣也不受傳統士大夫觀念的影響,並未對貿易抱持鄙夷的態度,而是將之視為社會活動的一環、新觀念進入的支點,以及引發時代大事件的起源。這並非表示陳舜臣的小說中不存在商業的黑暗面,而是說他會更細緻地區別一般商業活動與惡質商業活動之間的分野。最後,則是較少被提出的一個元素,由於陳舜臣的作品時常以戰爭作為背景,「間諜」與間諜活動在許多作品中,其實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憤怒的菩薩》正好包含了以上三點。
憤怒的菩薩
《憤怒的菩薩》描述在日台灣人楊輝銘與新婚妻子林彩琴,在二戰結束後半年多搭船回台灣。陪妻子回娘家的楊輝銘,在妻子故鄉「菩薩庄」,碰上妻子家族裡一連串令人驚訝的變化,最終捲入菩薩山上發生的「準密室殺人」事件。成為第一發現人的楊輝銘,開始了追兇的旅程。
陳舜臣的作品,雖曾在90年代經由遠流出版社引進,而成為一代人的共通記憶,但極為可惜的是,出於未知的原因,以台灣為背景的本作未曾出版,其「台裔/台籍」的身分,在當時台灣學仍奮力爭取主流認同的年代,尚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由於陳舜臣一度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他的著作在台灣甚至曾被列為禁書。因此,在其創作巔峰、頻頻得獎的70、80年代,我們對於這樣一位優秀的作家近乎一無所知。
往者已矣。來者雖然遲了些,也總好過不來。本次的中譯,選擇了陳舜臣的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自傳《半路上》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作為三部曲,在文類各異的情況下,出版目的也就不外乎是藉此讓台灣的讀者更加認識陳舜臣與他作為「在日台裔」的經歷,以及由其視角反觀席捲東亞的二戰與戰後經驗了。對於陳舜臣而言,比起自傳,他或許更能夠自由地藉著相隔了一段距離的小說人物,來表達他自身的情感經驗吧。畢竟,在《青雲之軸》中,作家本人曾這樣說道:
我終於發現,正是因為要寫「自傳小說」,所以文筆才會停滯不前。既然如此,那我就改寫「自傳性小說」吧。
(中略)
加進一個「性」字之後,我總算能鬆一口氣了。這麼一來,終於能夠比較輕鬆地創作了。
如果僅是「自傳」與「自傳性」的差別,就能讓陳舜臣從揉碎眾多稿紙到回復正常的寫作狀態,那麼全然虛構的小說,是否能讓他更為自在地回溯那一段時間雖短,卻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莊年代呢?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這大概也是《憤怒的菩薩》比《青雲之軸》與《半路上》要更早成書的原因吧。而儘管陳舜臣在設定陶展文與展開寫作之時,即已融入己身經歷,然而在本作中,那樣的融合可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便是在處理充滿激情的場面,陳舜臣的筆鋒亦常予人悠然淡遠之感。但在本作中,敘事者的情感卻多少衝破了那樣的筆法,而顯得格外醒目。若搭配日後的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與自傳《半路上》來看,當更能體會作者本人當時的經歷,是如何撼動了他的人生。這樣的震動,在倏忽一甲子後的現在,終於能夠藉由翻譯傳遞到我們的心裡。然而,我們是否準備好去真正撫平那樣的愴痛了呢?
近日,因陳舜臣而多次走訪新莊,試圖查訪出文本裡的標誌性地景。啟志書院就是明志書院應無疑義,但在小說中被主人公嫌棄過於華麗的祖師廟原型,是頂泰山巖還是下泰山巖?迎雲寺的原型,是山腳的西雲寺還是山頂的凌雲寺?交互比對著老相片與百年地圖的同時,前方觀音山如同千百年來一般悠然佇立。抬頭遠望,為此一風景而心生家鄉之愛的同時,一個疑問也突然擊中我——都說是「憤怒的菩薩」,但,翻遍全書,我卻還是無法釐清菩薩為何憤怒。
菩薩為何憤怒?
或者說,憤怒的,是菩薩嗎?
再見陳舜臣——概論陳舜臣推理文學
路那(推理評論家)
所謂記憶,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本人認為是最古老的回憶,很有可能出乎意料的新。而你認為是後來發生的事,反而很有可能是舊的回憶。——陳舜臣,《青雲之軸》,29頁。
記憶的形成,若非出於反覆的回想,便是源於事件所帶來的、讓人難以忘懷的體驗。陳舜臣爬上神桌,對著神明喃喃自語的「神桌」事件,即是兩者兼具,但若只源於其中一種,記憶時常只剩下「啊……那時候好像有這件事。」
對於「陳舜臣」這個名字,我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已經記不得我讀的第一部陳舜臣作品,...
目錄
【出版緣起】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陳思宇
【導讀】再見陳舜臣——概論陳舜臣推理文學╱路那
序章
朝風丸
歸鄉
回門
逛寺廟
軍人們
復活的男子
衝破黑暗的影子
槍聲
搜山
兩輛腳踏車
回家
再次陷入混亂
另一人復活了
迎雲寺會議
善後
落幕
三把鏟子
尾聲
【解說】菩薩為何憤怒?╱路那
【出版緣起】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陳思宇
【導讀】再見陳舜臣——概論陳舜臣推理文學╱路那
序章
朝風丸
歸鄉
回門
逛寺廟
軍人們
復活的男子
衝破黑暗的影子
槍聲
搜山
兩輛腳踏車
回家
再次陷入混亂
另一人復活了
迎雲寺會議
善後
落幕
三把鏟子
尾聲
【解說】菩薩為何憤怒?╱路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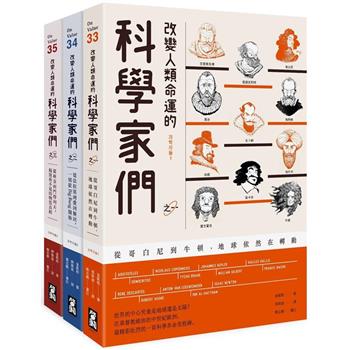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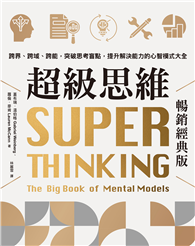



光讀小說,一點都看不出那邊憤怒. 感覺整本書最憤怒的是小說結束後附錄的推理評論家路那的解說. 路那在書前書末各有一篇文章介紹陳舜臣,很怕讀者不了解,實際上也是,沒有這些對陳舜臣背景的解說,光看小說根本感覺不到陳舜臣憤怒在那邊. 小說背景是發生在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但還沒發生後來的228事件之前,主角是一個從日本歸國的溫和好青年,有趣的是,刻板印象中那個時代的軍人(戰敗等待遣返的日本軍人,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軍人),在作者筆下都溫和善良值得尊敬許多(刻板印象是日本軍人很兇惡但自律且缺乏獨立自信,國黨軍人粗野但無所不為),作者筆下的人大體都是善良的,就算是壞人,他也有給他一些正面的認同。 這點讓我頗為欣賞。或許如路那介紹說的,陳舜臣因228之後遠走日本,再不回台灣,他對228顯然是有憤怒的,可是小說裡完全沒有藉勢(作者本身就是小說中最大的勢)藉端去醜化或惡化國黨軍人,有的只是政治轉移下人的無奈,若說有一點點有情緒的描寫,反而是寫到汪精衛的老婆受審時的剛毅與清明。 沒有刻意醜化什麼,抬舉的只有人的善。但無聲的控訴已在其中。原來菩薩的憤怒是這樣的. 溫柔有情,我覺得是很好看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