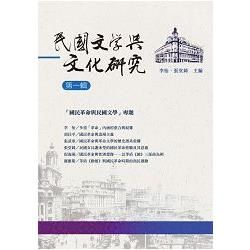「國民革命與民國文學」專題
李 怡/多重「革命」內涵的重合與混雜
胡昌平/國民革命與浪漫主義
張武軍/國民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歷史譜系重構
張堂錡/民國女兵謝冰瑩的國民革命經驗及其意義
倪海燕/國民革命與性別想像--以茅盾《蝕》三部曲為例
羅維斯/茅盾《動搖》與國民革命時期的商民運動華人世界第一份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開啟重返民國歷史現場的文學研究運動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為新創辦的學術叢書,從二○一五年末開始出版,本書為第一輯,預計每半年出版一冊。刊物由李怡、張堂錡兩人主編。
本輯推出「國民革命與民國文學」專題,特別收錄胡昌平、張武軍、倪海燕、羅維斯等多位博士各具觀點的精彩論文。
並且,為使讀者可以了解「民國文學」研究的發展歷史脈絡,「經典重刊」專欄收錄最早提出「民國文學」設想與最早倡導「民國文學」研究理論的陳福康與張福貴兩位教授的文章。
更有四篇分別來自台灣、大陸、日本、澳大利亞的四位作者,提出新方法與視角的論文。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創辦,是為了提倡一種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進行文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堅持學術立場、文學本位、開放思想則是本刊的宗旨。我們認為,在「民國框架」下討論問題,不僅可以積累一批被忽略的史料,而且最終也有助於形成與現代漢語文學相適應的研究思路和學術模式,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歐美學術範式的宿命,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對話。
「民國文學」作為一個學樹的生長點,其意義與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肯定。現代文學的研究,在經過早期對「現代性」的思索與追求之後,發展到對「民國性」的探討與深究,應該說也是符合現代文學史發展規律的一次深化與超越。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深信,學術界將可以在這方面開展更多的合作機制與對話空間。
本書特色
√ 是華人世界第一份有關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 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堂錡、北京師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怡共同主編。
√ 透過這份刊物,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發展與突破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和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