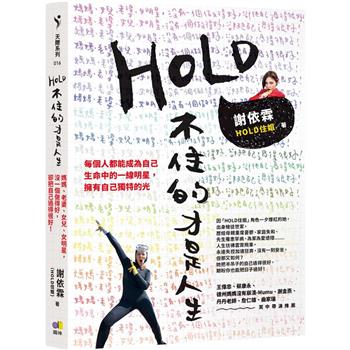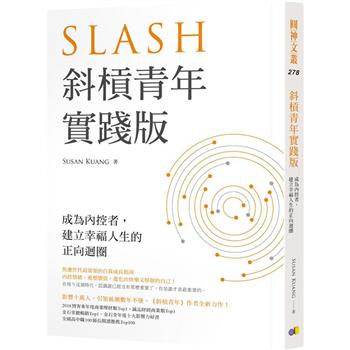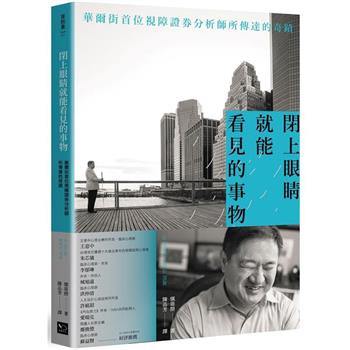穿越禁錮的厚重門窗,
訴說生命裡的返照時光。
訴說生命裡的返照時光。
落入國民黨手中的中共領袖,歷經逃亡、圍補、審訊、勸降,
在命運的盡頭前,他提起了筆長談,那是最後的──多餘的話。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是繼陳獨秀之後第二個被共產國際打倒的中共領袖人物。《多餘的話》是他於一九三五年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後在獄中寫下的反思錄。這篇反思錄不過是對其棄文從政給自己所帶來的惡果感到痛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這一作品卻被當作變節書,即宣佈其為叛徒,其妻子也慘遭逮捕、迫害致死。雖然後來瞿秋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他的這篇遺作仍然成為了他的一個軟肋,不能為人正視面對,至少不可能如另一紅軍將領方志敏的獄中遺作那樣廣為傳誦。
本書收入了目前能見到的瞿氏在獄中的全部遺稿,還編入了當年記者獲准對囚禁中的他進行採訪的記錄,國民黨軍圍捕他時所發電報,當局對他進行審訊、勸降等檔案材料,以及諸多見證者的回憶文章等等。本書是《多餘的話》最完善的版本,也是瞿案最為詳實的原始資料集。
本書特色
1.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瞿秋白的遺作,敘說民國初期共產黨成型期的經歷。
2.收錄大量相關資料,包括瞿秋白的創作詩詞、訪談紀錄、審問資料、相關人員的回憶錄等。
3.文本與注釋資料詳實,同時佐有圖片,具有保存重要史料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