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種種還原
黃文倩 2016/4/13
《光合作用》是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詩作合集,分成二部分,輯ㄧ為由詩社幹部評選的公開徵選作品,輯二是歷屆詩刊的代表作,選錄的標準及最終的結果,均由詩社成員自主運作、擇定,若逢爭議,亦兼採對話與討論,因此雖然作為一個大學級的詩社,但與其說「微光」跟進的是學院派近百年文學史上的詩歌典律,不如體現的更多是自身世代的主體特色,尤以90年代出生者為核心(例如「微光」的歷屆社長的出生年份為:第一屆洪崇德1988、第二屆曾貴麟1991、第三屆許雅筑1994、第四屆曹馭博1994、第五屆林佑霖1995)。
90年代所開啟的又什麼樣的時代與世代?在政治上是台灣解嚴(1987-),在思潮上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構主義,從史學上來說有新歷史主義的轉向,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則是所謂的「眾聲喧嘩」。他們一開始就在一片相對前輩世代更寬鬆的政治與教育體制下成長,但卻也被迫得承擔台灣經濟開始長期停滯的現實,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生、長大的以至於過渡到21世紀初期的文藝青年,儘管對本土與島國有著更多的自覺認同,對社會也有更直接的懷疑審問,對自身的存在,有著更理直氣壯的幻化與想像的回應方式。閱讀他/她們的作品,時常讓我聯想到昔日當我更年少時,恐怕也並未有他們自覺到的視野的許多部分。
我揣想本書以《光合作用》命名,一方面自然是刻意的詩化,二方面或許也不無表現「微光」渴望在有光的作用下拔高、成長的存在狀態與日漸飽滿化的感情認識。同時,與許多已成名與出師的豐富與複雜的作家相比,「微光」們階段性所體現出來的許多思考和美學上的實驗焦慮,我以為更為可貴,例如將「想像」的視野,以素樸自然的文字,聯繫上善意、信任與懷念,如〈想像〉(楊沛容):「想像真誠都寫進了等待/想像這個冬天是上一個冬天/想像你回頭望了幾眼/再一路走遠」,還有〈影子〉(邱伊辰):「作為一名影子我只能/學習在你身上沉默/學習如何不弄濕你的衣裳/……在你背上/學習成為最輕薄的所有」,願意相信別人的可能的溫暖,願將自身放輕,弱化對他者的負荷,在這個時代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品格。例如體現一種清醒的現代知性與自我反省的品格,如〈上周末的遺書〉(曹馭博):「你沒我那麼習慣/一絲不苟,或者/搪塞。/星期六/待在家裡也會迷路/……/你並不愛說謊,只是擔心/記憶有不在場證明。」馭博日後肯定會再繼續進步。例如揣摩與自身相異的性別及成人精神秘密世界的一角,如〈海岸是妳唯一的告別〉(李冠緯):「將那些遠去的日子/煮成沸騰的煙服下/填充自己」,昔日的沸騰之於成人既是一種安慰,但如煙的填充終究是虛的,冠緯的瞬間悟性時常令我印象深刻。又例如〈異邦〉記《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林佑霖),藉由一種異邦革命的視覺淵源滋養自身:「用眼睛交換眼睛/用鮮血交換鮮血/你想像中的異邦/有了一條真實的路」你或許也開始靠近/懂得虛實相生的辯證關係。
當然有些題材越出了較個人、自我的範圍後,對「微光」的詩人們來說,處理的難度確實較高,例如〈把月亮忘在動物園屋頂〉(鄭安淳),在「重擊土地/再度開自己的花」之前,無論是將自身定位在一個浪漫派或現實主義的創作者,我們在感性和靈性上所需作出的準備,有時會比我們想像來的漫長,有些世界難以透過理性或知性靠近,緩慢地消化混沌並從中自然生產出悟性,需要機緣與等待。至於〈線,在折行與滑行〉(Lalilu)是老靈魂對「美」的堅持:「明天我們再見吧/你依然穿著剪裁合身的折線/只有我知道它們已經老了/……一件又一件絲質外套/滑過交換過花的痕跡/一次又一次我希望痕跡/能把一切阻止」,我很喜歡。願作者此生都能記住,自己確實曾有過如此純粹信仰「文學」與「美」的階段。
而略長於90世代的80後的「微光」創社社長的洪崇德,在詩作的格局與視野,顯然對自我要求更高,〈我要問你公理與正義的問題〉仿擬楊牧的名作,但勇於帶出的是晚近台灣22K世代的新視野和困惑,對知識分子的質疑,處理的相當敏銳,對發達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亦有非媚俗的直覺詩化理解:「怎樣的水平才足以參與社會/且不讓知識的有無成為體制下/新的階級和暴力?/……假如渺小的此刻你放棄提問/假如在保安大隊的盾牆裡你發盡所有的聲音──/卻不能占領一個鏡頭」,希望崇德日後繼續追問「然後呢」?
我一向不認為自己有資格能作「微光」的「指導」,陪他們一起讀書和理解生活與生命,更接近我日常的實踐。中文系殷善培主任偶爾好調侃我,說從社員到老師,「微光」和讀書會的成員們都是瘋子,我願意善意地理解他的判斷,並以為這是我們對目前俗世與平庸的現實的一種抗衡,在廣義的美與詩意的文藝的召喚與漫遊下,我們不過嘗試想還原回種種真正意義上的全人。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光合作用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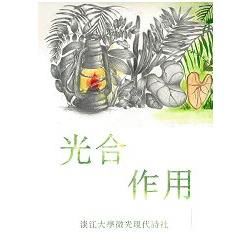 |
光合作用 作者: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 出版社: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50 |
中文書 |
$ 158 |
詩 |
$ 176 |
現代詩 |
$ 180 |
華文現代詩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光合作用
<內容大綱>
光合作用是由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所出版的作品合輯,其中收錄歷屆社員的
作品。書名取為光合作用,除了延續微光現代詩社的宗旨「僅僅是這樣渺小的
微光,便足以照亮整個黑夜。」,也傳達在光的滋潤下,我們要以詩創造自己
的光合作用。
本書特色:
《光合作用》是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詩作合集,分成二部分,輯ㄧ為由詩社幹部評選的公開徵選作品,輯二是歷屆詩刊的代表作,選錄的標準及最終的結果,均由詩社成員自主運作、擇定,若逢爭議,亦兼採對話與討論,因此雖然作為一個大學級的詩社,但與其說「微光」跟進的是學院派近百年文學史上的詩歌典律,不如體現的更多是自身世代的主體特色,
作者簡介:
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的歷屆成員
TOP
推薦序
代序:種種還原
黃文倩 2016/4/13
《光合作用》是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詩作合集,分成二部分,輯ㄧ為由詩社幹部評選的公開徵選作品,輯二是歷屆詩刊的代表作,選錄的標準及最終的結果,均由詩社成員自主運作、擇定,若逢爭議,亦兼採對話與討論,因此雖然作為一個大學級的詩社,但與其說「微光」跟進的是學院派近百年文學史上的詩歌典律,不如體現的更多是自身世代的主體特色,尤以90年代出生者為核心(例如「微光」的歷屆社長的出生年份為:第一屆洪崇德1988、第二屆曾貴麟1991、第三屆許雅筑1994、第四屆曹馭博1...
黃文倩 2016/4/13
《光合作用》是淡江大學微光現代詩社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詩作合集,分成二部分,輯ㄧ為由詩社幹部評選的公開徵選作品,輯二是歷屆詩刊的代表作,選錄的標準及最終的結果,均由詩社成員自主運作、擇定,若逢爭議,亦兼採對話與討論,因此雖然作為一個大學級的詩社,但與其說「微光」跟進的是學院派近百年文學史上的詩歌典律,不如體現的更多是自身世代的主體特色,尤以90年代出生者為核心(例如「微光」的歷屆社長的出生年份為:第一屆洪崇德1988、第二屆曾貴麟1991、第三屆許雅筑1994、第四屆曹馭博1...
»看全部
TOP
目錄
代序:種種還原
輯一 1
〈她今年才十六歲〉楊沛容 2
〈那些找不到愛情的夢遊者〉吳貞慧 4
〈為你,寫一首宇宙〉吳貞慧 6
〈宮燈姐姐〉楊沛容 8
〈想像〉楊沛容 10
〈種種生活〉吳貞慧 12
〈上周末的遺書〉曹馭博 13
〈大霧之內〉林佑霖 15
〈小丑〉陳皓臻 ...
輯一 1
〈她今年才十六歲〉楊沛容 2
〈那些找不到愛情的夢遊者〉吳貞慧 4
〈為你,寫一首宇宙〉吳貞慧 6
〈宮燈姐姐〉楊沛容 8
〈想像〉楊沛容 10
〈種種生活〉吳貞慧 12
〈上周末的遺書〉曹馭博 13
〈大霧之內〉林佑霖 15
〈小丑〉陳皓臻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淡江大學微光新現代詩社
- 出版社: 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08 ISBN/ISSN:978986924617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28頁 開數:32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