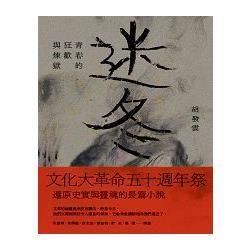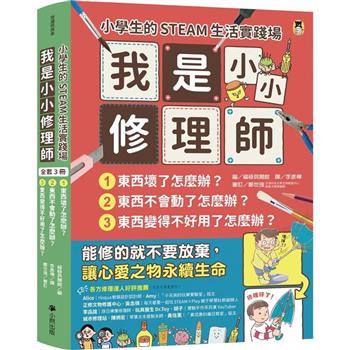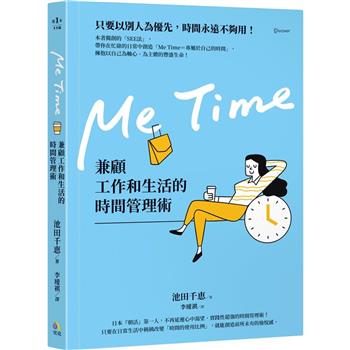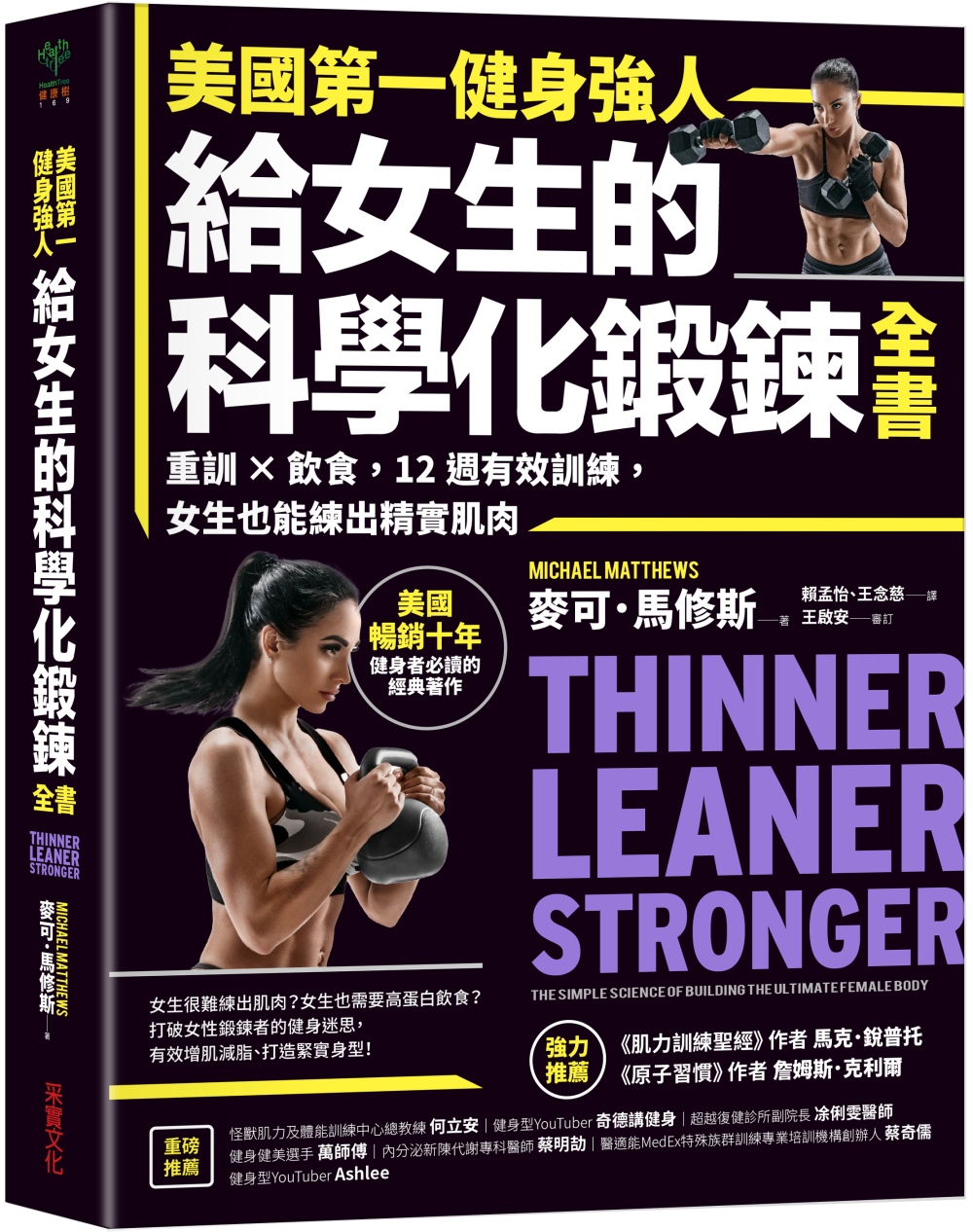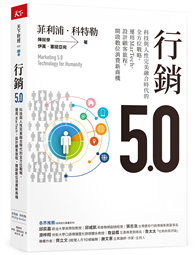名人推薦:
各界讚譽:
朱嘉明|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客座教授 專文推薦
「文革顯現了中國式政治和權利的「虛無主義」本質。後來,這種虛無主義引發了一種彌漫性犬儒主義,不再相信理想和義正言辭的真實性,拒絕發出正義要求和呼喊,甚至否定內心深處的良知存在。」
朱學勤|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文革之禍不僅在於它的發動與過程,也在於它的最終結局:官僚特權階層成為勝利者。由此形成的官方話語,反映更多的是勝利者對社會記憶的裁剪與禁忌。
胡發雲也否定文革,但他突破了官方禁忌,盡可能還原被禁忌的社會記憶。因此,他的《迷冬》既可以當小說讀,也可以當歷史讀。只有允許還原,文革才能真正否定,只有還原真相,否定才經得起歷史檢驗。
徐友漁|美國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
本書真實地再現了在那苦悶、壓抑的年代一群少男少女的純真追求,彼此的關愛和友情,說明人是弱小的,但人性是強大和無法扼殺的。邪惡可能壓抑人性,但無法摧毀人性。
章詒和|作家
整整五十年過去,文革已凝固為「記憶」,少有人議論,少有人書寫。當生活開始舒適起來的國人打算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突然發現「記憶」已劃為禁區。在這種情勢下,胡發雲的寫作就非常值得稱讚和敬佩。
文革代表著鬥爭、恐懼、背叛、冷酷與極端;青春意味著激情、戀愛、浪漫、迷茫與夢想。《迷冬》把兩者糾纏在一起,用文學的方式在音樂的烘染下把那個特殊時期的人與事,呈現給世人,金石滾滾,意氣翩翩。它讓我一次次體會曾經的緊張和慌亂,感受痛苦的觸動和衝擊。
野 夫|作家
胡發雲兄之大著《迷冬》,以親身見聞及經歷為素材,用冷峻筆法及深刻反思,塑造了一群既普通又經典的人物。並以他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命運遭際,深刻揭示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之本質真相……值此文革暴發五十週年之際,世道輪迴,當日危情險象隱若重現。也許細讀本書,或可從中檢討民族厄運之來龍去脈,並警示當下民衆前途之吉凶難卜。
◇各界讚譽
「一部揭示『文革』核心真相的活史詩!」----龔道軍(作家)
「小說對人物體驗的挖掘可謂細緻入微。不但重現了一代人扭曲的心靈史,也重現了一代人辛酸的藝術史。」----邢小群(刊於《江南週報》)
「作者凝聚了全部心血對於那場『大革命』的痛徹反思。」----郭于華(刊於《經濟觀察報》)
「撕開文革帷幕後的隱秘面紗,在撲朔迷離雲遮霧罩的迷惘中探尋人性的扭曲程度。」----李磊(刊於《文匯讀書週報》)
「以一個正直的作家的良心良知,以及道德勇氣,秉筆直書,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值得讀者細閱深思。」----〈舒心書評:《迷冬》〉
◇讀者好評迴響
「文革、武漢、青春、音樂,織就了一部大氣磅礴的史詩序曲!」
「寫那個時代的乖謬與錯亂,卻擺脫了知識分子苦大仇深的慣常敘述角度。」
「革命與愛情,總有它們的迷人之處。」
「用音樂,用舞蹈,無形的音樂和肢體的綻放,寫就了青春的狂歡和煉獄。」
「一代人在那特殊年代的特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