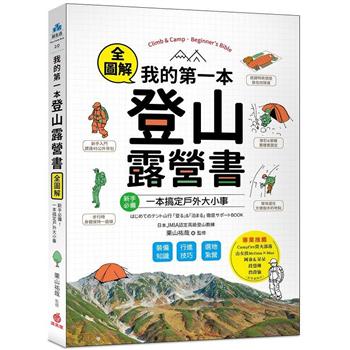英國脫歐,川普崛起
「極右派」狂潮襲來,世界將何去何從?
將種族主義描述為「瘋狂」當然很容易,把種族主義者稱為「暴徒」也無助於真正理解。
來自英國的第一手報導,體驗仇恨政治,直視極右派!
本書中,作者白曉紅觀察與追蹤英國極右派的街頭運動與組織,跟隨著其中成員,拼湊其生活背景、環境影響。有別於媒體非黑即白的報導,《憤怒的白人》探討他們的動機、政治策略、目標與社會影響。
在全球化時代,這是每個人必須正視的危機。
「憤怒的白人」的仇恨反撲!
法西斯、納粹、3K黨……皆是極右派代表,過去曾顛覆世界。如今川普銳不可擋,歐洲極右派強勢崛起,排外情緒日益高漲。在全球化時代,這是每個人必須正視的危機,並思考如何應對未來不可避免的種族與文化融合。
〈憤怒的白人語錄〉
1. 所有已知的穆斯林激進分子都該被遣返,包括他們的家人—無須經過法院審判,也不談人權,滾!
2. 必須接受我們的習俗,而不是我們接受他們的!
3. 所有人只要不能讀寫令人滿意的標準英文,立刻滾!
4. 不再接受移民,我們已經滿了!
5. 「我們應該開始試著找回彰顯英國價值的光輝歲月。每個人都得做出選擇,如果不堅持,只能等著完蛋。」
我們還有什麼扭轉情勢的可能選項?
極右派團體領導階層究竟如何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上街,就為了對抗一特定宗教及其習俗與教徒?
究竟是什麼樣的個人與社會條件導致他們做出這種基於偏見與迷思的決定?
他們所宣稱的目標背後是什麼?透過行動真正想達成的目標又是什麼?
能如何挑戰這類的種族意識形態?
如果光是藉由稱頌多元文化無法與其有效對抗,我們還有什麼扭轉情勢的可能選項?
作者簡介:
白曉紅
出生臺灣,自1991年定居英國。威爾斯大學批判文化理論研究所,杜倫大學東亞研究所,以及倫敦西敏寺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於《衛報》服務,並為各英華文報撰稿。長期關注非法勞工之議題,著有《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隱形生產線》、《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其中《Chinese Whispers》一書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前六名侯選名單;《散沙》一書於2013年贏得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單篇報導作品曾獲2004年艾瑪獎「最佳平面新聞獎」入圍;2008年獲勞動世界媒體獎「年度特寫報導獎」。
譯者簡介:
葉佳怡
木柵人,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被偷走的人生》、《死亡之心》、《返校日》、《缺頁的日記》、《被抱走的女兒》、《為什麼是馬勒?:史上擁有最多狂熱樂迷的音樂家》等十數種。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各界聯合推薦
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
王健壯|資深媒體人、《上報》董事長
陳冠中|作家、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
張翠容|戰地記者、國際時事評論員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作者、台大社會系教授
好評不斷
《憤怒的白人》充滿啟發性且別具洞見,深入剖析極右派的動機、政治策略與目標,並探討他們如何獲取支持。
—獨立報(Independent)
在英國風起雲湧的「新極右」勢力發展中,有兩個關鍵字:盧頓,以及英格蘭護衛聯盟(EDL)。
盧頓是倫敦以北的小鎮,居民來自多元族群,但二○○九年成立的組織「盧頓人民聯合」(UPL),讓這默默無聞的小鎮,從此變成杭廷頓文明衝突理論的現實樣本:患有伊斯蘭恐懼症的英國白人,將穆斯林定義為「國家的敵人」。UPL擴大成EDL後,全英國、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成為這股新極右派勢力必欲去之而後快的非我族類。
白曉紅與從盧頓崛起的憤怒白人,長期面對面對話,探索、質疑並紀錄他們的心路歷程,完成了一本調查採訪的經典,以及新極右政治的教科書。
王健壯|資深媒體人、《上報》董事長
《憤怒的白人》一書説的不止一個有關白人勞動階層的故事,而是道出了英國社群中的裂縫如何慢慢由九十年代西方世界介入中東產生,到近年來澈底撕裂傳統英國社區的過程。作者細緻的觀察,剖析了來自貧困勞動階級任何種族的可憐人們,是如何因爲菁英階級多年來的漠視以致跟不上政經大環境的腳步而各自衍生出激進組織背後的思緒,最後孕育了極端主義的脈絡。這本書對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歐洲日益氾濫的排外情緒有比媒體上看見的非黑即白更爲深刻的理解,不止每位研究歐洲政治社會的學人需要細閱這本書,在全球化每天沖刷著傳統社會架構的今日,生活在地球村的每一位居民都應該在看完這部書後細心思考應該用什麽態度去應對不可避免的種族和文化融合。
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
讓讀者近距離體驗仇恨政治,直面社會撕裂,無畏地真實!
陳冠中|作家、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
英國脫歐與川普崛起震驚世人,這背後的社會基礎都是憤怒的白人和民族主義,然而這不只是英美的問題,也是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名人推薦:各界聯合推薦
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
王健壯|資深媒體人、《上報》董事長
陳冠中|作家、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
張翠容|戰地記者、國際時事評論員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作者、台大社會系教授
好評不斷
《憤怒的白人》充滿啟發性且別具洞見,深入剖析極右派的動機、政治策略與目標,並探討他們如何獲取支持。
—獨立報(Independent)
在英國風起雲湧的「新極右」勢力發展中,有兩個關鍵字:盧頓,以及英格蘭護衛聯盟(EDL)。
盧頓是倫敦以北的小鎮,居...
目錄
推薦序
致臺灣讀者序
致謝詞
專有名詞之英文縮寫對照
序言 作者: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
一、生於斯,長於斯
二、捍衛想像中的國家
三、貝瑞公園的故事
四、「EDL無法在此生存」
五、激進右派翼不斷改變的面孔
六、英國種族主義的顏色
七、新的外來者
跋
索引
推薦序
致臺灣讀者序
致謝詞
專有名詞之英文縮寫對照
序言 作者:班傑明.傑凡尼亞(Benjamin Zephaniah)
一、生於斯,長於斯
二、捍衛想像中的國家
三、貝瑞公園的故事
四、「EDL無法在此生存」
五、激進右派翼不斷改變的面孔
六、英國種族主義的顏色
七、新的外來者
跋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