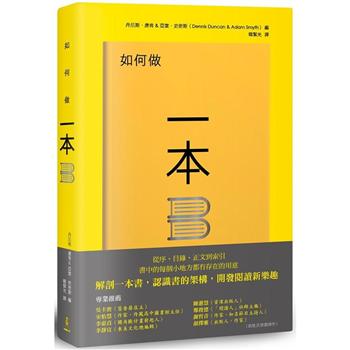張揚去阿德萊德求學,見證了澳洲的自由民主,也見證了歧視與冷漠。他結識了香港人基督徒傑森胡,高官子弟小盧,被小盧欺凌懷孕、到澳洲尋找被拐賣的女兒的施雪純,被小盧欺凌的時尚女莎莎等人,開始了對自身與中國的思考。
妻子朴茜在國內的孤獨中出軌了閨蜜的男友,閨蜜為報復而引誘假期回國的張揚出軌,使他陷入對婚姻愛情與性的掙扎。朴茜被戲弄後,來澳洲重尋張揚,途中遭遇偷渡組織並被傑森胡救至阿德萊德,後又遇小盧並激戰。張揚被捲入小盧虐待華工、槍殺莎莎和施雪純等事件中,深陷困厄糾紛的他,最終會做出何種選擇?
本書提出了情感、道德、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很多問題,卻始終保持著開放的敘述。主人公張揚在國內「困」的生活中掙扎,從日常生活、情感到事業追求與社會政治都太過壓抑,但他衝出中國地域文化的困局卻又被困在了國外,他要面對的不僅是西方,更是西方之中複雜而險惡的華人。他既背離中國卻又隔膜西方,這使他的社會屬性瀕臨無所歸依的迷惑。作者勇敢地剖開自我,大膽地叩問人與世界的本質,書中幾個重要人物全在各自的軌道上不屈地與命運對抗著,濃密而有張力地呈現著人類受難的縮影。
作者簡介:
王東岳,一九八六年生,數學系出身,曾留學澳洲攻讀教育學,並曾在立人鄉村圖書館位於重慶忠縣的第九分館編輯閱讀課讀本。本書故事發生地阿德萊德,為作者曾經留學之地。
章節試閱
張揚一進機艙就看到許多高低不平的鼻子和眼窩,深淺不一的說不上是白是黑是灰還是什麼其他顏色混合成的膚色, 像動物園裡的。幾個穿短裙黑絲襪的長腿空姐像馴獸師一樣穿行,路過張揚時,禮儀備至地打招呼,燦爛親切得像和他認識很久了似的。張揚心神震動,忙也擠出個難堪的笑,找到位置,把背包塞進頭頂的行李艙坐下了。
他挨著過道。一切令他奇特,他從未見過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像人又不像人的東西,在眼前走動說話,頭髮的顏色和質地,一看就不是之前見過的染成的黃毛白毛棕毛紅毛,而是真正的黃毛白毛棕毛紅毛。各種顏色的人輕手輕腳,彬彬有禮, 見人就咧開嘴笑,相互小聲說上幾句,離張揚太遠語速太快聲音又太輕,張揚英語不夠好,聽得半拉子懂。一雙空姐的絲襪長腿立在張揚的左側,貓腰撿著東西,不容忽視的撅起的屁股彷彿直沖著張揚的臉,張揚偏轉頭,發現那屁股幾乎蹭到他的左肩了,趕緊看那屁股最後一眼,頭擺正坐好,不讓那屁股碰著他。
張揚的父母妻子來北京送他,昨晚一家在小南國吃了河蝦仁毛蟹和露素雞,他們很少這樣吃,特別是母親,家裡剩飯剩菜從來不捨得扔,頓頓從冰箱拿出熱著吃完為止。張揚的父母屬於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在單位勤懇上班,像許多中國人一樣,埋頭苦幹,忙於置業,但存款甚微,靠節儉和精明買下了四套房,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浪潮中,身邊多少人靠著倒賣物資發了財,他們趕上了好時機卻沒做與時機有關的事,漸漸的,太窮的朋友他們嫌窩囊看不上,有錢的又覺得蹭著人家沒面子,因此在中規中矩的自持中,圈子越混越窄,少朋寡友, 拘謹正派。張揚大學的女朋友,就是如今的妻子樸茜,父母起初不同意他們在一起,嫌樸茜是小縣城的人,大學暑假張揚把樸茜帶到秦皇島家裡,父母客氣而緊張,給他們收拾了兩間屋子,不讓他們睡在一起,張揚說送樸茜回老家了,暗地卻安排住在旅館裡,經常去找她,稍回來晚些母親便疑神疑鬼地發脾氣。然而父母考核過關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促成了張揚的婚事,一路操辦著使他的女朋友飛速變成了現在的妻子。
二○一七年後,中國製造業下滑,經濟失衡,張揚的父母想移民紐西蘭沒移成,對張揚寄予厚望,父親希望他去澳大利亞讀研並技術移民,家裡充斥著抱怨和鼓勵的出國前的氛圍。張揚在私立學校當老師,婚後他和樸茜越來越說不到一起了。妻子雖然年齡沒變,相貌沒變,行事言談卻彷彿變得像老太太,張揚有時都區分不了她和他媽的心理年齡差了。樸茜的瑣碎絮叨讓張揚倍感孤獨,深感結婚太早導致的無望,彷彿青春還在,可是已經動彈不得。在被捆到婚姻關係上之後,在愛情沒有了更多尋覓的可能之後,在獨自闖蕩並迎接未來的機會喪失之後,張揚尚且年輕的身體中分泌過剩的荷爾蒙與生活的束縛之間的不平衡越發加劇,他憋得慌,但這卻不是做愛能解決的,他和樸茜的做愛已經不像大學時候,不像剛談的那兩年, 而是變得無趣煩悶,同樣的呻吟,同樣的動作,張揚得不到宣洩,內心失落。
這倒也罷了,張揚畢竟不是禽獸,問題是妻子的生活追求變得十分卑瑣,每天只是糾纏下頓吃啥,糾纏誰買菜誰洗衣服,或抱怨公司的工作累,把辦公室幾個人抹在嘴上循環著罵,抓住小事數落張揚,一開口就停不下來而且要他配合—這些多半在臥室悄悄進行的,他們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好意思大吵。也正因此,樸茜勸張揚再買一套他們自己的房子,因為張揚父親的另幾個房都在較遠的北戴河,而且還沒蓋好。樸茜為著攢錢買房,讓張揚把所有的工資全放在她那兒,張揚拗不過她,只好依從。
張揚不斷地喪失著自我,卻沒法跟父母說,也沒臉跟朋友說。他本來沒有留學的念頭,但不留學父母便終日不寧地製造危機感,他們雖無經濟的過多壓力,卻希望去更好的環境,過更有尊嚴的生活。樸茜來自山東的小縣城,並無這些想法,她佯裝配合卻暗中反對,常勸阻張揚別被忽悠。迷惘空虛中的張揚覺得留學也並非壞事,至少可以擺脫父母和妻子,而且中國的工作環境確實糟糕,他幹了兩年了,從來都是工資少雜事多,很多工都毫無意義而且沒有產出,張揚這些厭惡低效的形式主義,而且他鬥不過同事,再混若干年,估計別人全都晉升了自己仍在底層,因此終於開始著手,花一年時間考了雅思,申請了南澳大學的教育學,因為教師專業在澳洲的移民清單上。被錄取後他辭去了工作,按商定好的學費父母出生活費自己出,在妻子的怨恨中要回了一萬五兌成三千澳元,最終辦下簽證,登上了去阿德萊德的飛機。
昨天,他們一家坐大巴從小城秦皇島來到北京,吃完了那頓豐盛的晚餐,住到了機場的全季酒店。南澳大利亞正值冬天,阿德萊德屬地中海氣候,父母給張揚買了新的被子枕頭並用真空壓縮袋裝好,又給他帶上了電鍋和電餅鐺。張揚帶了雅思考試書,因為拿綠卡要雅思倆七倆八的,一個大行李箱一個背包的,下榻到了旅館。
張揚和樸茜住一間,父母住另一間。晚上,張揚和國內的熟人發消息道別,十點多洗漱罷了上床,叫樸茜卻叫不應, 使老大勁扳她的肩膀她才終於翻身了,原來在生氣呢,眼睛和鼻尖紅著,淚卻還沒下來。張揚忙問咋了,樸茜不吭又要翻過身去,張揚也生氣了,明天我都走了,今晚還要鬧一場嗎?樸茜帶了哭腔說你也知道你要走了?張揚就明白樸茜怪他沒搭理她,忙說,我在跟熟人道別呢,樸茜抹淚說,那你繼續找你那幫熟人吧,反正他們比我重要。
張揚很沮喪,但一想反正明天就走了,便不再多說,和氣地道了歉,從背後摟住樸茜,她穿著白色小背心,張揚手從背心的腋下伸進去用指頭搓她的乳頭,她的骨骼就漸漸軟了,轉身也抱住張揚,仰起熱烘烘的臉噙住了他的嘴。張揚本來驚訝樸茜為何對與他做這事如此樂此不疲,但此刻樸茜滾燙濕熱的淚印在了張揚臉上,她雖貼張揚那麼近卻還在睜眼望著他,張揚就覺得她可憐了,替她擦乾淚,她騎上來把張揚撅起的雞巴塞進去上下動了一會兒,張揚履行責任一般噙著她乳頭用舌頭撚著,她就帶了哭腔音色尖利地說,瞧你現在懶的,每次都要我主動,我一個女的還得求著跟你搞似的!
張揚深感荒唐,他把樸茜放平在床尾趴上去,樸茜的頭髮甩落在地,呻吟聲響隨著動作的加快變得急促,張揚說,我爸媽在隔壁呢,樸茜卻不耐煩地說,他們在走廊盡頭呢,瞧你這記性,在家就不敢出聲,壓抑得很,我說出去開房你卻不搭腔,你對我還剩下什麼?
張揚忙用嘴堵樸茜的嘴,樸茜的嘴立刻不說了,乖巧地進入了狀態,嗓子裡擠出動物般的鳴叫,舌尖在張揚牙齦上轉著,像認真做著檢測的醫生。張揚抖了一會兒,屁股撐不住了,酸軟地停在樸茜身上,表情痛苦得如同內心的痛苦,每次一射完就覺得一無所獲,沒有激情後應有的愉悅和寧靜。他側躺著揉妻子的陰蒂,妻子的確壓抑得太狠,高昂地挺起身子夾著他的指尖,高聲的尖叫像心臟快停時的求救。張揚愧疚,洗完躺下了。
樸茜說,你不是一直反感我,這下終於可以擺脫了。張揚說,我沒反感,我只是自己痛苦。樸茜說,哪來那麼多痛苦,出國了你這方面咋辦?張揚說,出國了誰還有心思整這個。樸茜說,你確實不該有心思的,花那麼多的錢,你爸媽非要你去我也不好說啥,但你要不努力拿綠卡看你對得起誰。張揚卻說,你是我的人,這話他們能講你卻不能。樸茜說,我不在乎什麼綠卡藍卡,我只是不想讓你走,聽說國外很開放,你可不能亂來,我給你寄個充氣娃娃吧,範冰冰的要不要?樸茜捅了捅張揚的腋窩。張揚噗嗤笑了,還是寄個黃奕的吧,我不喜歡範冰冰。
樸茜問,你走這麼長時間會不會擔心我?張揚說擔心你什麼?樸茜說擔心我出軌呀。張揚不吭了,漠然而陌生地望著樸茜。樸茜仍在說你擔不擔心,張揚就彷彿忍不住了,要坐起來理論,樸茜忙攔住說,逗你的,不會出軌的,會等你回來的。
說完乖巧地抱了上來。張揚搞不清樸茜糟糕的腦袋裡都裝了些什麼,對這種儀式感毫無興趣,像置於一片雨霧中一般茫然, 他說你神經病,以找事為樂。
樸茜說,你一走我就得獨自面對你的父母了,想著心裡就發怵。
這倒是實話。張揚都覺得在家裡壓抑,樸茜不是他們的親閨女,卻要獨自跟他們一起生活了。張揚見樸茜伏在他胸口的頭頂有一根白髮,給她拔下了說,別怕,我一放假就回來的。樸茜說,你爸叫你放假打工別回國的。不過,等你把那邊的事處理好了,我可以辭掉工作去找你。但就是不知道你爸媽同不同意。說完眼睛又潮紅了。
今早睡了個懶覺,醒來已近中午,他們在酒店的餐廳吃了便飯,直奔機場。臨別氣氛尷尬,張揚不習慣和父母煽情, 但出關的最後當口揮手告別之時,張揚剛要進去,卻聽見母親在背後高喊他的名字。母親矮矮的身子在人堆中東倒西歪擠進來,半頭的白髮在排隊的人之中那麼刺眼,驚慌地重複著,兒呀,你忘了帶護照了,張揚忙接過來,才說了一聲媽,母親的胳膊就已經被卷著,淹沒在人的洪流中。張揚看著她花白的頭髮被人潮淹沒,扭過身繼續走,胸口卻砰砰地跳。
直到現在,坐在飛機的深藍色座椅上望著窗外,他才意識到要走了,以往的一切已然告別,未來的一切還渺遠未知, 而且徹底孤身一人了,去的是從未去過的地方,用的是從未用過的語言,從這動物園一樣荒誕嚴肅的地方就開始了。張揚按了按褲腰的一千澳元紙幣,父親出於安全給他在褲腰內側縫了個兜裝進去的。他強烈地感受著沉重的呼吸,彷彿什麼都沒有了,只有命還在,命那麼真實,他的手受傷似的蜷縮於膝蓋,獨自品嘗著孤獨。
飛機在跑道上滑行,小小的窗口外是別的飛機,下邊的遠處是草地,天灰濛濛的像下雨前的色調。飛機越滑越快,轟響聲越來越大,巨聲轟隆不像生活中能有的,機身顫動,窗外機翅的襟翼上下抖得快要斷裂了似的,張揚和它們一起顫抖著,被卷到聲音和感覺的掙扎中,身不由己地猛然往後仰,飛機一翹飛上天了,把張揚牢牢地擠在椅背上。他頭一次坐飛機,大口吸著氣緊握著扶手,和陌生的恐懼感相抗衡,眼前又浮現出母親被人群淹沒的手和白髮,淚水終於忍不住大片大片地滑落了。
張揚一進機艙就看到許多高低不平的鼻子和眼窩,深淺不一的說不上是白是黑是灰還是什麼其他顏色混合成的膚色, 像動物園裡的。幾個穿短裙黑絲襪的長腿空姐像馴獸師一樣穿行,路過張揚時,禮儀備至地打招呼,燦爛親切得像和他認識很久了似的。張揚心神震動,忙也擠出個難堪的笑,找到位置,把背包塞進頭頂的行李艙坐下了。
他挨著過道。一切令他奇特,他從未見過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像人又不像人的東西,在眼前走動說話,頭髮的顏色和質地,一看就不是之前見過的染成的黃毛白毛棕毛紅毛,而是真正的黃毛白毛棕毛紅毛。各種顏色的人輕...
推薦序
困與惑──《阿德萊德》序
給東岳的小說作序,我頗費躊躇,由我來推介這部好讀而且有快感的小說,我很怕不能給這部優秀的小說更能走進別人心裡帶來足夠的幫助。讀小說我首先讀的是「意思」,有意思的文本我才會興趣盎然地細讀,細讀之後才會關注作品所要傳達的內涵,即所謂的意義和思想。
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我一讀就細讀下去了,閱讀中,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國人,尤其年輕人為什麼要出國?通常的說法是為理想,具體到小說主人公張揚,他的理想是什麼?學業?移民?找份好工作?掙錢買房,和妻子過好日子?都是,也都不是。他家境不差,父母健在,妻子嬌美, 生活小康,他的出國留學,在我看來是因為「困與惑」。張揚在國內的生活是「困」,在困的生活中掙扎,在掙扎中不斷地「惑」,迷茫而找不到答案。從日常生活、情感,到事業追求與社會政治,都太過壓抑、難以忍受,到異地尋求答案,就成了家境尚可的他的必由之路。
張揚儘管有猶疑,還是決然登上了去澳洲的飛機,落腳在了小城阿德萊德。去國外容易,長時間待下去,生活和情感上卻要經受煎熬,不同文化的碰撞會撞痛尋夢的人,甚至可能撞得頭破血流,命喪異鄉。張揚到澳州適應嗎?尋到人生答案了嗎?他的惑解了沒有?我在此不贅述,小說很好讀,張揚所經歷的故事會給讀者精彩的交代。但我可以明確告訴讀者,作品提出了很多問題,情感、道德、社會、政治等等方面的,然而始終是開放的,沒有給出完全的結論(我始終不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是小說的使命),細心的讀者可以慢慢琢磨其中的奧妙。
許多人強調小說的故事性,認為把故事講好小說就算基本成功了,我卻堅持小說更應該把人物寫好,像沈從文講的, 「貼著人物寫」。這部小說中,張揚用他的眼睛看到了很多, 用他的大腦思考了很多,他沖出了中國地域文化的困局,卻又被牢牢困在了國外,而且困的強度、力度和厚度都升級了。對張揚這個主人公,作者運用具有張力、充滿衝擊力和小說美學暴力的一串故事不斷呈現,使其形象逐漸豐滿,體現著作者的美學追求;作品敘述節奏把控得很從容,語言乾淨、簡練,我的閱讀快感與這些很有關。
我尤其要提出的是,作品常在緊張的情節中,或在人物深入思考、思想糾纏而難以自拔時,文筆突然轉到周邊的環境, 描寫簡潔而不繁密,像詩歌語言一樣,既有力量又富有意味, 一下子讓讀者長舒一口氣,情緒舒緩下來,這種延宕自自然然的,毫無做作,和作品內容扣合得嚴絲合縫,這是真正的作家天然的本能,也是不斷積累的真本事、真功夫。希望東岳揮槳奮進,寫出更多有意思、有意義的精彩作品,我喜歡東岳的小說,期望讀者也喜歡。
尹聿
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
困與惑──《阿德萊德》序
給東岳的小說作序,我頗費躊躇,由我來推介這部好讀而且有快感的小說,我很怕不能給這部優秀的小說更能走進別人心裡帶來足夠的幫助。讀小說我首先讀的是「意思」,有意思的文本我才會興趣盎然地細讀,細讀之後才會關注作品所要傳達的內涵,即所謂的意義和思想。
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我一讀就細讀下去了,閱讀中,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國人,尤其年輕人為什麼要出國?通常的說法是為理想,具體到小說主人公張揚,他的理想是什麼?學業?移民?找份好工作?掙錢買房,和妻子過好日子?都...
目錄
困與惑—《阿德萊德》序/尹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後記
困與惑—《阿德萊德》序/尹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