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山之戀〉
峨嵋老農誇言峨嵋刺之迅猛難當,竟說:「有個人十年磨一劍,然後就改練峨嵋刺了。」這話乍聽之下頗不可解,劍與峨嵋刺型制全然不同,峨嵋刺長約尺許,成對,雙頭刺,中間以鉚釘接上指環套手指,可旋轉。若說劍磨得窄短,至多也近似尺、鞭、稜刺之類兵器,和峨嵋刺全搭不上邊啊。
相傳峨嵋刺是峨嵋派白眉道長所創,後為峨嵋派代表武技之一。數代之後峨嵋派普善道長為派中高手,自也精擅此技,其拳、氣、劍等也是一時之選。但普善道長過的卻不是什麼專心求道、練武的清淨日子。
當初,甫成年的普善因藝有所成,又聰明俊秀,連同幾位江湖上已具名望的師叔伯輩,被分別遣往武林各派致書傳告峨嵋派老掌門仙蛻、新掌門繼立之事典。歸派途中,卻以抱不平,因緣際會,與一群俠義好漢一齊搗毀了惡貫滿盈的人間公敵天威堡。清除殘餘,殺入堡中內廳,內廳惡賊與己方盡皆鬥死,只餘帶了幾處創傷的普善和堡中一個小女孩。普善一念慈心未泯,暗暗放走了她,從秘道逃走。普善想那女孩秀美幼小,縱是邪惡日夕薰染,一個未及笄的小姑娘能有多惡?
普善所想雖未必盡然,事實上這回倒是對的,小姑娘是天威堡主十三歲的幼女丁眉姑,養在深閨,雖說不免驕氣,究竟年幼尚未及惡事,也不甚知曉世事。
三年後,眉姑潛上峨嵋,在荒僻裏堵上了普善。這小姑娘江湖上行走三年,世事漸通,也清楚了天威堡遭滅乃是報應,自知此仇報無可報,故尋到普善實非為了仇恨。這嬌憨女兒另有所恨,認為當時普善放了她,乃是因為視她幼弱武藝低微,不屑與鬥,就忿恨不已。孑然一身的她,人生無依無事,遂非與普善狠鬥一場,鬥贏了這瞧不起人的白面皮漢子,方爭一口氣。
普善給她弄得啼笑皆非,竟被逼得不得不動手過招。眉姑使的是一把尺二的短刃寶劍,普善則用二尺四的松紋古劍,兩個都是受不得折辱的高傲心性,功深得多的普善當然勝了。自此,眉姑隱居在峨嵋一處山坳日日磨劍,勤練劍法,隔上數月或經年,自覺武藝已有進境,便來伺尋普善私下偷偷邀鬥,但勝負都是一樣的。
若天威堡毀亡是遭惡報,那麼兩人其實不但談不上仇恨,反是恩義。除了爭一口氣,這兩個俊秀男女也都是敏才正人,雖然都對對方暗生好感,相鬥還是很認真,但就是盡術較技,沒有了殺氣。這樣在荒山上鬥了幾年,暗生愁悵的這對男女,普善是出家人,眉姑則是傲性人,雙方只得在越來越長的鏖戰中凝視對方,眉姑心中漸漸生出了另一種恨意。
鬥到第十年,眉姑不依了,說比試根本不公平,普善的劍太長了,佔盡便宜,不依不依。普善給她鬧得不知如何是好,說理也說不清。忽爾靈光一現,從腰間抽出了一對隨身攜帶的峨嵋鎮派兵刃峨嵋刺,說:「我用這個吧,尺寸與你的短劍相彷,這峨嵋刺我也練得熟,但嫌它小巧不夠大器,平常對敵是不大使用的。」眉姑還是不依:「長短是相類了,可是我劍是一把,你刺是一對,還是不公平。」
普善甚是苦惱,只得說:「那怎麼辦?你說吧,都依你。」眉姑收起短劍,奪過一把峨嵋刺,說:「依我說,這把刺我收下了,可是我不會使,你得教我,肯嗎?」
到底肯不肯?肯,就一切可以發生。不肯,即一切就此結束了。
〈公主現形記〉
娶了她之後,我這個黃金、鑽石單身貴族的鎂光生涯自就結束啦,但她是公認的絕色美人,我們這一對,還是戒不掉鎂光燈的。
她說我何止是貴族,方方面面都不脫是王子了,還說,不讓她過上公主生活,不讓她道地就是個公主,我這高貴的小王子也太沒面子了。既然要有公主比較像樣,我就讓她當了公主,買了小島,造了王宮,雖沒敢真的獨立建國,排場還是上擬王侯的。但稅可得多繳好幾倍啦,沒關係,要是她真能越來越像公主,我也是挺樂意的。
不幸她開始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公主,是神所選,不是我所選。並且認真的開始各方面研究,仔細定義「公主」的一切。
果然她日子過得越來越像公主,生活任何細節都以公主格調來做出要求。比如他囑我備辦二十床最最上等的毛毯,毛毯下面放了顆綠豆,自己則躺在二十床毛毯上一刻鐘,然後臭著臉起來跟我抱怨:「書上說真正的公主睡在二十床毯子上,還是難以忍受二十床毯子下一顆綠豆的顛疼,為什麼我睡你這二十床毯子卻什麼也感覺不到?絕對是你備置的這些毯子太次貨了,不夠柔細,根本不合我公主的身份啊!我不管,你一定得再給我備些真正的高級毛毯!」
到底是什麼書會寫出這樣子的餿文啊?再說,我所訂製的毛毯當然都是世上最貴、最高級的貨色啊,什麼喀什米爾羊毛、剖腹取胎的胎毛、鳳凰肚臍邊向內長的五根毫毛(鳳凰有肚臍?).....等等,各式各樣奇貨試了也不知道幾次了,我們的公主別說睡不出綠豆的顛疼了,有一次我把綠豆偷偷換成一顆海膽,她不是也睡得挺舒爽嗎?起來還是照樣罵我挑無可挑的二十張毛毯是省錢貨。
後來她常常幽嘆我不是個真正的王子,娘的!想想我當「貴族」的時候哪受過這種王子氣?於是我把她休了,但她自己說這是島內人才被逼出走。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韓愈)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山月小屋詩話】
本詩描繪長安城的春景,全詩充滿生氣勃勃的氛圍,風光絕勝,瀰漫著盎然的生機與無限希望。
描寫萬物萌生的春意,多從殘雪已盡,暖暖的春陽遍照,百花齊放入手。本詩寫的卻是春雨,這時的雨,不但不令人感到不便,也不帶憂愁。春雨不僅如油酥一般滋潤著大地,也讓春天的景色溶在水漫的暈染中,造成一種朦朧的美感。正如稀疏的草尖冒出來了,近看不覺得多少綠意,遠遠一片看起來,才竟有一抹迷迷濛濛的蒼綠,加上春雨浸染其間,景物的輪廓、顏色更是互相交融在一起。春雨微寒,河岸上的柳樹也浸潤在雨霧煙氣當中,整個畫面便如一幅絕美的潑墨水彩畫。
這裏說的是一年當中最好的時節,但這當然是人生得意之時才容易這樣感受起來的啊。
〈茶棚裏的對話〉
一隊馬車進了長安城,貶官到南荒八年,吳老爺子被皇上召了回來,噩運總算過去了。路途順利,比預定時間提前幾天抵達,京城裏新置的公館還沒派人來迎接。吳老爺子便要僕人快馬先去連繫,一行人暫在城門附近的茶棚稍作停留。
細雨久下不止,路上泥濘,趁這喘息時候,車夫們都忙著刷車軸、車輪上淤積的泥土,以便等等上路能好走些,車能好駕些。
吳老爺子坐在棚裏喝著自帶的上等好茶,對年方六歲的小兒子說:「看呀!這就是風光絕美的長安城,你可終於見識到了。」兒子卻說:「可是陰陰潮潮,怪不舒服呢。」吳老爺子就說:「說什麼呢?沒了這綿綿細雨,就不夠美啦。韓昌黎的詩不是說『天街小雨潤如酥』嗎?春雨貴似油,不但農夫要雨,文人墨客也愛這種情調呢。」
茶棚一角,僕人吳貴跟婢女晴兒正整理著已經開封的茶葉,重新包紮,一邊低聲談笑,聲音只有兩人自己聽得見,吳貴說:「你聽聽,還記得嗎?八年前老爺貶官出城,也跟今天一樣天氣呢,老爺當時怎麼說?」晴兒說:「誰記這些呀!不過當時老爺滿口抱怨,絕不像今天這樣笑瞇瞇的就是了。」兩人偷偷笑著。
小公子又說:「可是雨下得讓人心煩,路上更難走了,天好像在哭呢,又什麼都看不清楚。」老爺子卻哈哈笑起來,說:「這就是『草色遙看近卻無』的妙處了。爹這兩天在車裏教你讀的這首昌黎詩,正是描寫長安春雨的絕妙好詩啊。『絕勝煙柳滿皇都』,多麼優美的景致!你好好多讀書,慢慢就可以體會文人心境了。」小公子只得點點頭。
背向老爺的吳貴跟晴兒聽了更是笑,晴兒把聲音壓得更低,說:「八年前要出城時,老爺說的話跟小公子差不多呢。」吳貴也說:「看來這八年來老爺有『好好多讀書』啦,今兒個全是『文人心境』了呢。」
說到這裏,遠遠看見派去連繫的僕人帶著人回來了,吳老爺子一家就要在長安城開始過他們的文人新生活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在僻處自說Ⅳ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在僻處自說Ⅳ
《在僻處自說》為極短篇小說系列,本極短篇集而成冊,概念如市集街道中各類展示櫥窗,櫥窗在窄小有限的空間中,欲展現的美感仍需完整,必須具體而微,片時便能傳達激醒的感受,不論是強烈的、靜謐的、悠遠的、諷刺的、穎悟的......。又,在一眾櫥窗的集合中,各自彰顯小單位中的小宇宙,採取的風格便很多樣,都會、武俠、鄉野、科幻、鄉土、軼聞、歷史......等等類型,依所採題材,形成不同語境的小說。
《在僻處自說》系列中的第Ⅰ、Ⅱ集約有三分之一偏重實驗性,有的篇章似詩、似雜文,甚至有以古文似筆記小說之寫作,直到第III集漸次全然回歸現代小說語彙,實驗性則內化在較穩定的小說語彙中。
《在僻處自說IV》在穩定中求取新變,書分甲、乙部,甲部賡續上述小說語言發展的軌跡進發,寫尚未寫故事。乙部則以古典詩(唐詩)為題材,跨部、跨古今演出,以讀詩發揮奇想,這是一種閱讀古人情感的新方法,也是一種擴展現代小說視野的嘗試。
作者簡介:
張至廷(1967-),國立中興大學文學碩士,任靜宜大學台文系兼任講師。學術研究領域為中國傳統思想哲學、佛學、明末思想。文學創作方面,涉獵現代詩、小說、劇本等領域,著有極短篇小說集《在僻處自說》(三集)、短篇小說集《在僻處自說‧外編》,雜文圖集《舌苦齋休耕圖草》,長詩集《吟遊‧奧圖》、長詩集《西藏的女兒》獲選2013臺中市作家作品集、詩集《詩長調‧十五日之思念小冊》,崑劇新編劇本《思凡色空》、合編戲曲劇本《聊齋》參演2013上海國際藝術節、合編戲曲劇本《畫皮》等。
TOP
章節試閱
〈荒山之戀〉
峨嵋老農誇言峨嵋刺之迅猛難當,竟說:「有個人十年磨一劍,然後就改練峨嵋刺了。」這話乍聽之下頗不可解,劍與峨嵋刺型制全然不同,峨嵋刺長約尺許,成對,雙頭刺,中間以鉚釘接上指環套手指,可旋轉。若說劍磨得窄短,至多也近似尺、鞭、稜刺之類兵器,和峨嵋刺全搭不上邊啊。
相傳峨嵋刺是峨嵋派白眉道長所創,後為峨嵋派代表武技之一。數代之後峨嵋派普善道長為派中高手,自也精擅此技,其拳、氣、劍等也是一時之選。但普善道長過的卻不是什麼專心求道、練武的清淨日子。
當初,甫成年的普善因藝有所成,又聰明俊秀,...
峨嵋老農誇言峨嵋刺之迅猛難當,竟說:「有個人十年磨一劍,然後就改練峨嵋刺了。」這話乍聽之下頗不可解,劍與峨嵋刺型制全然不同,峨嵋刺長約尺許,成對,雙頭刺,中間以鉚釘接上指環套手指,可旋轉。若說劍磨得窄短,至多也近似尺、鞭、稜刺之類兵器,和峨嵋刺全搭不上邊啊。
相傳峨嵋刺是峨嵋派白眉道長所創,後為峨嵋派代表武技之一。數代之後峨嵋派普善道長為派中高手,自也精擅此技,其拳、氣、劍等也是一時之選。但普善道長過的卻不是什麼專心求道、練武的清淨日子。
當初,甫成年的普善因藝有所成,又聰明俊秀,...
»看全部
TOP
目錄
[甲部‧碎夢摭譚]
〈鹹菜農〉
〈都很專業〉
〈沒種的男人〉
〈人貓失戀記〉
〈抱怨人生〉
〈隱身者流〉
〈三叉幫軼聞〉
〈隱身高手〉
〈露餡〉
〈動搖〉
〈桌球學〉
〈文明通〉
〈時事貧論〉
〈學妹的夢〉
〈荒山之戀〉
〈公主現形記〉
〈講學自由〉
〈逐客〉
〈換身〉
〈質子〉
〈不變初心〉
〈老王與小三〉
〈海景〉
〈畫皮尋夫記〉
〈人皮〉
〈都是畫皮〉
〈爭個臭皮〉
〈善皮〉
[乙部‧唐詩亂彈]
[五言絕句之卷]
渡漢江(宋之問)〈歸鄉變調〉
登鸛雀樓(王之煥)〈更上一層樓〉
春曉(孟浩然...
〈鹹菜農〉
〈都很專業〉
〈沒種的男人〉
〈人貓失戀記〉
〈抱怨人生〉
〈隱身者流〉
〈三叉幫軼聞〉
〈隱身高手〉
〈露餡〉
〈動搖〉
〈桌球學〉
〈文明通〉
〈時事貧論〉
〈學妹的夢〉
〈荒山之戀〉
〈公主現形記〉
〈講學自由〉
〈逐客〉
〈換身〉
〈質子〉
〈不變初心〉
〈老王與小三〉
〈海景〉
〈畫皮尋夫記〉
〈人皮〉
〈都是畫皮〉
〈爭個臭皮〉
〈善皮〉
[乙部‧唐詩亂彈]
[五言絕句之卷]
渡漢江(宋之問)〈歸鄉變調〉
登鸛雀樓(王之煥)〈更上一層樓〉
春曉(孟浩然...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至廷
- 出版社: 島讀文化學社 出版日期:2018-11-15 ISBN/ISSN:978986928294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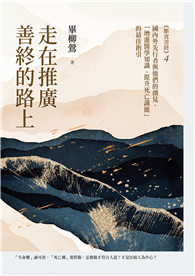



百病需讀仙人語─讀張至廷《在僻處自說IV》 11/24星期六,選舉日,感覺這世界病了,人們為選舉而瘋狂、為選舉而奔忙,這場選舉的結果其實可以預期,我知道我會陷入人生的谷底的谷底,我拿起了張至廷的《在僻處自說IV》,讀著作者自序,每一則都彷彿是指引心靈的明燈,讓人領悟到人生的荒謬,執著於此,何苦來哉? 11/25星期日,選舉後的憂鬱症,台中失去了蓋一條台海大隧道的機會,我不懂台中人怎會如此,或許我參不透,就像「公主現形記」中自以為是的公主一樣,明明不是公主,卻把自己當成公主又要別人把自己當公主,留不住人才,人才是否真的是人才?這種大智大慧的事情,看來只有真神能夠明白,我不了解我的明白。 11/26星期一,生活依然是乏善可陳,做事情依然處於失智狀態,「抱怨人生」裡講到銀杏治健忘似乎沒啥效果,但是可以提醒自己是健忘的,人貴自知,人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一無所知。 11/27星期二,這天要去學校上課,出門前看著家裡的三隻貓兒彼此爭鬥,想起書中「小碾子」家族的各種故事,從這幾隻貓的角度來看,或許對於我出門這件事都是充滿抱怨與憤恨吧,家族這個概念很微妙,是我無法體會的事情。 11/28星期三,身體不適的一天,大概是前一天上課回來時騎車沒穿外套有點受寒,想想社會病了,我也病了,拿起《在僻處自說IV》看了幾則乙部的「唐詩亂彈」,在作者的詩話與故事張力下,我的病似乎不藥而癒了!古有曹操聞陳琳檄文頭疼不痛,今有紹平讀真神小說風寒自癒。 11/29星期四,世界依然紛亂,小說裡的妖,總是比人類有情,可惜現實裡沒有妖,不然我一定只跟妖當朋友。現實的世界有著虛擬的你我,虛擬的小說空間卻有著真實的情感。每個文字的內容都可以想像,就像每一條假新聞可能只是文學的再詮釋而已,就像書中的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新的故事,他未必是假,也未必是真,可能是平行時空裡的一抹塵埃。 11/30星期五,才驚覺《貴時代好亂》線上雜誌要出刊了,而我一週的時間,都沉浸在這小說的世界中,覺得不推薦這本書給芸芸眾生實在對不起社會,也對不起作者,更對不起還有些許對這世界期待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