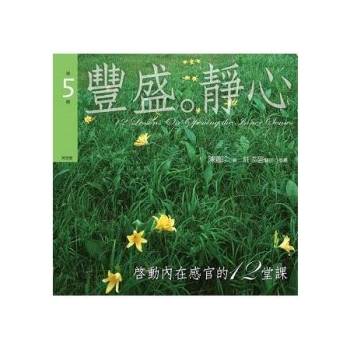李舒白尚在宗正寺裡等待案情明朗,
而努力尋求轉機的黃梓瑕,卻不知新的陰謀已朝她而去。
可最殘忍的並非遭到陷害,而是陷害妳的,是妳親近的人。
縱使黃梓瑕能依靠出色的推理能力破案,洗清自身的嫌疑,
可心理上的傷害,卻早在得知真正的犯人時就已造成。
為何她身邊的人會突然認為夔王即將覆滅大唐?
為何他們又都在指證夔王後自殺?
小紅魚、符咒、連串命案,
設計這一切的人對李舒白步步進逼,意圖令他身敗名裂而死。
黃梓瑕藉著王家的勢力,逐漸探查出事情的原貌,
即便代價是放棄她最後的退路,
她也要讓李舒白逃離所有樊籠,再也不會受困危局!
本書收錄番外〈元夜〉。
本書特色
側側輕寒
精采絕倫的大唐辦案軼聞,改編電視劇緊鑼密鼓籌備中!
她拔下髮間的簪,逐漸撥開擋在真相前的重重迷霧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簪中錄 第四簪 天河傾下(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言情小說 |
$ 190 |
古代小說 |
$ 190 |
Comic Book |
$ 204 |
古代小說 |
$ 216 |
中文書 |
$ 216 |
華文羅曼史 |
$ 216 |
文學作品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簪中錄 第四簪 天河傾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