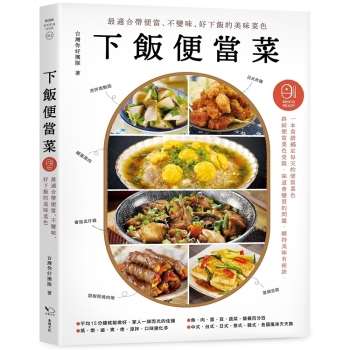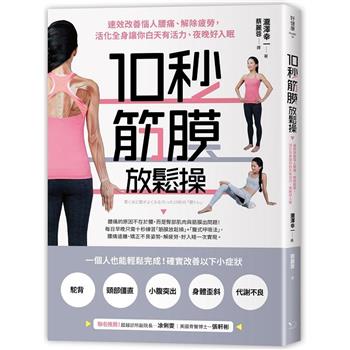傅明珠身為宰相之女,太皇太后是她的親姑姑,
早逝的先皇是她的表哥,當今皇上是她的表侄,
從小受盡萬般寵愛,被養得飛揚跋扈,天真自我,
而她對臨安王宇文佑一見鍾情,任性要嫁的結果,
竟讓她備受凌辱,最終含恨而終。
而今她又重生回到十六歲那一年,
一切悲劇尚未發生,她摩拳擦掌,興致勃勃,
打算一改過去的驕縱任性,拯救傅家於覆滅之前!
只是人的本性、智慧,豈是這麼容易改的?
她以為自己料敵機先,父兄卻說她自作聰明;
她以為自己能當黃雀,殊不知其實只是一隻被覬覦的蟬。
她的身分讓她的婚事註定牽扯各方利益,
前世的經驗也讓明珠對愛情失去信心。
卻不想在前世無甚交集的英王宇文初,今生卻處處都看得到他!
不僅如此,他還十分陰險卑鄙,將她幾個大好計畫,全部破壞殆盡……
她到底是幹了什麼招惹了這個魔星啊──!
本書特色
意千重最新歡樂宮鬥原創言情作品
當驕縱貴女遇上腹黑王爺,
究竟是能順利擺脫,還是會落入陷阱?
草包就算是重生,也不會突然變聰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九闕鳳華 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華文羅曼史 |
$ 205 |
古代小說 |
$ 205 |
言情小說 |
$ 234 |
古代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28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九闕鳳華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