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控制》和《列車上的女孩》的你,現在,只有這本小說能滿足你!
《週末泰晤士報》十大暢銷排行榜連續12週!
*暢銷犯罪小說!翻譯超過30個國家!
*i Book 2015年最佳書籍!
*《死者》作者彼得‧詹姆斯、《誰在門那邊》作者伊莉莎白.海涅斯、《兇手在隔壁》作者艾莉克絲‧瑪伍德 一致推薦!
誰殺了那個孩子?
她感覺他從身邊跑開,跑往家的方向。門廊亮著燈,洋溢著溫暖,此刻的他要的只是牛奶、餅乾和二十分鐘的電視。那輛車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接著,事情接連發生:汽車急煞,男孩猛力撞上擋風玻璃,身體在引擎蓋飛起又重重摔落。剎那間,一切就結束了……
繼續人生道路的唯一辦法,只有離開熟悉的一切,重新開始?
一個纖細美麗的年輕女孩深夜抵達威爾斯海岸,就此住了下來。沒有人知道她從哪裡來,發生過什麼事,她遠離人群,似乎隨時充滿恐懼和悲傷,似乎有段人生的回憶仍糾纏不休……
被害與加害者瞬間翻轉,眾人看到的不見得是真相?!
布里斯托刑事調查部雷‧史蒂芬始終對那樁肇逃案件無法釋懷,暗中追查卻仍如大海撈針,受害者的母親竟也人間蒸發。一年過去,不放手一搏,恐怕再也沒有機會……
研究犯罪心理學多年,曾服務於警界的克萊爾.麥金托,獨特的經歷與細微的觀察力,創作出知名作家一致推薦,譽為「完美無瑕」,希望永遠讀下去的精彩之作!
國外各方好評
※「故事轉折之巧妙讓我眼紅!」——馬克.畢利漢,《Blood Line》得獎作家
※「全書曲折離奇,讓人心跳加速。完美悲傷的寫照,讓人久久不能自已。」——iBook
※「精采絕倫,內容生動,出人意表,讓人甘拜下風。實在太好看了!真希望能永遠讀下去。」——彼得‧詹姆斯,《死者》作者
※「這本書讓我落淚,讓我大聲喘氣,最重要的是,我多麼希望這本書是我的作品啊!引人入勝,非常真實,讓人極度不安。一部讓人愛不釋手的作品!」——伊莉莎白.海涅斯,《誰在門那邊》作者
※「氛圍十足,麥金托充滿情感又完美無瑕的作品!」——艾莉克絲‧瑪伍德,《兇手在隔壁》作者
※「緊張的情節接二連三,一種危機跟恐懼感隨時重壓心頭。結局十分巧妙,令人難忘。」——莎曼珊.海耶斯,《直到你屬於我》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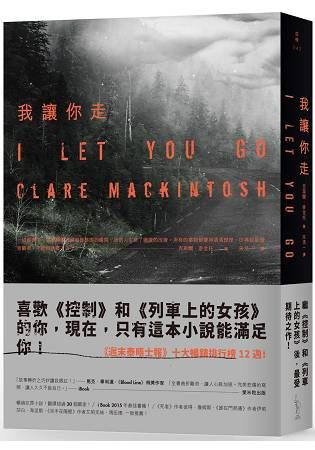
 2017/10/09
2017/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