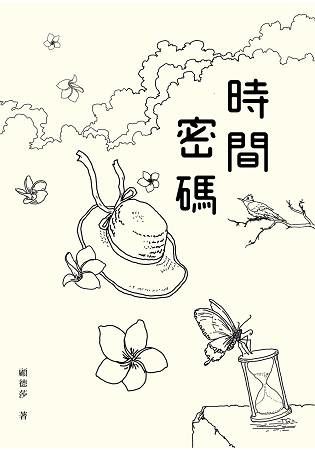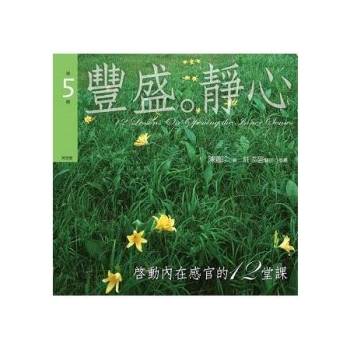傷心酒店
其實,我們並不相愛
對著落日抽煙,尋酒館飲酒
一起做的事都是因為寂寞
寂寞很長,纏住回家的雙腳
不願意分手
因為酒館還沒有關門
他們總是不明白
隔著菸霧和酒氣我們可以勇敢一點
把寂寞瀉漏出來
白天 寂寞被寫在電腦檔案裡面
以excel加總
用word長敘
加上密碼誰也不能開啓
夜晚 我們倚著欄杆,在菸霧中
交換密碼
開啓寂寞
放進酒杯加幾顆冰塊
冷靜燒灼的孤單
酒店關門前不回家
因為家裡只有發霉的空氣
鏡子。玻璃
用鏡子看自己
塗上水銀的玻璃
反射我的眼目
衰頹的水晶體
看見了眼淚
看見了歲月
看見了歡喜
看見了 漸漸熟悉的自己
透過玻璃看你
直視隔著空氣灰塵的你
像看見遙遠星球的自己
曾經的眼淚
曾經的熾熱
曾經的熟悉
再見了
曾經愛過的你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時間密碼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5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現代詩 |
$ 315 |
文學 |
$ 387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時間密碼
妳:你怎麼可以把我的故事洩漏出去。
我:那是另一個朋友的故事。
妳:當妳的朋友好危險,會被出賣。
我:除了幸福進行式,每個相遇到分手
都是公式,誰都可以對號入座。
妳:所以,妳也是主角。
我:讀進去的人是主角。
妳:妳好狡猾。
我:詩本來就是狡猾的文體。
寫詩是每一個人的權利,我用詩寫日記,紀錄自己、他者,每一首詩都可以對話入座,如果,您覺得,「它」符合您的氣息。
作者簡介:
德莎,doksa
嘉義人,高中校刊總編,畢業後與文字分開四十年,2012年重新提筆,以書寫作為生命最終之自我完成。
曾獲全國高中組小說比賽第二名(聿珊的心願)
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極短篇(篇名:父親 以季隱筆名發表)
第二屆新北市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 說吧。記憶)
第四屆桃城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桃城迴旋曲)
第二屆全球華文星雲文學獎(散文組 篇名:夜色被街燈一盞一盞推開 星雲集結得獎作品出版《推開夜色》散文集)
第十五屆台北市文學年金(長篇小說創作 驟雨之島 尚未發表)
2016年第一期國藝會創作補助(長篇小說創作)
2016年在嘉義市社區大學教授「影像詩創作」
TOP
章節試閱
傷心酒店
其實,我們並不相愛
對著落日抽煙,尋酒館飲酒
一起做的事都是因為寂寞
寂寞很長,纏住回家的雙腳
不願意分手
因為酒館還沒有關門
他們總是不明白
隔著菸霧和酒氣我們可以勇敢一點
把寂寞瀉漏出來
白天 寂寞被寫在電腦檔案裡面
以excel加總
用word長敘
加上密碼誰也不能開啓
夜晚 我們倚著欄杆,在菸霧中
交換密碼
開啓寂寞
放進酒杯加幾顆冰塊
冷靜燒灼的孤單
酒店關門前不回家
因為家裡只有發霉的空氣
鏡子。玻璃
用鏡子看自己
塗上水銀的玻璃
反射我的眼目
衰頹的水晶體
看見了眼淚
看見了歲月...
其實,我們並不相愛
對著落日抽煙,尋酒館飲酒
一起做的事都是因為寂寞
寂寞很長,纏住回家的雙腳
不願意分手
因為酒館還沒有關門
他們總是不明白
隔著菸霧和酒氣我們可以勇敢一點
把寂寞瀉漏出來
白天 寂寞被寫在電腦檔案裡面
以excel加總
用word長敘
加上密碼誰也不能開啓
夜晚 我們倚著欄杆,在菸霧中
交換密碼
開啓寂寞
放進酒杯加幾顆冰塊
冷靜燒灼的孤單
酒店關門前不回家
因為家裡只有發霉的空氣
鏡子。玻璃
用鏡子看自己
塗上水銀的玻璃
反射我的眼目
衰頹的水晶體
看見了眼淚
看見了歲月...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心情捕手—小序顧德莎詩集 ◎林央敏
初識顧德莎已是四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時有十幾位出身嘉南平原的文藝青年,他們大多還在嘉義、台南兩地的學校就讀,而且都各自擔任該校學生刊物的編輯,也都是各自校園的文青健將,這些人因文學興趣,加上地緣之便,糾合起來共組詩社、出版一本名叫「也許」的現代詩季刊,於是顧德莎和我雖然不同校,卻成了同仁,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得有幾次連誼互動,記得那時,德莎的筆耕重點是在散文。
由於大家當年都是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畢業後各奔前程,或升學或就業或服役去,散居他鄉外里,《也許》也在五...
初識顧德莎已是四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時有十幾位出身嘉南平原的文藝青年,他們大多還在嘉義、台南兩地的學校就讀,而且都各自擔任該校學生刊物的編輯,也都是各自校園的文青健將,這些人因文學興趣,加上地緣之便,糾合起來共組詩社、出版一本名叫「也許」的現代詩季刊,於是顧德莎和我雖然不同校,卻成了同仁,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得有幾次連誼互動,記得那時,德莎的筆耕重點是在散文。
由於大家當年都是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畢業後各奔前程,或升學或就業或服役去,散居他鄉外里,《也許》也在五...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寫詩年代 自序
詩人顧城說:詩是樹葉,比秋冬短,比世界長。
那時候,我們的世界是一座高牆—「髮長不得過耳」、「裙長要過膝」、「男女分校、分班」、「異性不可私下約會」、「不得說閩南語」、「不得議論師長」......每一項規定都是一塊磚,疊成一座牆。
青春是想展翅飛翔的鴿子,牆高如籠,稍稍不慎便要因為衝撞而折翼;於是我們用文字編成繩索,結繩成梯,爬上高牆,眺望牆外一片森林—余光中、瘂弦、葉珊、鄭愁予、席慕蓉,均是枝葉亭亭,鬱鬱蒼蒼的樹林提供烈火青春一片清涼。我們一面讚嘆,一面拿起筆,學著寫下心中的詩句。
當...
詩人顧城說:詩是樹葉,比秋冬短,比世界長。
那時候,我們的世界是一座高牆—「髮長不得過耳」、「裙長要過膝」、「男女分校、分班」、「異性不可私下約會」、「不得說閩南語」、「不得議論師長」......每一項規定都是一塊磚,疊成一座牆。
青春是想展翅飛翔的鴿子,牆高如籠,稍稍不慎便要因為衝撞而折翼;於是我們用文字編成繩索,結繩成梯,爬上高牆,眺望牆外一片森林—余光中、瘂弦、葉珊、鄭愁予、席慕蓉,均是枝葉亭亭,鬱鬱蒼蒼的樹林提供烈火青春一片清涼。我們一面讚嘆,一面拿起筆,學著寫下心中的詩句。
當...
»看全部
TOP
目錄
心情捕手—小序顧德莎詩集 林央敏序
寫詩年代 自序
輯一 速描
春的布陣圖
綠牆
光
青苔
雨中的傘
貓 燈
葉子在牆上寫詩
少女 咖啡
茶花 筆
落葉
輯二 時間變奏曲
中年失憶
老屋
時間
雲泥
鏡子
失眠
輯三 愛情劇場
誰是主角
我的傷心和你的傷心不同顏色
初戀
我想不呼吸
情書
分手的理由
把夢調整一下
冷戰
紅玫瑰
忘川
我不願意想你
我們在暗黑的街頭分手
我的夢慢慢躺下
傷心酒店
新同居時代
情人節
給情人的分手信
絕情詩
輪迴
算命
銹蝕的金石盟
鏡子。玻璃
輯四 花事
蓮...
寫詩年代 自序
輯一 速描
春的布陣圖
綠牆
光
青苔
雨中的傘
貓 燈
葉子在牆上寫詩
少女 咖啡
茶花 筆
落葉
輯二 時間變奏曲
中年失憶
老屋
時間
雲泥
鏡子
失眠
輯三 愛情劇場
誰是主角
我的傷心和你的傷心不同顏色
初戀
我想不呼吸
情書
分手的理由
把夢調整一下
冷戰
紅玫瑰
忘川
我不願意想你
我們在暗黑的街頭分手
我的夢慢慢躺下
傷心酒店
新同居時代
情人節
給情人的分手信
絕情詩
輪迴
算命
銹蝕的金石盟
鏡子。玻璃
輯四 花事
蓮...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顧德莎
- 出版社: 日初 出版日期:2016-12-01 ISBN/ISSN:978986929520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