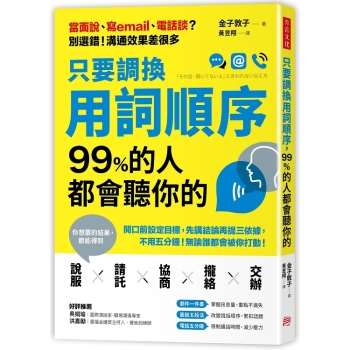宮崎駿的魔法世界 : 遺失的創造力 /蔡昇諭(精神科醫師)
………………
精神分析是ㄧ種人在生命中自主地按下慢轉,暫停甚至倒轉的狀態,我們想著某個片刻的自己,琪琪的母親看著琪琪準備離家,驚訝之餘也讓母親本人的思緒倒轉到自己曾經離家的記憶中。
父母親和周圍的鄰居,也像參加某種畢業典禮的場合,見證這一刻的到來。生命之中,有些改變命運的事件出現,某些注定,但也又有一些未知數,等待人運用自己的潛力或特質前進。
電影版中稍微仔細交代了父母親的出生背景,父親是人類,母親是魔女,如果在哈利波特,這樣魔法師和麻瓜(一種對人類戲謔的稱呼)的組合也不陌生。魔女琪琪對自己要成為像父親的人類,或是像母親的魔女,顯得非常明確(我只想做個魔女),沒有猶豫,然而考驗卻是要如何在人類(父親)居住的環境中做個魔女,這對從小生長在魔女世界的琪琪是很陌生的,有可能琪琪對父親也是很陌生的,到人間探險是否意謂著開始了解父親所生存的世界?所遺忘的另一半世界。
我很好奇,帶著這份傳承自母性天賦的琪琪,如何承接這份禮物或是重擔?如果說精神分析的某個面向是要問自己從何而來,顯然當時的琪琪一點都不覺得這是個關鍵的問題,某些天賦異稟的人或許也自然而然遨遊於天地造化之中,一點都沒有任何障礙,但生命的苦難及趣味也在於當障礙出現時,當自然不再自然時。
如果把琪琪的飛天掃帚魔法與兒童發展時所曾經出現各式各樣的魔幻想法相比,這則動畫似乎是在講一個從年幼孕育而生且伴隨成長的願望,充滿興奮之情,動畫中的想像力怎麼樣落實在旅行的所見所聞,而我認為,在琪琪還沒開始旅行,想像力早就開始運作,推波助瀾,於是琪琪說:「我現在的心情就像拆禮物一樣興奮」。旅程就像是過著一個又一個迎接禮物的節日,如果進一步再想下去,琪琪離家的不安和對父母的依賴跑到哪兒去了呢? 會不會透過想像力所帶領的冒險過程,抵銷了這些害怕?
當魔法實行於人間之初,挫折遠遠多於興奮,生澀的開端造成許多混亂,琪琪並不了解人間的秩序,不了解人類世界的移動方式是道路平面的挪移,而不是琪琪所熟悉的世界。
飛行的琪琪要如何在人間掌握掃帚、控制方向?也就是認識新的規則及空間概念,已經不再是以前在魔法世界中盡情變魔法過日子。
在幾部片子當中,兩個主要角色往往一個是擁有魔法的強者,另一個是不具備特殊能力的凡人,例如「魔女宅急便」中琪琪身為天生的魔女,喜歡她的則是善於騎車想要將腳踏車轉為飛行器的蜻蜓,「神隱少女」一塊磚都搬不動的千尋面對法力強大的湯婆婆,「霍爾的移動城堡」中被詛咒而一夜白髮的蘇菲卻協助擁有魔法卻內心脆弱不已的霍爾,這種魔法與人類之間對應的關係,如同是想像與現實之間往往互相呼應及需要,另一個層次則是關於擁有魔法是否真的比較有能力的辯證,結果往往不是。
在片中經過一連串的快遞任務後,琪琪為何失去魔法,無法再飛行?這是一個耐人尋味值得玩味的問題。琪琪面臨許多外在的壓迫,例如強風來襲、被烏鴉攻擊、遺失黑貓玩具而把真貓當假貓等挑戰,她似乎都能一一克服,也開始提供生柴火烤派、換燈泡等其他相關服務,這些擴大了她在人間從事服務的經驗範圍。
琪琪先是接受男孩蜻蜓的邀約,又接連接到不少工作,看似因為工作時間壓迫無法赴約而感到失望,或是因為淋雨飛行而感冒臥床,另一個心情的衝突是否來自於看見接受禮物的女孩完全沒有任何開心的回應,這個衣著華麗的女孩正進行著生日派對,相較於一襲粗陋黑衣的琪琪,也對比於得完成工作無法參加派對的琪琪。
當琪琪與蜻蜓約會騎車遊玩的喜悅被一群蜻蜓的友人撞見而消失,當一路相伴的黑貓愛上鄰家白貓而不再能和她通話,她失去聽懂黑貓話語的能力,她飛不起來了,她失去對抗重力漂浮的力量,那股心想飛成的力量化為烏有。
當被分析者說他曾想起卻又想不起來的記憶,這時懊惱到腦中一片空白。沒辦法想或想不起來的狀態會不會就像飛不起來的魔女,而「阻抗」像是某種分析者試圖理解被分析者陷入泥濘的形容,在心中揣摩著這些阻抗力量來自精神結構的哪個位置,如何對抗和化解。
電影版中麵包店老闆娘安慰琪琪創業之初的門可羅雀「做不成魔女,做個普通人也不錯」,甚至表示「做個普通人,我不覺得沈悶」,這些在琪琪很想施展魔法的雄心壯志,卻經不起一通電話都沒有的挫敗之際所提出的言論,或許是大人的老生常談,卻也像預言一般暗示著未來失去魔法時的解決之道。
當灰心的琪琪到畫家大姊的山中小屋重新體驗生活,那恰好是她在飛行時,被一群黑色烏鴉攻擊摔落的地方,回到曾經跌倒之處,再從那裡爬起來。
她和大姊徒步一步一腳印到山中小屋,而不是以往熟悉的飛行方式,飛行可以瞬間從A鎮到B鎮,如同想像可以任意改變風景的座標,也可以讓凡人仰頭稱羨崇拜,也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一切。而這些曾經從飛行獲得的興奮及暢快都不見了。或許是一種對全能幻想的告別,也或許暫時失去飛行能力,才能讓琪琪真正經驗到人類的處境,她與週遭的人們便能有同樣的時間感,琪琪不得不徒步走在草原、石子路和林中各種路徑中,也得因迷路或腳酸而低聲求人搭便車。
在經歷見山又是山之前,總有見山不是山的階段,在《走路,也是一種哲學》一書當中,作者說明步行是一種緩慢的重新體驗,「所謂慢,就是完美地貼合時間,直到分分秒秒宛如沙漏滴流,像小雨般滴滴答答地打在石頭上。這種時間的延展深化了空間。這是走路的奧妙之一,用一種慢慢靠近風景的方式,使風景逐漸顯得熟悉。」
電影版中的琪琪,則是發現自己只會飛行,其他都不會,而不會的對她來說反而都是魔法,例如騎腳踏車令她感到不可思議。一個學習新魔法(騎腳踏車)的過程讓琪琪感覺心裡有人陪伴的必要,一個恆在客體的重要,這個恆在客體的延續似乎是透過男主角蜻蜓的協助而完成。
從掃帚這個工具如何被使用的角度來看,剛開始它比較像是琪琪的玩具,它提供琪琪玩耍的樂趣,也讓眾人可以睜大眼睛注視她,一個她不用費力就可以獲得他人目光的「物品」。
在《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一書當中,佛洛伊德提到遊戲中孩童的幾個特質,這些特質或許跟後來的創造力有關。孩童投入相當多情感所創造出一個想像的世界,並且與現實保持分離。琪琪要從孩童轉變成大人,飛行不再是個遊戲,它與現實的分野逐漸消失,隨著琪琪的成長,魔法不會只是停留在要如何飛行,飛到哪裡的器具,也包含這項能力要如何在現實中找到一個寄放之處。她體悟到掃帚可以是一個傳遞人們喜悅,分享禮物的工具,也可能變成攻擊、復仇的載體。
於「心之谷」這部關於作家如何獲得靈感及實現的片子裡,女主角月島雯從隨興的填詞到非寫出不可的創作,她因為對男主角聖司的愛戀而效法他追尋一項技藝的磨練,她著迷於寫歌詞的興趣,便開始發展去寫一部小說,月島雯認同了聖司,當她看見聖司所製作的小提琴,讚嘆道「簡直跟『魔法』一樣」,她想要寫完美的小說,如同聖司想要製作完美的小提琴,像是一種初生之犢的全能幻想,真誠但難以實現。
聖司的爺爺把帶有綠寶石成分的石頭拿給女主角看,「如果要做小提琴、寫小說,則要從心裡找到那塊石頭,經過磨練。」月島雯做了場惡夢,顯示她對創作的焦慮,她於夢中努力奔跑在景物變化的路上,出現幾個洞口,「哪一個才是真的?」撿起一顆晶瑩剔透的寶石,握在手中,打開發現一隻早夭的雛鳥。她的創作力量背後或許連結到能否和聖司重逢的願望,如果自己無法像聖司那樣專注在技藝上的追求,如果無法把自己琢磨成一顆寶石的下場為何呢?
月島雯的青澀小說暗喻,如何在心中「超我」嚴厲要求不眠不休的工作下,找到一條「原我」仍能興奮歌唱的空間?內容談到貓伯爵的由來,他是手藝粗糙見習生的作品,但因為被愛澆灌,所以有愛人的能力。貓伯爵像是自己創作時內在的投射,她創作的過程不乏協助她的人,父親、聖司爺爺及胖貓。
「霍爾的移動城堡」中有個四色開關,可以立即將城堡移放到綺麗祥和的國度或戰火日夜的大地。創作者的空間就是營造一個從現實通往想像的空間,「心之谷」聖司爺爺的工作室,擺放著鐘琴與貓男爵的雕像,流傳著爺爺自己失落的情感記憶與貓男爵的童話傳說,工作室也是月島雯融入聖司提琴世家和諧樂音的歡唱空間,加斯東.巴什拉的《空間詩學》談到:「一個作者內在擁有的房間,以及他把生活中不存在的生命活起來。」月島雯在聖司離開的失落空間裡醞釀自己的創作。
溫尼考特於《遊戲與現實》一書中提到關於創造力的定義,也就是面對外在現實時,興味盎然的生存態度。創造力並未僅侷限在作家或藝術家的創作功力,而是每個人在面對自身生活的某種前進節奏、靈感風味或思想領悟。創造力往往從遊戲出發,藉由一些模仿或假裝,當蜻蜓看見飛行船,或羨慕琪琪飛行的能力,他試圖製造飛得起來的腳踏車。
魔法是需要被駕馭的,否則也會有可能毀壞琪琪的幻想,也有可能導致她把這支獨特的「自己」折斷、塵封或隔開。如同霍爾中的蘇菲如何面對火不被燃燒,卻又能夠運用它協助霍爾走下去。
畫家大姊與琪琪分享畫畫就像魔法,有時也會失靈畫不出來,畫家大姊在琪琪同樣年紀時,也曾經有低潮無法創造的時候,那時候她發覺到自己的畫都是在模仿別人,然而要如何畫出自己,似乎也只有不斷原地踏步的練習,還有休息。
折翼之後的天使才會開始思考自己以前為何可以飛行。琪琪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魔法消失呢?原本再自然不過的創作停頓下來的時候,想到的會是如同畫家大姊,自己為何而飛?或是傳承自母親的能力換作在自己的身上開展,又要如何能飛出自己的天空呢?
雖然片尾琪琪是因為男孩蜻蜓的生命危險而重新飛起掃帚,表面上是想要拯救一個讓她情感矛盾,可能愛戀的對象,所激發的動力,這也是電影慣用的奮不顧身英雄救美元素的翻版老梗,但我以為從琪琪在失落時,仍然可以從現實中汲取與自己有關的經驗,她並沒有因此放棄魔女做個凡人,她容許自己留白而重新銜接與生俱來的天賦,她也受到畫家大姊的啟發,沒有將當初攻擊她的烏鴉視為害怕的敵人,在充滿夏卡爾風的黑夜飛行畫作這幅畫中,琪琪與烏鴉是飛行的旅伴,魔女的側臉變形為長出馬匹耳朵及獅鬃的奇幻人獸,這代表內在擁有不同於之前,是有更異質更豐富的元素居於其中。
黑貓對琪琪而言,不僅是陪伴她不變的過渡客體如玩偶,它從寵物、玩伴變成一隻不再說話的貓,宮崎駿讓貓也隨著主角的改變而改變,貓也有屬於自己的蛻變。「心之谷」中貓的角色意義更多重而有意思,它可以是引發月島雯好奇尾隨進入想像世界的胖貓,當月島雯聽到老爺爺對她創作的評價時激動、哭泣,胖貓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打哈欠、走開,它也化身一面冷靜清楚的鏡子,讓敏感易於受挫的心回到平常心。還有擬人化為理想情人的貓男爵,牽領她上天下海開發其豐富的想像力。
相較於魔女琪琪逐漸下降到地面的真實處境,「神隱少女」千尋則反方向地上升到荒野半山腰上,一處被人類貪婪的慾望過度開發但終究圮倒如廢墟的虛幻城鎮中。千尋是被丟擲到那個莫名其妙的世界的。當她從熟悉的時空不得不離開,由於父母搬家的緣故,她的焦慮反應在與父母進入山洞時的怯步和依賴上,她需要緊抓著母親,才不會被來自陌生的巨大的害怕吞噬。她不是大膽又好奇的武陵人闖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裡,她脆弱的自我尚無法睜大眼睛,如同武陵人去觀察儼然屋舍阡陌交通。
在「神隱少女」的故事終點,父母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曾被變成豬,只有千尋知道,這個故事很像千尋獨自做了一個夢,夢醒時自己百感交集,懷疑著哪個是真實?哪個是虛幻?雖然只有自己能照見這心中的過程,但卻如此真實而有所領悟,而能用珍惜的角度面對父母。
這場千尋和觀者一同進行的夢也通往兒時的記憶,千尋一直感覺白龍似曾相識,沒想到卻是在年幼救過她的琥珀川堂主。
然而創作者在最後安排一個千尋不能回頭,否則回不到現實,類似奧菲斯之歌的橋段,回頭是一種無法承受在漆黑隧道裡的膽怯,無法忍耐暫時看不見光亮,或是擔心尤麗狄絲跟不上腳步強迫般忍不住確認。
千尋的夢遊仙境是不能以人的身份進入的,她忐忑不安地在宮殿外圍黑暗之中攀爬著樓梯,而在宮殿內則是各種生物神怪聚集,舉行著慶典、宴會、湯屋、迎財神活動等。人需要睡眠不被驚醒才能做夢通往潛意識,做夢時的人還是清醒時候的人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是的話會不會就進不到夢中了,千尋要取得進入宮殿裡的入場券是要變換一個自己,她需要找到一個工作的位置才能繼續做夢,如果她被發現是個人類,她或許也會被變成豬,或許她忘了自己是誰也忘了父母在哪,但是如果我們少做一個夢,損失的又是什麼?
如果事情可能像精神分析想得那麼複雜,那麼千尋對父母的情緒跑到哪裡了呢?如果和同學的關係得因為父母而分離,千尋難道不會對父母有一絲絲埋怨或不滿嗎?而父母轉變為豬該如何解釋呢?
將人物轉變為動物的創作手法並不罕見,在卡夫卡《變形記》中主角格里高變成甲蟲後的遭遇,卡夫卡讓主角的家人跟著他的創作一起荒謬,傳遞父母妹妹對變成甲蟲主角既厭惡又憐憫,既排斥又不捨的深刻情感。
我們可以理想化某人而讓偶像在心中永遠完美無瑕如媽祖,有沒有可能千尋對父母的難言情緒而將父母的形象轉變為豬呢?當然許多人大可以反駁父母是自己因為貪吃而被懲罰,這跟千尋有何關係呢?不過既然心理玄妙的力量可以引領創作者,將想像中千尋的父母變成豬,那麼容許觀者揣摩主角的心理的深井,有沒有甚麼大大小小的石頭也不為過吧!
或許有許多理由讓千尋在心中想攻擊父母,而一旦千尋攻擊的願望成真(就讓他們變成豬好好吃吧!或他們只是豬不會是我的父母......),父母不只變成豬還不見失蹤了,這樣所引發的罪咎感會不會也讓千尋開啟她的尋找歷程,尋求修復,讓心裡的父母得以延續,不會真正消失。
父母擁有瘦小千尋所訝異的胃口,這正是小孩難以跨越進入大人世界的差距。如果把大人小孩之間的距離擴大到如格理佛遊記中,船長在小人國裡如何被小人們對待,小人國皇帝驚訝於船長高聳如天的身材及造就此等巨人身材的食慾,皇帝下令京城方圓九百里之內的村莊,每早送來六頭牛、四十頭羊和其他零零總總的食物。父母吃不停的貪婪,一部份也可能是千尋尚無法理解的大快朵頤。
千尋在片中除了吃白龍給的飯團外,沒有吃任何食物。如果把千尋視為拒食的孩子,當她意識到自己找不到父母,只剩下白龍可以幫忙她或是至少有白龍願意幫忙她,她開始吃了第一口飯團,胃口也可能是意識
到自我匱乏的顯現
一個被分析者說,父親拼命叫我吃,我其實很餓,但不知道為何就是吃不下。
千尋吃了第一口飯團開始落淚,情緒潰堤,但也就開始一口一口吃了起來。或許是現在才開始感受到自己少了父母,才瞭解到對他們的依賴與渴求,亦或是白龍施予飯團的魔法,讓千尋感受到自己也如同父母擁有食慾,不再否認。因為難過,不僅不會吃不下,更謙虛地吃了起來。
貪吃作為一種失控的慾望此主題在片中不斷出現,除了千尋父母帶著孩子卻只顧自己吃之外,還有無臉男無底洞的吸盤,吞入一切卻只是囫圇吞棗,最後又原封不動地吐出,或是腐爛神扮演著清除人類製造的各式汙染的善心角色,但得定期到浴池泡藥休憩。
再更擴大來看,食慾也只是眾多慾望的代表,如果父母的食慾已如此讓千尋吃不消,更遑論父母的其他慾望,會帶給千尋多少驚恐,湯婆婆正是其他慾望展現的代表人物,她控制員工、奪取他們的名字、對金錢的追逐;千尋所進入的花花世界,各路人馬競逐著各種慾望,但自始至終,千尋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
白龍對千尋說:「吃了藥丸,才不會變成透明的。」變成透明是自我消失的前兆,君不見緩行於水鄉澤國的列車上的乘客均是透明的,他們在沒有任何城鎮屋舍規模,只有孤伶伶的車站下車,千尋在車上看見一群無家可歸的漂泊幽魂。
另一個自我消失的警訊來自於名字的遺忘,「忘記名字就回不去人間了。」這句銘刻在白龍命運的切身之痛,也同時提醒著千尋,當湯婆婆看到荻野千尋這個名字說到:「這是個奢侈的名字」,之後拿掉荻野尋,只剩千。千尋用藝名小千在湯婆婆手下做事,這是一個勤勉低調的工作藝名,但藝名不是真正的名字,藝名用久了會忘記自己究竟是誰。白龍忘記自己的名字,不過白龍還能記得自己忘記了名字,如果連遺忘什麼這個某個關乎自我的連結都忘了的話,可就萬劫不復了!
名字是「自己究竟是誰」的疑問,也是「自己從何而來」的源頭,白龍替小千找到她的本名,藉著留下當初進入奇幻宮殿前,現實生活中同學寫給她的離別紀念卡。分開並沒有被忘記,千尋可以在與同學分離後仍被記住,或是在心中留一個空間記住對方,於是自我被某種記憶方式留下來;完全不記得,通常是分離太痛苦的否認,記得一清二楚又讓人陷進虛妄中,無法獲致新的經驗,這個一丁點的記憶召喚千尋從虛幻走進現實。
名字通常也是父母取的,少女不願忘記自己叫做千尋,就如同她身陷在暗黑陌生的城市街道上,看見父母變成豬隻後,仍不願放棄尋找他們;會不會是這種尋找源頭的力量,抵禦了千尋面對鬼魅重重的害怕,讓她勇敢地追尋下去
千尋轉變的條件雖在虛構的宮殿之中,卻是紮紮實實的工作。以她的年紀和生命經驗,從來沒做過什麼工作,也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工作,卻得照白龍的意思,假裝「自己要工作」,才能被湯婆婆接受,而在湯婆婆經營的宮殿裡,找到一個位置生存下來。如果借用Esther Bick對於人格如何凝聚的理論,嬰兒會尋求一種相當於包覆身體肌膚的精神肌膚,藉此創造出一種感覺,讓他最初始的人格結構可多少因此得以凝聚,也就是「次級肌膚」。千尋雖不是嬰兒,但被拋擲到這個陌生機構,心情如嬰兒般潰散無依,她在父母失蹤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形體褪色透明,如同重新經驗初生時,子宮外危機四伏的焦慮狀態,四周都是威脅其生存,可能嗅出她的「人」味的敵人生物,藉由大姊小玲暫教給她的工作守則,會不會如「次級肌膚」雖僵化不是真我,但也抵禦了眼前的困難而保留了殘存的真我?
千尋得先用「假裝」來換取入場券,好像自己已經成為另一個角色。相較於假裝地很生澀的千尋,白龍顯然已經自在地遊走在原始真實的自己和工作假裝的自己之間,像個明確的開關沒有遲疑。溫尼考特說明了真實與虛假自我的不同名稱,用來指有的人把自己劃分為介於靈巧適應於外在客體的部分,和一個真實但完全主觀的生活。這似乎是千尋的一種考驗,她是要維持一個原有但已經發現缺陷的手足無措的存在(父母變成豬不見了),還是變成一個很職業性沒有自己感覺就跟其他人一樣就好的角色?
湯婆婆具有眾多奇特的魔法,例如變成鳥可以飛翔、任意移動物品、封住千尋的嘴巴、讓被控制的人失去記憶、利用改變名字的法術,控制員工的心智。這些魔法似乎都建立在他人對她的需要上,她看見人性的匱乏與貪婪,她利用了這些人性建立她的事業王國。白龍想跟她學習魔法,所以幫她偷錢婆婆的貴重印章,員工們想要更多的金錢,有錢能使鬼推磨,同時金錢也控制了湯婆婆去接待惡臭但有錢的腐爛神,千尋也需要湯婆婆找到將父母變回人形的方法。
然而她雖控制了身邊大多數人的心智行為,她的魔法卻無法幫她面對兒子的哭鬧索求,湯婆婆物慾盈身、財大氣粗的形象,顯然無法去做一個溫尼考特描述的「夠好的母親」,「夠好的母親」得要配合小嬰兒的需求,隨著嬰兒的適應力和挫折忍受力增加,母親的主動配合會慢慢減少,嬰孩的成長才會啟動,而無法由來自大人無時無刻餵養形成。
她養育出一個虛胖的「巨嬰」,可能她的魔法讓她以為在兒子面前,她依然能創造出的無止境被依賴的全能幻想,電影中的嬰兒可以長得比成人高壯許多,是母親湯婆婆創造出來的幻覺,這個幻覺一下子就被錢婆婆的另一套魔法點破。
如果這是由她所養育的孩子,她被自己始終和嬰孩一體的母性幻術所惑,她看不見巨嬰變成老鼠後,仍是她的孩子,雖然她擁有有多魔法,很可悲的卻看不到自己孩子真實的個性何在。
在「神隱少女」片尾魔法逐漸被破除。黃金其實是泥巴變的,握有魔法的人,卻看不見最簡單的事實。錢婆婆邊打毛線邊說:「用魔法做的,一點用都沒有。」許多童話故事在破除魔法中,還原出動物形體下,人真實的樣貌。不過不管是青蛙被扔下牆壁或是野獸被美女的眼淚解除魔咒,卻都變成了英俊王子,這往往又是另一件浪漫情懷所形塑的魔術。
佛洛伊德對「幻想」基本功能的看法為,用來填補慾望和滿足之間的空隙;在人的初期,這個空隙中流動的往往是全能幻想,有時也是許多幻覺。湯婆婆、錢婆婆、無臉男和白龍,他們各自的魔法代表各自怎麼樣的幻想或全能幻想?裡頭唯一沒有魔法的千尋,卻無懼無臉男的吞食,因為她對黃金的沒有慾望,不受制於無臉男。如同蘇菲並不害怕被荒野女巫施予魔法,一夜白髮雖然使蘇菲擔憂,但心裡的慈愛母性反而找到共振的形體,受制於魔法與被自己無法掌握的慾望依存有關。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給孩子的夢想飛行器:宮崎駿與精神分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心理學理論 |
$ 312 |
精神分析 |
$ 315 |
概論/入門 |
$ 315 |
精神分析 |
$ 315 |
社會人文 |
$ 315 |
心理學理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給孩子的夢想飛行器:宮崎駿與精神分析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發展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在地運動,從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看到、聽到的素材: 動畫」出發,正如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還是一個年輕的、正在起步的組織的發展歷程一樣,從我們熟悉並且感興趣的素材出發並且嘗試述說、書寫,也是精神分析對於自我本質探索的一種實踐。
進行到第二年的精神分析應用的講座,邀請了幾位願意嘗試各種精神分析式書寫可能性的會員,完成了這樣一部小書。在這本書裡,王明智心理師深入「風起」這部動畫,從風的聯想到「生死」與「侘寂美學」,以動畫內容為材料述說他對於生死的想像;蔡昇諭醫師以「魔女宅急便」中少女琪琪法力的失去與重拾以及「神隱少女」千尋經歷的冒險故事,連結宛若精神分析歷程中重新經歷成長過程的經過;林怡青醫師用一種自在的書寫方式,從「霍爾的移動城堡」這部作品進行聯想,述說她個人精神分析的治療經驗與閱讀經驗,故事中的角色在她細膩的文筆下,也一一找到精神分析理論的位置;彭奇章心理師深入宮崎駿作品中,重要的「飛行」主題,從「降臨、降落、墜落」等飛行相關身體經驗出發,探究來自於嬰兒時期的身體經驗以及幻想形成的根源。本書中每位作者各種書寫的形式雖然迥異,但也證明了「創造精神分析式的書寫」非常豐富而多元的可能性。無論是否熟悉宮崎駿的動畫或者是否熟悉精神分析,我想都能在其中享受難得的閱讀經驗。
作者簡介:
王明智/單瑜/蔡昇諭/林怡青/彭奇章/唐守志等六人。
TOP
章節試閱
宮崎駿的魔法世界 : 遺失的創造力 /蔡昇諭(精神科醫師)
………………
精神分析是ㄧ種人在生命中自主地按下慢轉,暫停甚至倒轉的狀態,我們想著某個片刻的自己,琪琪的母親看著琪琪準備離家,驚訝之餘也讓母親本人的思緒倒轉到自己曾經離家的記憶中。
父母親和周圍的鄰居,也像參加某種畢業典禮的場合,見證這一刻的到來。生命之中,有些改變命運的事件出現,某些注定,但也又有一些未知數,等待人運用自己的潛力或特質前進。
電影版中稍微仔細交代了父母親的出生背景,父親是人類,母親是魔女,如果在哈利波特,這樣魔法師和麻瓜(一...
………………
精神分析是ㄧ種人在生命中自主地按下慢轉,暫停甚至倒轉的狀態,我們想著某個片刻的自己,琪琪的母親看著琪琪準備離家,驚訝之餘也讓母親本人的思緒倒轉到自己曾經離家的記憶中。
父母親和周圍的鄰居,也像參加某種畢業典禮的場合,見證這一刻的到來。生命之中,有些改變命運的事件出現,某些注定,但也又有一些未知數,等待人運用自己的潛力或特質前進。
電影版中稍微仔細交代了父母親的出生背景,父親是人類,母親是魔女,如果在哈利波特,這樣魔法師和麻瓜(一...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創造精神分析式的書寫 / 單瑜
2016年11月5日,臺灣精神分析學會舉辦的精神分析應用的活動邁入
第二屆,就如蔡榮裕醫師所說的,2015年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所舉辦的「村上
春樹與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應用在臺灣的一個起頭,那麼我們從此刻開始
已經邁開步伐往前跨進。
在佛洛伊德時代「藝術創作」在他大量的精神分析書寫中大概有幾種呈現,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博學的佛洛伊德在他作品中時常信手拈來的歐洲文學與文藝典故,豐富而廣泛的引經據典往往讓後世的讀者需要有詳細註解,才能夠深入理解佛洛伊德引用文字的相關背景。另外一類的作法...
2016年11月5日,臺灣精神分析學會舉辦的精神分析應用的活動邁入
第二屆,就如蔡榮裕醫師所說的,2015年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所舉辦的「村上
春樹與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應用在臺灣的一個起頭,那麼我們從此刻開始
已經邁開步伐往前跨進。
在佛洛伊德時代「藝術創作」在他大量的精神分析書寫中大概有幾種呈現,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博學的佛洛伊德在他作品中時常信手拈來的歐洲文學與文藝典故,豐富而廣泛的引經據典往往讓後世的讀者需要有詳細註解,才能夠深入理解佛洛伊德引用文字的相關背景。另外一類的作法...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創造精神分析式的書寫 單瑜
風起與風落:關於生死的一些聯想 王明智
宮崎駿:動畫界的達文西 單瑜
遺失的創造力:談宮崎駿的魔法世界 蔡昇諭
霍爾的移動城堡...
風起與風落:關於生死的一些聯想 王明智
宮崎駿:動畫界的達文西 單瑜
遺失的創造力:談宮崎駿的魔法世界 蔡昇諭
霍爾的移動城堡...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明智、單瑜、蔡昇諭、林怡青、彭奇章、唐守志等六人
- 出版社: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01 ISBN/ISSN:97898692972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1頁 開數:32開(13.7*21cm)_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