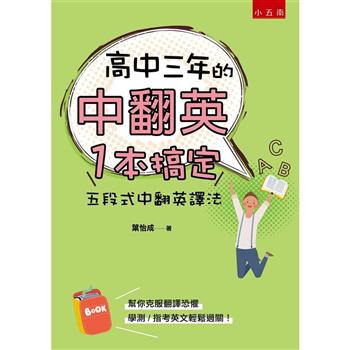這是一本談論心理治療技術的書,是多年臨床實作和精神分析理論相互呼應的結晶。
它不是一本有問有答的操作手冊,不可能從本書知道個案說什麼後,我們就回應什麼,而是討論和思索,技術裡的理論和理論裡的技術。
因為,沒有技術這件事,有的是,理論和技術的對話合體。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技術篇)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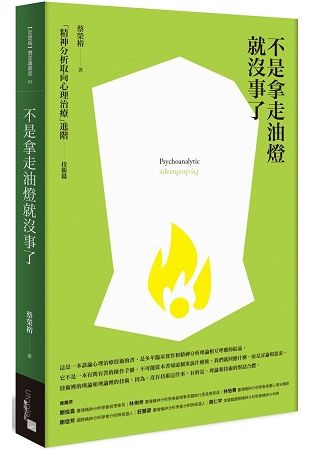 |
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技術篇) 作者:蔡榮裕 出版社: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0 |
二手中文書 |
$ 340 |
心理治療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心理學理論 |
$ 360 |
心理治療 |
$ 360 |
社會人文 |
$ 360 |
個案分析與諮商輔導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技術篇)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蔡榮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成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委員會副主委
<簡介>
蔡榮裕醫師,學生時代參與高醫大學《阿米巴詩社》,之後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目前的松德院區)開始精神科的工作,期間與同儕創立《採菊東籬下》和《思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小組》為名的團體及刊物,陸續發表大量文字作品,大多圍繞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間或有一些文藝創作。他的文字風格特異,下筆又如有神,其篇幅常常是同儕裡占最大比例,是最勤於寫作的一位。1998年赴英,至Tavistock Clinic專攻精神分析,兩年後學成歸國,帶動一批年輕精神科醫師前仆後繼、負笈英倫學習精神分析的熱潮。
蔡醫師從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的專業領域,到詩、散文、小說及戲劇的文學創作,乃至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大議題,永遠有源源不絕的思想靈感。其中,與林玉華教授前後耗費十年合譯完成的精神分析皇皇巨著——《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1945),更是經典的里程碑。
2004年蔡醫師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共同創立「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同時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連上線,經過十來年的辛勤奮鬥,終於在2015年 7 月正式以Taiwa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名稱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機構,此後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地方以自己的語言進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認可的分析師訓練。
蔡榮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高雄醫學大學《阿米巴詩社》成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委員會副主委
<簡介>
蔡榮裕醫師,學生時代參與高醫大學《阿米巴詩社》,之後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目前的松德院區)開始精神科的工作,期間與同儕創立《採菊東籬下》和《思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小組》為名的團體及刊物,陸續發表大量文字作品,大多圍繞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間或有一些文藝創作。他的文字風格特異,下筆又如有神,其篇幅常常是同儕裡占最大比例,是最勤於寫作的一位。1998年赴英,至Tavistock Clinic專攻精神分析,兩年後學成歸國,帶動一批年輕精神科醫師前仆後繼、負笈英倫學習精神分析的熱潮。
蔡醫師從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的專業領域,到詩、散文、小說及戲劇的文學創作,乃至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大議題,永遠有源源不絕的思想靈感。其中,與林玉華教授前後耗費十年合譯完成的精神分析皇皇巨著——《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1941-1945》(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1945),更是經典的里程碑。
2004年蔡醫師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共同創立「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同時與「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連上線,經過十來年的辛勤奮鬥,終於在2015年 7 月正式以Taiwan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名稱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訓練機構,此後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地方以自己的語言進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認可的分析師訓練。
目錄
推薦序
劉佳昌 / 青山高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
林俐玲 / 尋寶的歷程
林怡青 / 是煉金師還是馬拉松跑者? 精神分析這條路
謝佳芳 / 那些言語到不了的地方
莊慧姿 / 守護分析治療的勇士
周仁宇 / 人生無常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經驗談(小小說)
第一章 其實,我真的不懂你
第二章 你又來了,是什麼意思?
第三章 需要有綠洲的中間地帶
第四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的可能性?(上)
第五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可能性?(中)
第六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可能性?(下)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技術篇)
治療技術的12堂課 / 詮釋 . 行動 . 阻抗 . 修通
第一堂 關於創傷/這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技術嗎?
第二堂 分析的金和暗示的銅/「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基礎結構
第三堂 梗在喉嚨裡努力做自己/治療技術需要什麼地圖?
第四堂 回到佛洛伊德/從挫敗的地方開始
第五堂 失望的胃口吞不下東西,如何招待它?
第六堂 以「朵拉」為例的想像/從暗示到詮釋的光譜距離
第七堂 是驅魔或感恩?/回到暗示與建議
第八堂 臨床案例/思索診療室外的某些「行動化」
第九堂 哥白尼.達爾文.佛洛伊德/關於自戀的想像和技藝
第十堂 三位精神分析師主張的技藝/從歷史裡修改影子
第十一堂 理想性的困境和節制/超我作為主人的技藝
第十二堂 我要在一條舊毯子上活出自己/需要什麼技藝?
跋
劉佳昌 / 青山高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
林俐玲 / 尋寶的歷程
林怡青 / 是煉金師還是馬拉松跑者? 精神分析這條路
謝佳芳 / 那些言語到不了的地方
莊慧姿 / 守護分析治療的勇士
周仁宇 / 人生無常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經驗談(小小說)
第一章 其實,我真的不懂你
第二章 你又來了,是什麼意思?
第三章 需要有綠洲的中間地帶
第四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的可能性?(上)
第五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可能性?(中)
第六章 抱怨裡有多少人生可能性?(下)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進階(技術篇)
治療技術的12堂課 / 詮釋 . 行動 . 阻抗 . 修通
第一堂 關於創傷/這是精神分析取向的技術嗎?
第二堂 分析的金和暗示的銅/「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基礎結構
第三堂 梗在喉嚨裡努力做自己/治療技術需要什麼地圖?
第四堂 回到佛洛伊德/從挫敗的地方開始
第五堂 失望的胃口吞不下東西,如何招待它?
第六堂 以「朵拉」為例的想像/從暗示到詮釋的光譜距離
第七堂 是驅魔或感恩?/回到暗示與建議
第八堂 臨床案例/思索診療室外的某些「行動化」
第九堂 哥白尼.達爾文.佛洛伊德/關於自戀的想像和技藝
第十堂 三位精神分析師主張的技藝/從歷史裡修改影子
第十一堂 理想性的困境和節制/超我作為主人的技藝
第十二堂 我要在一條舊毯子上活出自己/需要什麼技藝?
跋
序
推薦序
尋寶的歷程
林俐伶
這是一本為臨床經驗整理立論的書。
點亮油燈,翻開書頁,當我們手執一本這樣的標題的書,我們有期待嗎?可能的期待又是什麼呢?你也許以為你找到了一本食譜,一份菜單,人稱「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這就是我們的期待嗎?如果這本書像菜單,會不會教人失望?它如果不像菜單,是否也教人失望?
從病人的抱怨與諮詢開始,佛洛伊德為了回應對方,加上對症狀、對人心的好奇,他開始思考並運用可能可以與個案工作的臨床技術,接著透過觀察與思考技術與人的互動內涵,佛洛伊德開始建構理論。這三大元素:臨床資料、分析技術、理論建構,充斥著他創建精神分析的整個過程,他在此間不停地思辯、與人交流,書寫自己的想法再駁倒自己的想法,層層堆疊,寫了二十四卷,成一家之言。
這本書似是如上過程的縮影,和蔡榮裕醫師潛意識叢書的前四本不太一樣,少了詩意,多了許多重要的智性內容與人性關懷。讀者讀著這本書,比較有可能的是,在最初翻開的數頁,甚至數十頁,給人一種怎麼對人是既了解卻又不了解,懂卻又不懂的情況?感覺不是很容易進入蔡醫師的思緒脈絡,但是,跟著文字,要隨心所欲地緊跟著(這句話怪怪的,不過卻是一個分析治療者頗為理想的工作狀態),可以發現慢慢地產生一種處處拾穗的經驗,閱讀此書,有點像爬上了一座物產豐饒的島嶼,邊走邊認識那一切映入眼簾的,有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駐足做著自己的聯想。聽蔡醫師說過幾回:「腳下所踩的所在就是一個人想要在的地方。」這句話是一個在閱讀此卷時可以運用的態度:眼前所見的就是我要讀的、要想的、要感受的、甚至質疑的。蔡醫師在字裡行間完全地打開了這些可能性。
本書中,蔡醫師對幾個固有的技術觀,包括分析的金所意指的移情詮釋、中立的態度等概念進行審視,並且對於使用僵硬的認識論看待它們的態度發出質疑,在此質疑中,也許就改變了一個臨床家看人的角度,那裡面滿是慈悲。比方說,他以描述變性人可能有的內在心理經驗去了解個案在治療場域中「退回」到自己的世界的行動動力,直接展現的可能只是對於做治療花費了他的時間與金錢的抱怨,但某部分卻可能是深層內在難以與他者連接上的無奈與絕望,個案既然「退」,我們要不要考慮「進」?因此,蔡醫師提出了「邀請的態度」,認真者如他,絕不會簡單發明介紹一個新概念就算了,前前後後的,讀者會讀到「暗示的銅」的歷史地位及實用性,還會讀到費倫齊(Ferenczi)的「主動技術」,葛林提議的主動的態度,當然也不乏古典的「分析的態度」,克萊恩看待自戀與死亡本能與自體心理學對自戀的專研等等。他在書中描寫了許多觀察,提出一些問題,舉出不少的例子和比喻,例如:以夢境作為治療互動或外在現實的比喻,然後再回到精神分析歷史與理論以及對台灣現有的臨床經驗做些理解與辦證的歷程,這幾個元素,就如同分析治療經驗一樣,不是以穩定的連續性出現,而是以高度的複雜性,還有一種廣泛性的風格,在文字間以一圈又一圈渦輪般的形式展現,時而重疊,時而停駐轉而論述另一個概念,時而以嶄新的比喻展露頭角,蔡醫師的寫作風格呼應著他文章中提到的:「從『分析的金』到『暗示的銅』之間,有一片值得被探究的場域,如溫尼科特所說的『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或我想用的『餘地』,留有餘地的餘地,可以在僵局裡再創新的領域。」
從蔡醫師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直接地感受到精神分析的「創新」不是憑空的,那裏面有著身為一個人原本帶來這世上的和他的生命歷史軌跡中的經驗,使得一個人的內心還存有著更多更多的人的思緒,包雜著當下所受的苦,在治療中,隱隱的期待能「蛻變」(transformations),在移情中蛻變。但如果我們思考蛻變歷程,蔡醫師提醒我們:「生命早年的真正記憶,並不是在口說的故事裡」,也就是老祖宗佛洛伊德所說的,真正的記憶是在行動裡,而且是重複不止的行動(關係模式),但精神分析的工具是語言啊!當某種語言方式和行動接不上時,分析治療師的意願為個案去臆測、去了解有著關鍵的重要性。書中提到,佛洛依德說他的 ......「後設心理學是一種猜測......不是和個案打轉一輩子的人所做的謙虛陳述,而是作為精神分析師或分析治療師,面對『臨床事實』(clinical facts)所真實經驗到的感受。精神分析師和分析治療師對於個案內心世界的探索,唯一的工具是猜測......作為分析治療師,沒必要對於自己的作為大都是猜測而感到汗顏,因為這是臨床事實,而唯有面對這種具有主觀且猜測的性質,分析治療師才能仔細傾聽個案的故事。」在這樣的傾聽態度之下,很自然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會以另一種新的語言方式建立,因此「回到當刻的脈絡」,「中立並非冷漠」而「詮釋是一種聯結」,這些蔡醫師提出的原則得以增進分析歷程的豐碩,語言和情感生成一種關係,而其中的感受能直接賦予語言在精神分析以及分析治療過程中,在人生其他遭遇裡不會有的獨特生命力。
最後,我特別想說的是在談到比昂提的要追求真實感(sense of truth)的重要性時,蔡醫師很令人動容地寫到:「生為一朵花就是拼命要開出花,不論是否有石頭壓著,也因為有監督者的存在而讓表現的美學和手段有了多樣性。」我們讀這本書,會是這樣的一種尋寶的歷程,撿拾著一則則的臨床情境,一段段的理論概念分享,時而出現的對技術的省思與創見。綻放,在走走停停、尋尋覓覓、細細思想中輕巧地發生。
(作者:林俐伶。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副理事長暨執行委員會委員、美國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秋隱精神分析工作室負責人)
尋寶的歷程
林俐伶
這是一本為臨床經驗整理立論的書。
點亮油燈,翻開書頁,當我們手執一本這樣的標題的書,我們有期待嗎?可能的期待又是什麼呢?你也許以為你找到了一本食譜,一份菜單,人稱「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這就是我們的期待嗎?如果這本書像菜單,會不會教人失望?它如果不像菜單,是否也教人失望?
從病人的抱怨與諮詢開始,佛洛伊德為了回應對方,加上對症狀、對人心的好奇,他開始思考並運用可能可以與個案工作的臨床技術,接著透過觀察與思考技術與人的互動內涵,佛洛伊德開始建構理論。這三大元素:臨床資料、分析技術、理論建構,充斥著他創建精神分析的整個過程,他在此間不停地思辯、與人交流,書寫自己的想法再駁倒自己的想法,層層堆疊,寫了二十四卷,成一家之言。
這本書似是如上過程的縮影,和蔡榮裕醫師潛意識叢書的前四本不太一樣,少了詩意,多了許多重要的智性內容與人性關懷。讀者讀著這本書,比較有可能的是,在最初翻開的數頁,甚至數十頁,給人一種怎麼對人是既了解卻又不了解,懂卻又不懂的情況?感覺不是很容易進入蔡醫師的思緒脈絡,但是,跟著文字,要隨心所欲地緊跟著(這句話怪怪的,不過卻是一個分析治療者頗為理想的工作狀態),可以發現慢慢地產生一種處處拾穗的經驗,閱讀此書,有點像爬上了一座物產豐饒的島嶼,邊走邊認識那一切映入眼簾的,有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駐足做著自己的聯想。聽蔡醫師說過幾回:「腳下所踩的所在就是一個人想要在的地方。」這句話是一個在閱讀此卷時可以運用的態度:眼前所見的就是我要讀的、要想的、要感受的、甚至質疑的。蔡醫師在字裡行間完全地打開了這些可能性。
本書中,蔡醫師對幾個固有的技術觀,包括分析的金所意指的移情詮釋、中立的態度等概念進行審視,並且對於使用僵硬的認識論看待它們的態度發出質疑,在此質疑中,也許就改變了一個臨床家看人的角度,那裡面滿是慈悲。比方說,他以描述變性人可能有的內在心理經驗去了解個案在治療場域中「退回」到自己的世界的行動動力,直接展現的可能只是對於做治療花費了他的時間與金錢的抱怨,但某部分卻可能是深層內在難以與他者連接上的無奈與絕望,個案既然「退」,我們要不要考慮「進」?因此,蔡醫師提出了「邀請的態度」,認真者如他,絕不會簡單發明介紹一個新概念就算了,前前後後的,讀者會讀到「暗示的銅」的歷史地位及實用性,還會讀到費倫齊(Ferenczi)的「主動技術」,葛林提議的主動的態度,當然也不乏古典的「分析的態度」,克萊恩看待自戀與死亡本能與自體心理學對自戀的專研等等。他在書中描寫了許多觀察,提出一些問題,舉出不少的例子和比喻,例如:以夢境作為治療互動或外在現實的比喻,然後再回到精神分析歷史與理論以及對台灣現有的臨床經驗做些理解與辦證的歷程,這幾個元素,就如同分析治療經驗一樣,不是以穩定的連續性出現,而是以高度的複雜性,還有一種廣泛性的風格,在文字間以一圈又一圈渦輪般的形式展現,時而重疊,時而停駐轉而論述另一個概念,時而以嶄新的比喻展露頭角,蔡醫師的寫作風格呼應著他文章中提到的:「從『分析的金』到『暗示的銅』之間,有一片值得被探究的場域,如溫尼科特所說的『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或我想用的『餘地』,留有餘地的餘地,可以在僵局裡再創新的領域。」
從蔡醫師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直接地感受到精神分析的「創新」不是憑空的,那裏面有著身為一個人原本帶來這世上的和他的生命歷史軌跡中的經驗,使得一個人的內心還存有著更多更多的人的思緒,包雜著當下所受的苦,在治療中,隱隱的期待能「蛻變」(transformations),在移情中蛻變。但如果我們思考蛻變歷程,蔡醫師提醒我們:「生命早年的真正記憶,並不是在口說的故事裡」,也就是老祖宗佛洛伊德所說的,真正的記憶是在行動裡,而且是重複不止的行動(關係模式),但精神分析的工具是語言啊!當某種語言方式和行動接不上時,分析治療師的意願為個案去臆測、去了解有著關鍵的重要性。書中提到,佛洛依德說他的 ......「後設心理學是一種猜測......不是和個案打轉一輩子的人所做的謙虛陳述,而是作為精神分析師或分析治療師,面對『臨床事實』(clinical facts)所真實經驗到的感受。精神分析師和分析治療師對於個案內心世界的探索,唯一的工具是猜測......作為分析治療師,沒必要對於自己的作為大都是猜測而感到汗顏,因為這是臨床事實,而唯有面對這種具有主觀且猜測的性質,分析治療師才能仔細傾聽個案的故事。」在這樣的傾聽態度之下,很自然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會以另一種新的語言方式建立,因此「回到當刻的脈絡」,「中立並非冷漠」而「詮釋是一種聯結」,這些蔡醫師提出的原則得以增進分析歷程的豐碩,語言和情感生成一種關係,而其中的感受能直接賦予語言在精神分析以及分析治療過程中,在人生其他遭遇裡不會有的獨特生命力。
最後,我特別想說的是在談到比昂提的要追求真實感(sense of truth)的重要性時,蔡醫師很令人動容地寫到:「生為一朵花就是拼命要開出花,不論是否有石頭壓著,也因為有監督者的存在而讓表現的美學和手段有了多樣性。」我們讀這本書,會是這樣的一種尋寶的歷程,撿拾著一則則的臨床情境,一段段的理論概念分享,時而出現的對技術的省思與創見。綻放,在走走停停、尋尋覓覓、細細思想中輕巧地發生。
(作者:林俐伶。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副理事長暨執行委員會委員、美國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秋隱精神分析工作室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