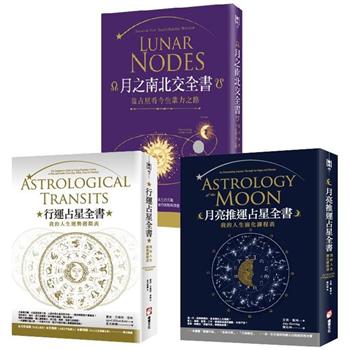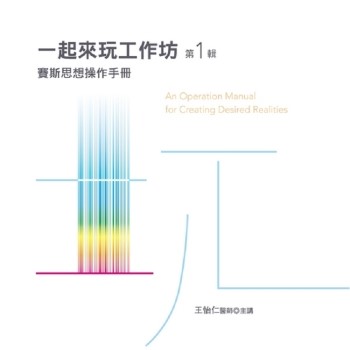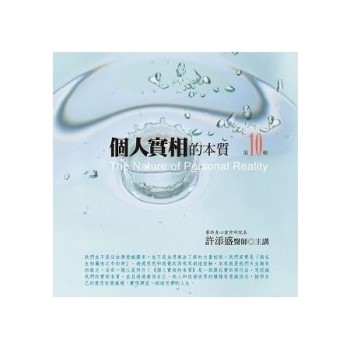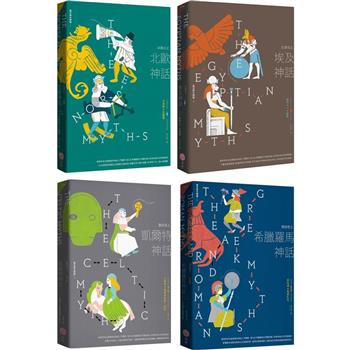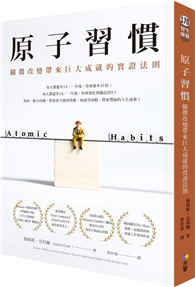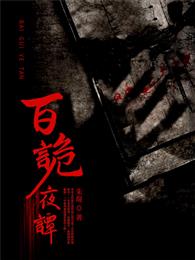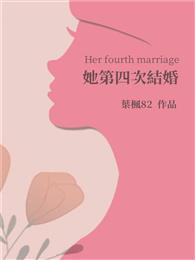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
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吳承恩,《西遊記》
課程進度:何謂「犧牲」?
*研讀範圍: M-4.I & M-13
約莫十天前的一個晚上,正當好夢方酣,忽然間卻醒覺過來,耳朵裡傳來一個聲音:「去找《西遊記》吧!那是年後上課的絕佳教材!」三天之後,我就到書店裡買了一本原版的《西遊記》,利用年假期間讀了大半。果然那一念所言不虛,裡頭盡是趣味橫生的活教材,有寓言、有詩詞、有笑料,恰好也對得上年後新開的主題──犧牲與特殊之愛。
《西遊記》是我這輩子除了《奇蹟課程》之外讀過最多回的一本書。不過小時候讀的是兒童版,直到現在才真正把原著讀上一遍。八、九歲的時候我就著迷於孫悟空的出神入化和百般武藝,一本兒童版《西遊記》翻過十幾回,連皮都差點要掉下來。直到二十年後,裡頭的情節還隱約能記得大半。
小時候讀的是情節,長大之後看的是隱喻和象徵。《西遊記》顯然是一部談修行的小說;既是小說,總會有人物和情節,有時還開展成一趟外在的旅程,但一切外在的旅程反應的必然是內在的成長和轉化。小說如此,現實生活裡邊大抵也是如此。光看作者的用字遣詞就有三分明白了:「心猿意馬」這個成語頻繁地出現,「猿」指的是孫悟空,「馬」指的是唐僧的坐騎白龍馬,可可孫悟空當年在天庭也是個管馬的弼馬溫。「心猿意馬」本指雜念紛飛的狀態,在小說裡卻成了心靈必須統攝意念的象徵,隱喻的是心靈的修持和鍛鍊。
孫悟空在《西遊記》裡是個鮮明突出的角色,雖是個虛構的人物,至今仍有「齊天大聖廟」在拜他。七十二變化和好動惡靜的自性可說象徵著我們的頭腦,一分鐘裡就可以轉過成千上百的念頭,並且難以止息。唐僧從五行山下救出孫悟空之後給他取了「行者」之名,便是要他一步一腳印地走在修行的道途上;雖然筋斗雲一翻身就有十萬八千里,但頭腦的望想和造作畢竟不能取代心靈的鍛鍊。孫悟空雖然神通廣大,自封為齊天大聖( 真是好大的口氣),天庭裡畢竟難容這等倨傲:與天(上主)同齊,這不正是小我最隱微的私欲嗎?上西天取經不僅路途遙遠,而且鬼魅叢生、危機四伏,唐僧一行人碰上的妖怪可說都是「心魔」的化身。若真想求得解脫,就不能規避心魔,反而要各個擊破。頭腦往往會藉著理智化來逃避面對這些心魔,但這是不成的。唯有死心塌地、一步一腳印地行將去,才終有斷除煩惱的一天。
這一週研讀的M-4.I 便是耶穌親身的修行經歷。真正躬身實踐寬恕的人就會知道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歷程,因此讀來心有戚戚焉,字字血淚。看來耶穌也曾經是個凡人,就和你跟我一樣,但憑他的願心和決心,最終能夠達致超凡入聖的境界。他不但碰上了「心魔」,還與之周旋許久,險些無法脫身。修行路上的「心魔」到底是什麼呢?當我們仔細研讀「信賴形成的六個階段」,就會發現裏頭的關鍵字:犧牲與失落。除了第四和第六階段之外,這兩個關鍵字不斷地出現。而且,既然第四階段尚未達到真正的「完成」,表示犧牲的心魔還沒有完全斷除。似乎辛辛苦苦經歷了五個階段,面對的心魔總是同一個,就像寬恕來寬恕去,面對的小我也總是同一個一樣。
事實上,犧牲和失落只是不同的名詞,表達的卻是相同的意涵:假若寬恕了分裂之念,就要放下罪咎和恐懼,也就表示這個世界是個幻相,包括我們的自我和一切人間的欲樂。放下一切人間的欲樂、放下自我?!
聽起來可是莫大的犧牲!的確,但也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契入神的境界,回歸我們的實相──上主的完滿造化。畢竟實相和幻相是截然二分的,不可能保留一部份小我喜愛的幻相,卻又能同時回歸於實相。
既然耶穌也曾經是個凡人,當年他所面臨的內在掙扎或許不亞於我們。即使已經走過了四個階段,卻還會掉入第五個階段的「動盪期」。這段動盪期在神秘主義的文獻裡被稱作「靈魂的暗夜」(the dark night of soul)。因為在前四個階段裡我們還試圖保留並合理化自我和人間的欲樂。然而,最終卻發現這僅有的「一點點」仍需悉數捨去。此時內心裡升起的洶湧狂潮和抗拒可說是無以復加的。長夜漫漫,實在不曉得還要折騰多久才會到達目的地。
修行是個內在的旅程,通常需要相當的時間、精力、和紮實的鍛鍊。我們必須學習唐僧取經一步一腳印的精神,時時勤於拂拭,才能獲致真實的進步。然而,《奇蹟課程》也告訴我們,寬恕或者奇蹟並不需要時間──一切就只在一念之間。這兩件事看似矛盾,但實際上並無衝突。既然心魔是同一個,小我也是同一個,我們只要願意寬恕它就成了。因此,不管目前處在六個階段中的哪一個,該學習的功課是不會改變的。或許形式不同,但內涵則一;並不因為身處更高的階段,就得學習更「高階」的法門。
《奇蹟課程》徹頭徹尾就只教了「寬恕」一門。在靈性修持的過程裡,我們免不了要區分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什麼是我們真正想要,什麼又是我們不想要的。然而,犧牲或說特殊之愛之所以構成修行途中的難題,在於我們區分二者的方式。通常我們會很想把界線畫在特殊之愛跟特殊之恨的中間,我們很希望能夠同時保存無條件的愛和特殊之愛( 也就是有條件的愛),卻不明白,或說不願看明白這兩者根本是無法並存的。假使不願放下特殊之愛,習學再多法門、花費再多時間和精力,可說都是枉然。因此,真正的界線如下:事實上,人間的愛與恨必然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即使它們的形式可以千變萬化。這一點我們往後將能逐漸看清。不可能只丟掉一個銅板的一面而不同時丟掉另一面;同理,不可能只放下特殊之恨而不同時放下特殊之愛。《馬太福音》的第四章記載了耶穌接受魔鬼考驗的故事。顯然他最終面對的心魔仍是特殊之愛: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從《奇蹟課程》的觀點來看,在第一道考驗裡,耶穌給出如下的答覆:我不是一具身體,我是靈性。(靈性)生命的來源是神,而不是麵包。在第二道考驗中,耶穌抗拒了誤用心靈力量的誘惑,否則人都能死而復活了,如何不能從廟頂一躍而下?最後一道考驗則委實道出了小我的心聲:以特殊之愛來交換上主無條件的愛。然而,沒有人能夠腳踏兩條船,兩邊都要的結果就是落入小我的陷阱。
課堂上有同學問道,既然放下特殊之愛會引發巨大的犧牲感,那又該如何是好?事實上,耶穌在六階段中的第三階段就提供了解答,只怕我們讀了不免要感到失望:既然你害怕失落和犧牲,那就真的放下特殊之愛試試看!畢竟若不是親身嘗試,一切都只是想像而已,一場空。這有點類似心理治療中的「洪水法」,既然你害怕蟑螂,那就真的去跟蟑螂面對面看看。當我們真正鼓起勇氣親身嘗試,才會發現原先的擔驚受怕都只是小我想像出來的,根本就不存在。「心魔」根本就不存在!
犧牲感是小我鼓舌如簧的利器,它拚命要說服我們留住娑婆世界。然而,正因娑婆世界本是個幻相,因此放下這個世界根本算不上是什麼犧牲。一切犧牲與失落的感受都是尚未放下之前的想像,但我們怎能憑著小我來揣度天堂的境界呢?這就好比跟一個瞎子請教彩虹的顏色和美感一樣的可笑,是吧?事實上,放下這個世界恰好能剜除揮之不去的犧牲感和失落感,因為這個世界的本質就是無常──不斷不斷地走入失落與死亡,而且沒有任何人、事、物能夠例外。或者說,我們真正會「犧牲」的就只有犧牲!所謂「為道日損」(而且必須「損之又損」),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犧牲重大,實際上卻是真正的獲得──我們終於能夠回歸最純粹的平安、喜樂、和愛。你說,這不是真正的獲得,那是什麼呢?
犧牲的信念究竟是那兒來的呢?研讀《奇蹟課程》的要領,一者是以簡馭繁,二者是返本溯源,一切的問題和答案都必須在根源處找尋。是的,犧牲實際上就是分裂的內涵;當心靈選擇與上主分裂,以便在上主之外另行創造的時候,它就犧牲了完滿的自性,並且創造了自我概念。換句話說,自我便是犧牲了自性所換得的產物。然而,心靈將分裂和自我當真之後,卻在其中產生了巨大的罪咎和恐懼,從而掉入了自我詛咒(M-13.3);這是為什麼自我詛咒和自我會有所關聯的原因。
與上主一體的自性原是我們的實相,而我們視同己出的自我卻是個幻相。然而,認同分裂的心靈卻將自性視為是幻相,而將自我和娑婆世界認定是實相。自我概念原是虛空中的一念,待心靈投射出有形有相的娑婆世界之後,它便找了其中的一具形體與之認同。因此,當我們向人自我介紹的時候,講的不外乎就是這具身體。(順帶一提,《奇蹟課程》所講的「身體」或「形體」尚包括因投射而破碎成片片斷斷的心靈。)身體和特殊之愛在《課程》裡被耶穌稱作是「夢中的英雄」(M-13.2; T-27.VIII),那是自我的寄身之所,為的是要躲避心靈之中排山倒海而來的罪咎和恐懼。
想想我們從小的成長歷程,自出生、求學、工作、到成家,無一不是為了鞏固我們的自我。我們從一具赤條條的身體,到擁有衣物、金錢、房舍、和伴侶。這些佛書裡邊稱之為「我所」(也就是「我的」)的事物,事實上就代表了我們的自我。無怪「我」和「我所」在《阿含經》中往往是並稱的。然而,正因為選擇分裂、離開了完滿的愛必然成為一種自我詛咒,不論我們抓取再多的特殊之愛,總逃不了罪咎和恐懼的投射,乃至心靈內在的空虛。特殊之愛既然是幻相,便無法真正滿足我們的心靈,雖然我們好似擁有許多,也隨時準備再抓取更多。這便是「夢中英雄」的真相,也就是自我的真相。
許多心理學家和心理治療師窮盡畢生的精力研究自我的發展。他們不明白,無論自我再怎麼發展,必然都是一種自我詛咒。即使表面上好似能夠適應這個社會,甚至開展出種種自我價值,並獲取金錢、地位、和成就,它從不曉得什麼是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平安。它從不曉得什麼是真正的愛。自我必須離開這些遠遠的,就像蚊蟲撞見了青蛙一般,否則它就會掉入自性──那可是自我的窮途末路。因此,真實的靈性修持和真實的療癒必得朝向消解自我的方向,而非鞏固自我的路數,這也是為什麼傳統的心理治療無法真正療癒病人的原因。
《奇蹟課程》所教導的寬恕走的就是一條放下自我的道途。放下自我可說是靈性追尋最嚴峻的挑戰之一,然而,終能通過挑戰的人會發覺放下自我的確是天底下最愜意的事兒。把心靈鎖在身體裡頭,就好比一輩子住在一個暗無天日的小抽屜裡一樣地難受。只因我們習以為常,遂不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然而,若能舒展在陽光和新鮮的空氣之下,又何必堅持一定要住在臭水溝裡呢?其實無需如此,是不是?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奇蹟心旅:通往喜樂的21堂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0 |
二手中文書 |
$ 323 |
社會人文 |
$ 342 |
心理學理論 |
$ 342 |
心理學理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奇蹟心旅:通往喜樂的21堂課
本書是作者的上課筆記,他將《奇蹟課程》選出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運用「主題歸納」的方式,配合相關章節,再搭配許多淺顯易懂的圖解,藉此達到聚焦學習的效果。這在台灣還是個獨創之舉。藉由本書,作者期望能挖掘出《奇蹟課程》最深刻的內涵,盡可能地對其中文字做最綿密的探討,希望能將《奇蹟課程》的文字與生活經驗和操練的體驗加以結合。
無論你是否為《奇蹟課程》的學習老手,本書深入淺出卻縝密完善的解說,將帶給你非常不一樣的體驗。讓我們一起踏上這趟「奇蹟之旅」!
本書特色
*「潛意識結構」大解謎
* 打破靈性學習的迷思
*「主題歸納式」教學
* 清晰易懂的「圖文」解說
* 學習《奇蹟課程》的最佳工具書
作者簡介:
許自呈
一九八六年生於台灣,台大醫學系畢業,輔修哲學。曾任台大醫院住院醫師,因緣際會之下脫去白袍,專職教學《奇蹟課程》,足跡遍布宜蘭、台北、台中和高雄。喜歡寫作、讀詩、看畫、聆賞音樂。熱愛真理,熱愛教學,熱愛《奇蹟課程》,致力透過課堂的分享和寫作發散療癒的訊息,著有《奇蹟之旅──通往平安的26堂課》。
學習資源與課程資訊請見作者的個人網站:http://miracledoer.weebly.com
臉書社團:原汁奇蹟小舖‧奇蹟課程
粉絲專頁:許自呈 https://www.facebook.com/miracledoer/
TOP
章節試閱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
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吳承恩,《西遊記》
課程進度:何謂「犧牲」?
*研讀範圍: M-4.I & M-13
約莫十天前的一個晚上,正當好夢方酣,忽然間卻醒覺過來,耳朵裡傳來一個聲音:「去找《西遊記》吧!那是年後上課的絕佳教材!」三天之後,我就到書店裡買了一本原版的《西遊記》,利用年假期間讀了大半。果然那一念所言不虛,裡頭盡是趣味橫生的活教材,有寓言、有詩詞、有笑料,恰好也對得上年後新開的主題─...
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吳承恩,《西遊記》
課程進度:何謂「犧牲」?
*研讀範圍: M-4.I & M-13
約莫十天前的一個晚上,正當好夢方酣,忽然間卻醒覺過來,耳朵裡傳來一個聲音:「去找《西遊記》吧!那是年後上課的絕佳教材!」三天之後,我就到書店裡買了一本原版的《西遊記》,利用年假期間讀了大半。果然那一念所言不虛,裡頭盡是趣味橫生的活教材,有寓言、有詩詞、有笑料,恰好也對得上年後新開的主題─...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尤里西斯的壯遊
你安居上主懷中,只是夢見自己遭到放逐,卻隨時能夠覺醒於實相。
──《奇蹟課程》
大家手上拿到的這本書,是我從二〇一四年二月到二〇一四年七月給同修上課的筆記。我將上課重點鋪展成一篇篇散文,你讀到的每一個字都出自我的雙手。我找出了《奇蹟課程》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運用「主題歸納」的方式,配合相關章節,達到聚焦學習的效果。這在台灣還是個獨創之舉。
傳統的讀書會或上課方式向來是依循章節而行,優點是全面(但也可能囫圇吞棗),缺點則是散漫。由於同一個主題往往散落在不同章節,討論起來總覺難以聚焦。除...
你安居上主懷中,只是夢見自己遭到放逐,卻隨時能夠覺醒於實相。
──《奇蹟課程》
大家手上拿到的這本書,是我從二〇一四年二月到二〇一四年七月給同修上課的筆記。我將上課重點鋪展成一篇篇散文,你讀到的每一個字都出自我的雙手。我找出了《奇蹟課程》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運用「主題歸納」的方式,配合相關章節,達到聚焦學習的效果。這在台灣還是個獨創之舉。
傳統的讀書會或上課方式向來是依循章節而行,優點是全面(但也可能囫圇吞棗),缺點則是散漫。由於同一個主題往往散落在不同章節,討論起來總覺難以聚焦。除...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部 犧牲與特殊之愛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第三堂課
第四堂課
第五堂課
第六堂課
第七堂課
第八堂課
第九堂課
第二部 疾病與療癒
第十堂課
第十一堂課
第十二堂課
第十三堂課
第三部 死亡與生命
第十四堂課
第十五堂課
第十六堂課
第十七堂課
第四部 時間與永恆
第十八堂課
第十九堂課
第二十堂課
第二十一堂課
附錄
我讀《靈性衝撞》
再談抗拒
如何研讀《奇蹟課程》的原文
奇蹟手札
後記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第三堂課
第四堂課
第五堂課
第六堂課
第七堂課
第八堂課
第九堂課
第二部 疾病與療癒
第十堂課
第十一堂課
第十二堂課
第十三堂課
第三部 死亡與生命
第十四堂課
第十五堂課
第十六堂課
第十七堂課
第四部 時間與永恆
第十八堂課
第十九堂課
第二十堂課
第二十一堂課
附錄
我讀《靈性衝撞》
再談抗拒
如何研讀《奇蹟課程》的原文
奇蹟手札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許自呈
- 出版社: 一中心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7-26 ISBN/ISSN:978986929910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