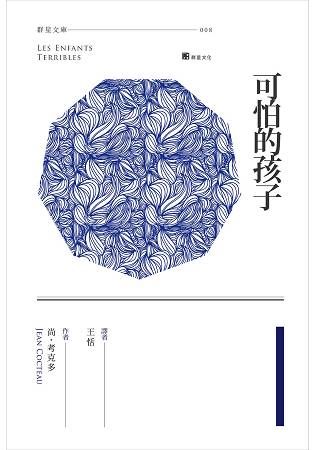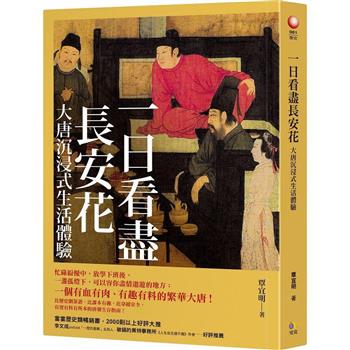法國文壇鬼才尚.考克多代表作,首度在台問世
電影版更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之先驅傑作
作家盧郁佳專文導讀
電影版更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之先驅傑作
作家盧郁佳專文導讀
孩子們是怎樣長大的?
如果父母師長是失能的大人,任其無所依傍地自由生長,
他們將往哪裡伸出枝幹?是否會斲傷或毀滅了誰?
伊莉莎白和保羅這對姊弟在父母相繼發狂、病逝後,得到一位醫生的親切資助,讓他倆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
他們不去上學、也沒人管教約束,只是待在被他們布置怪異的房間裡,帶上他們的朋友傑拉爾,無休無止地玩著各式各樣的「遊戲」。
這「遊戲」,是劇場式的角色扮演,是姊弟從屬關係的一再確認,是逃脫現實、拒絕分離,又渴望愛與獨立的刺探和掙扎。
孩子們活在不尋常的狀態裡,長期以來的自我封閉蒙蔽了他倆的眼睛,終致引發一場無法逆轉的悲劇……
尚.考克多以詩般的文字,放大檢視人性的極限,寫下一則唯美卻荒誕狂野的青春奇譚。
尚.考克多談《可怕的孩子》──
這本書已超越界限,變成了神話,循著因保羅和伊莉莎白奢侈而激蕩的青春精神,以及那場雪映射在情節中的某種致命光亮。無可否認,這部作品施展著一股魔力,激起了年輕人既渴求又排斥的不安。我眼看著它反過來對付我,那些粗暴的靈魂緊隨我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