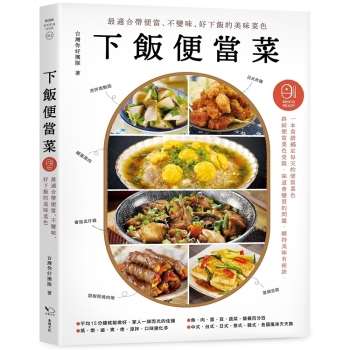每一次閱讀,都是人和文本之間的自由連結,
如星火,觸發著不斷變幻的聯想,無從預期的影響。
如星火,觸發著不斷變幻的聯想,無從預期的影響。
閱讀在不同時間、不同心境下,往往與被閱體之間產生不可思議的化學反應。詩意少年說,這是閱讀最神祕、無可控制,而最迷人或最折磨人的特色。
今天讀一點張愛玲,明早吟一首商禽詩,從一句話聯想一個電影畫面,甚至從一張照片或畫作中領悟人生。這些沒有固定路徑、固定方法的閱讀,就如同星星之火,在空氣中飛散著,靈光一現,便燎燒出了知識與思考的火光。
這些你可能不認識但值得認識,沒讀過但應該要讀的人與書,藉由楊照的私房讀書筆記,如星火燎原,再次感染,並豐富你我的心靈。
二十一世紀引發我們「閱讀」衝動,
最有「閱讀」本事的閱讀體
在札記中,我們看見楊照如烈焰般對閱讀的熱愛,如地熱般蓄積對閱讀的能量、如星火般傳遞對閱讀的火苗。
毫無疑問的,楊照是引發我們「閱讀」衝動,最有「閱讀」本事的閱讀體。
「時間,是生命最大的詛咒,帶走所有我們捨不得放走的念頭與經驗,因而我們必須抵抗時間,發明各種方式,留住那必然被時間磨損、破壞的思考與感受。散文是我的抵抗形式,也是抵抗的紀錄,懷想著自己曾經有過、或許有過的生命,於是書寫,面對自我,也面對時間,更面對時間與自我的衝突齟齬。
@關於楊照閱讀札記
本套書是楊照從多重閱讀經驗中,截取靈光,隨手寫下對「為什麼要閱讀?」、「當在閱讀時,我在想什麼?」「哪些書哪些人勾起青春回憶」的閱讀隨筆,預計分三輯出版,內容如下:
《烈焰:閱讀札記I》
羅曼.羅蘭、赫曼.赫塞、霍布斯邦、漫談閱讀及生命中的音樂
《地熱:閱讀札記II》
愛德溫.艾勃特、川端康成、鈞特.葛拉斯、張文環、胡適、柏楊、李文堯、索忍尼辛、普拉斯、彼得.杜拉克、《藏書之愛》、談棒球書寫、原著與電影
《星火:閱讀札記III》
馬奎斯、毛澤東、馬克思、黑格爾、夏濟安、臺靜農、張曉風、夏元瑜、失天心、商禽、三島由紀夫、張愛玲、盧騷、唐諾,談史學方法論,關於閱讀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