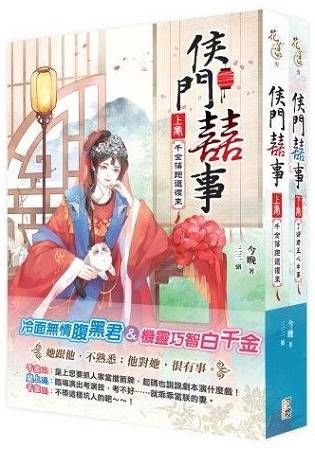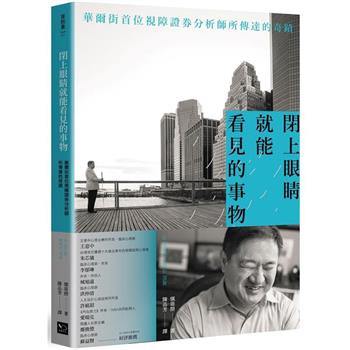白良辰在月黑風高的夜裡帶上她的小包袱,跑了。
一個月後,她坐在知縣大人的案桌上,涼涼的聽著聞訊趕來的白老爹破口大罵。
抗旨、拒婚、離家出走,細數每一條都是滔天大罪,然而要她忘了三年前與她定情的那個人,與剛登基的皇上成親。她,辦不到!
雖說如此,她還是被架進宮了。(掏出手帕兒為自己默哀)
君王權力比天大,要她住進皇宮她就得住;要她和後宮纏鬥她就鬥,但要她愛上他──抱歉,門兒都沒有!
可為什麼她對他明明一點兒印象也無,他卻老是一副「我倆很熟」的模樣?
白良辰摸摸頭:帝王心,好難猜啊。
「白良辰,除了閻王殿,朕看妳還往哪裡逃!」
【上卷】千金落跑還復來
【下卷】了卻君王心中事
【人物簡介】
白良辰:
白將軍府嫡長女,容貌秀麗,個性堅毅聰穎。生母失蹤於三年前的一場蹊蹺大火,她誓言找出母親失蹤的真相。然而卻因新帝陌易唐的後宮選秀被迫進入宮中,她索性將計就計,一邊與陌易唐周旋,一邊運用宮中的權勢探查那場大火背後的秘密。
陌易唐:
西夜國新皇,俊美無雙,為人冷酷無情,對白良辰有著難以言喻的執著。因太后一族支持登基,不得不向其低頭,卻也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勢力,伺機而動,欲拔除來自太后與陸氏的威脅。
陸璿璣:
璿璣郡主,太后嫡親母族陸氏之女,是陌易唐的青梅竹馬,亦是他表面上的心愛之人。被父親陸仲民利用以保全權位,又被陌易唐當作攏絡陸氏的工具,看似為後宮之首,卻如棋子般卑微可憐。
本書特色
【上卷】千金落跑還復來/【下卷】了卻君王心中事 同步發行!
冷面無情腹黑君 & 機靈巧智白千金
她跟他,不熟悉;他對她,很有事。
千金怒:皇上您要抓人家當擋箭牌,起碼也說說劇本演什麼戲!
皇上道:臨場演出考演技,考不好……就乖乖當朕的妻。
千金囧:不帶這樣坑人的吧~~!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侯門囍事:套書上下卷(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350 |
羅曼史 |
$ 350 |
華文羅曼史 |
$ 350 |
古代小說 |
$ 450 |
古代小說 |
$ 450 |
言情小說 |
$ 594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侯門囍事:套書上下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