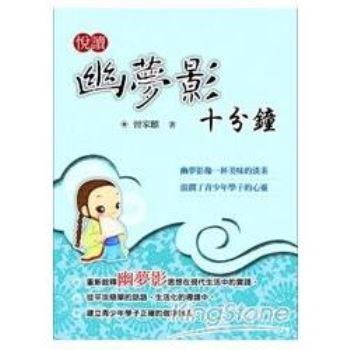我也許會想像,啊,那雲端之處便是未來終老所在的天堂光景吧,有著燦爛和煦的陽光,笑容親切的看顧者、一張張無慮的面孔………而完全沒有一處想對!
那又如何呢?
一旦開始回溯天堂,不管是誰都會徒勞地想錯,任何人都註定要遠離它。就是因為成功躲開所有人記憶的重擔,天堂才能像這樣姿態輕盈地安然立於這能俯瞰一切的最高處!
這裡沒有任何可疑之處,有的只是可惜!
排在隊伍中,我完全理解了……天堂呈現的不是終處,而是一道道離開的路徑。
即便如此,也沒有誰覺得自己被騙。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變成鬼了之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小說 |
$ 198 |
現代小說 |
$ 198 |
文學作品 |
$ 198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98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變成鬼了之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巴黎晚餐
1974年12月28日出生於鹿港。先後畢業於師大附中、清華大學,主修經濟學。學生時代起即對小說的世界非常著迷。迄今不墜、且不挑特定作品閱讀的這份熱情所帶來的後勁,便是不知不覺也著手寫起小說來,並且作品風格不受限於固定的框架。
著有長篇小說「惑心石」(2014年出版)。
巴黎晚餐
1974年12月28日出生於鹿港。先後畢業於師大附中、清華大學,主修經濟學。學生時代起即對小說的世界非常著迷。迄今不墜、且不挑特定作品閱讀的這份熱情所帶來的後勁,便是不知不覺也著手寫起小說來,並且作品風格不受限於固定的框架。
著有長篇小說「惑心石」(2014年出版)。
目錄
死了之後,人的命運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瑞華 2
鬼域,往生 施佩瑩 4
靈魂的本質是慾念 巴黎晚餐 6
變成鬼了之後 10
老公公 36
招魂別在月光下 45
Thought Maker 82
千千萬萬個我 105
痛 137
男神不是對手 147
莫尼瓦城 177
姐姐 183
冷 213
千千萬萬個你 223
鬼域,往生 施佩瑩 4
靈魂的本質是慾念 巴黎晚餐 6
變成鬼了之後 10
老公公 36
招魂別在月光下 45
Thought Maker 82
千千萬萬個我 105
痛 137
男神不是對手 147
莫尼瓦城 177
姐姐 183
冷 213
千千萬萬個你 223
序
死了之後,人的命運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瑞華
我有個秘密,我喜歡看小說。也許你們覺得奇怪,這算什麼秘密。不過,以我在大學經濟學系任教的身份,這是一個未必該讓人知道的事。我願意說出這個秘密,是因為我的學生中有不少人不只喜歡看小說,還會寫小說。本書的作者就是這樣的人。
我看小說的時候,經常可以放任想像,進入一個經濟理性之外的世界。巴黎晚餐的這本小說,帶我到了一個鬼的世界。不過,別以為鬼故事就很恐怖,這些變成鬼之後的人,有很多的懷念、留戀與遺憾,卻並不怨恨、報復。這些故事更透露了中國文化對死亡的一種溫柔態度,那就是轉世投胎的希望。
這幾年我也迷上了一些美國的影視節目。即使已經有許多的僵屍片,「陰屍路」(TheWalkingDead)還是有特殊的吸引力。劇中的僵屍可怕,活人更可怕。活人的可怕不僅是因為每個活人身體裡都有個僵屍,更重要的是因為那個世界裡許多活人沒有了希望。死了之後,不會變成鬼,卻讓活人比鬼更恐怖。
最近美國又有一部關於死亡的電視劇讓我大開眼界。嚴格來講,「守望塵世」(Leftovers)裡大量消失的人並非因為死亡,卻被認為上了天堂。當宗教預示的選秀結束時,那些被留下來的生存者成為不幸的「剩人」。失去親人的痛苦,再加上被上帝遺棄的絕望,這齣劇裡人物的生命一個比一個難過。又是生不如死,人比鬼慘。
死亡的可怕是因為生命結束後什麼都不能做,想做什麼都來不及了。我講的不是死去的人,而是活著的人,無法再對死去的人做什麼。這是我在「陰屍路」、「守望塵世」裡看到的悲劇。那死去的人呢?死了之後,還可以做什麼嗎?這本書的書名留給讀者許多餘韻。
回到我的本行。我在大學教經濟學,談的是如何選擇。人的一生中經歷許許多多的選擇與不選擇,承受著那些決定的後果,而且充滿了事後的回憶與悔恨。經濟學雖然是為了現實的選擇所發展出來的學問,但是當我們把想像力放到現實以外,那些生命中的選擇依然循著人性繼續延伸。我很自豪的說,作者是我們經濟學系教過的學生。
只要不死,就還有改變的機會,也就還有希望。人死了之後呢?我們看到許多沒有希望後的悲劇,從這些悲劇中獲得的最深感受是對於生命的珍惜。對照那些對死亡絕望的悲劇,變成鬼反而是一種希望。
中國文化的轉世投胎信仰,給了死後更多的希望。死後的希望讓人能夠比較勇敢面對死亡,可是如果希望來的太過容易,卻會讓活著沒有價值,失去面對生命的勇氣。命運已不可知,死後當然也不可知。變成鬼了之後…,這裡的故事,還是有許多選擇與不選擇的懷念、感激、遺憾、無奈。
鬼域,往生
施佩瑩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知道人死後去了哪裡,如果變成了鬼,之後呢?乍看單純的問題,巴黎晚餐在書中娓娓建構了一個個令人感覺再真實不過的情景,讀了之後不但已經要相信了這就是天堂的樣貌,而且還迫不及待往下翻,想知道後面的情節發展。就像在看日劇「世界奇妙物語」一樣,而且每個獨立小故事還能環環相扣,邊看邊享受找梗的樂趣。
與巴黎晚餐相識是再自然不過的同學關係,從小就喜歡看書寫作的她,對文字的使用亦很敏銳,到現在還記得我們國中時玩過的文字接龍遊戲,我接詞的内容總是被她說這不好笑啊、換一個,而她自己的接龍內容卻天馬行空、笑果十足,在那個學校老師只教怎麼考試的年代,她仍然能在平淡日常中發現許多大大小小的亮點,就像她的小說。
她上一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們除了佩服更為驚豔,因為她文藝美少女的形象太深植我們同學心裡,即使當了媽媽也是一樣優雅緩和,生活時尚、旅行美食的主題好像跟她比較相近,結果厚厚一本紮實的奇幻小說卻在忙錄育兒的空檔突然間產出;當我以為這本新書可能是奇幻小說第二部的時候,她又再度顛覆我們的想像,出了這本集結她過去、現在的短篇創作小說,雖然是陸續寫成,但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的故事中,隱隱展現了對生命中來不及或錯過的、不論好壞的人事物的追悔。
捨棄華麗的詞藻卻仍能將故事說的有趣、人物描寫細膩、細節處理恰到好處,她獨特的洞察力,讓這本書具有高度影像化的效果,各個場景與書中人的表情動作,似乎都能輕易浮現眼前、描繪出畫面,增添不少閱讀趣味。
閱讀巴黎晚餐的書,從中發現自己曾有過的念頭、曾想做的舉動,與其說她透過創作表達或趨近自己,不如說她的創作讓身為讀者的我們,伸手觸向摸不到的內在世界。
靈魂的本質是慾念
巴黎晚餐
這本小說雖是以鬼為出發點的故事,但並非在一開始我就抱持著「這一次,我想特別花一點時間來談談鬼的事!」不是這樣。
而是如同過去寫作時,選擇的角色自然各別帶著不同的身分、性格、經歷…等,這些型塑一個角色時必要的種種元素,而此次被寫進故事裡的某些人物,他或者她,在那些元素中,有一樣特徵恰巧是「鬼」。應該這麼說。
一直以來我的寫作習慣總是多軌進行,從第一段第一行開始順順地、好好地寫,對我來說完全無法想像,而是經常同一時間在琢磨不同章節的橋段。這本由十一個短篇集結而成的小說也是如此。除了其中幾篇在許久以前就完稿之外,其餘的,整體說來皆是在這種多頭作業的書寫習慣下完成。
小說中特別費心的部分,應該是角色語氣的修改。這項工作比起寫就初稿本身,耗費我更多的時間。即便是那些看似隨興帶過的詼諧對白,都是故事在完成七、八成左右時,再慢慢花時間一點一點加以安插、修改。相較於決定要寫關於鬼的故事,這一點,反而才是我一開始就確定的。
「希望讀者能在豪不感覺沉重的情況下接收到我想藉由故事傳達的某些想法。」
決定要這麼寫之後,特別斟酌不同故事間的敘述口吻。沒有道理登場的「我」才八、九歲,說起話來卻用詞扭捏,或是登場的「我」明明是率性的男生,對話卻拖泥帶水…等等這些考量,更促成上述寫作方向。總之每篇一處一處慢慢被調整成合理的口吻。
會被誤解嗎?——那簡直像是玩笑般、作為開場白的第一篇故事,由這樣的故事開始娓娓道來的話——還是恰巧相反會因此吸引到曉得其中費工夫部分所在的讀者,而結果被正面地理解了呢?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
然而「就是打算這樣寫」的方向是如此明確,像抱定要由地質剖面結構來敘述一座小丘那樣——這一層是略帶水氣的黏土層、那一層有著豐富的沉積物、接著是極為單調卻不透水的紅土層、或除了化石什麼都沒有的一層…層層分明,各有所因——配合角色轉換說話語氣到了寫這本小說的後期,便成了再自然不過的事。我想要這樣說故事。
小說全部完成後,我以作為讀者的立場自己讀過一遍,感覺經由對白修改,小說彷彿被整個重新寫過一遍!自己也感覺驚訝。而對於作品中四處都有的鬆散雲團般的輕鬆感,我自己很喜歡——雖然偶有不太相信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的奇異感觸。
大概猶如同一輪月亮,不過形狀稍稍改變就令觀者的感受截然不同。
也如同鬼,不過是一眼,就被誤以為是可怕、可恨。或如同千千萬萬個你我,不過是一句話,就被誤以為可惜或者可惡。
而其實完全來自我們的想像。
這個世界上既有各式各樣的人,那麼有各式各樣的鬼自也是合情合理。
明明什麼鬼也沒有見到,卻才燒完一炷香,就感覺被激勵了!確實有這樣的人吧,很可能還為數頗多!供桌上的香才燒了一半,那鬼卻已豪不戀棧生前至親,早已轉身,堅信來世會勝過此生,勢必也有這樣的亡者吧!
於是一切無法掌握的事況、人物,總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最終都令世人不安,同時強烈地好奇。
「希望」也是這樣。
假使連想像中理應可怕的鬼都給予我們祝福的時候,那個「希望」要落實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夠稱得上是一帆風順呢?我向湖面打了一個這樣的水瓢,並將這份不確定和慨歎悄悄夾進不同的篇幅中。
「希望」有時很討厭,存在著「即使盡了全力也無法獲得百分之百的回報」這樣的特質。正如同鬼,無論多想見或多不想見,不是拼命去做什麼就會有果斷的答覆。
於是鬼才令我們踹踹不安,那份不安並非來自鬼的可怕,而是我們心中那股作不了主的無從著力。
這本小說,寫的是這兩件事。說穿了,其實是同一件事。
至於…鬼是模糊而突兀的存在?是令人備感懷念的憧憬?是神思安心的寄托?…說到底,鬼是否真存在我們的四周呢?
只能說,不同的讀者想必各自心裡有數。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劉瑞華
我有個秘密,我喜歡看小說。也許你們覺得奇怪,這算什麼秘密。不過,以我在大學經濟學系任教的身份,這是一個未必該讓人知道的事。我願意說出這個秘密,是因為我的學生中有不少人不只喜歡看小說,還會寫小說。本書的作者就是這樣的人。
我看小說的時候,經常可以放任想像,進入一個經濟理性之外的世界。巴黎晚餐的這本小說,帶我到了一個鬼的世界。不過,別以為鬼故事就很恐怖,這些變成鬼之後的人,有很多的懷念、留戀與遺憾,卻並不怨恨、報復。這些故事更透露了中國文化對死亡的一種溫柔態度,那就是轉世投胎的希望。
這幾年我也迷上了一些美國的影視節目。即使已經有許多的僵屍片,「陰屍路」(TheWalkingDead)還是有特殊的吸引力。劇中的僵屍可怕,活人更可怕。活人的可怕不僅是因為每個活人身體裡都有個僵屍,更重要的是因為那個世界裡許多活人沒有了希望。死了之後,不會變成鬼,卻讓活人比鬼更恐怖。
最近美國又有一部關於死亡的電視劇讓我大開眼界。嚴格來講,「守望塵世」(Leftovers)裡大量消失的人並非因為死亡,卻被認為上了天堂。當宗教預示的選秀結束時,那些被留下來的生存者成為不幸的「剩人」。失去親人的痛苦,再加上被上帝遺棄的絕望,這齣劇裡人物的生命一個比一個難過。又是生不如死,人比鬼慘。
死亡的可怕是因為生命結束後什麼都不能做,想做什麼都來不及了。我講的不是死去的人,而是活著的人,無法再對死去的人做什麼。這是我在「陰屍路」、「守望塵世」裡看到的悲劇。那死去的人呢?死了之後,還可以做什麼嗎?這本書的書名留給讀者許多餘韻。
回到我的本行。我在大學教經濟學,談的是如何選擇。人的一生中經歷許許多多的選擇與不選擇,承受著那些決定的後果,而且充滿了事後的回憶與悔恨。經濟學雖然是為了現實的選擇所發展出來的學問,但是當我們把想像力放到現實以外,那些生命中的選擇依然循著人性繼續延伸。我很自豪的說,作者是我們經濟學系教過的學生。
只要不死,就還有改變的機會,也就還有希望。人死了之後呢?我們看到許多沒有希望後的悲劇,從這些悲劇中獲得的最深感受是對於生命的珍惜。對照那些對死亡絕望的悲劇,變成鬼反而是一種希望。
中國文化的轉世投胎信仰,給了死後更多的希望。死後的希望讓人能夠比較勇敢面對死亡,可是如果希望來的太過容易,卻會讓活著沒有價值,失去面對生命的勇氣。命運已不可知,死後當然也不可知。變成鬼了之後…,這裡的故事,還是有許多選擇與不選擇的懷念、感激、遺憾、無奈。
鬼域,往生
施佩瑩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知道人死後去了哪裡,如果變成了鬼,之後呢?乍看單純的問題,巴黎晚餐在書中娓娓建構了一個個令人感覺再真實不過的情景,讀了之後不但已經要相信了這就是天堂的樣貌,而且還迫不及待往下翻,想知道後面的情節發展。就像在看日劇「世界奇妙物語」一樣,而且每個獨立小故事還能環環相扣,邊看邊享受找梗的樂趣。
與巴黎晚餐相識是再自然不過的同學關係,從小就喜歡看書寫作的她,對文字的使用亦很敏銳,到現在還記得我們國中時玩過的文字接龍遊戲,我接詞的内容總是被她說這不好笑啊、換一個,而她自己的接龍內容卻天馬行空、笑果十足,在那個學校老師只教怎麼考試的年代,她仍然能在平淡日常中發現許多大大小小的亮點,就像她的小說。
她上一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們除了佩服更為驚豔,因為她文藝美少女的形象太深植我們同學心裡,即使當了媽媽也是一樣優雅緩和,生活時尚、旅行美食的主題好像跟她比較相近,結果厚厚一本紮實的奇幻小說卻在忙錄育兒的空檔突然間產出;當我以為這本新書可能是奇幻小說第二部的時候,她又再度顛覆我們的想像,出了這本集結她過去、現在的短篇創作小說,雖然是陸續寫成,但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的故事中,隱隱展現了對生命中來不及或錯過的、不論好壞的人事物的追悔。
捨棄華麗的詞藻卻仍能將故事說的有趣、人物描寫細膩、細節處理恰到好處,她獨特的洞察力,讓這本書具有高度影像化的效果,各個場景與書中人的表情動作,似乎都能輕易浮現眼前、描繪出畫面,增添不少閱讀趣味。
閱讀巴黎晚餐的書,從中發現自己曾有過的念頭、曾想做的舉動,與其說她透過創作表達或趨近自己,不如說她的創作讓身為讀者的我們,伸手觸向摸不到的內在世界。
靈魂的本質是慾念
巴黎晚餐
這本小說雖是以鬼為出發點的故事,但並非在一開始我就抱持著「這一次,我想特別花一點時間來談談鬼的事!」不是這樣。
而是如同過去寫作時,選擇的角色自然各別帶著不同的身分、性格、經歷…等,這些型塑一個角色時必要的種種元素,而此次被寫進故事裡的某些人物,他或者她,在那些元素中,有一樣特徵恰巧是「鬼」。應該這麼說。
一直以來我的寫作習慣總是多軌進行,從第一段第一行開始順順地、好好地寫,對我來說完全無法想像,而是經常同一時間在琢磨不同章節的橋段。這本由十一個短篇集結而成的小說也是如此。除了其中幾篇在許久以前就完稿之外,其餘的,整體說來皆是在這種多頭作業的書寫習慣下完成。
小說中特別費心的部分,應該是角色語氣的修改。這項工作比起寫就初稿本身,耗費我更多的時間。即便是那些看似隨興帶過的詼諧對白,都是故事在完成七、八成左右時,再慢慢花時間一點一點加以安插、修改。相較於決定要寫關於鬼的故事,這一點,反而才是我一開始就確定的。
「希望讀者能在豪不感覺沉重的情況下接收到我想藉由故事傳達的某些想法。」
決定要這麼寫之後,特別斟酌不同故事間的敘述口吻。沒有道理登場的「我」才八、九歲,說起話來卻用詞扭捏,或是登場的「我」明明是率性的男生,對話卻拖泥帶水…等等這些考量,更促成上述寫作方向。總之每篇一處一處慢慢被調整成合理的口吻。
會被誤解嗎?——那簡直像是玩笑般、作為開場白的第一篇故事,由這樣的故事開始娓娓道來的話——還是恰巧相反會因此吸引到曉得其中費工夫部分所在的讀者,而結果被正面地理解了呢?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
然而「就是打算這樣寫」的方向是如此明確,像抱定要由地質剖面結構來敘述一座小丘那樣——這一層是略帶水氣的黏土層、那一層有著豐富的沉積物、接著是極為單調卻不透水的紅土層、或除了化石什麼都沒有的一層…層層分明,各有所因——配合角色轉換說話語氣到了寫這本小說的後期,便成了再自然不過的事。我想要這樣說故事。
小說全部完成後,我以作為讀者的立場自己讀過一遍,感覺經由對白修改,小說彷彿被整個重新寫過一遍!自己也感覺驚訝。而對於作品中四處都有的鬆散雲團般的輕鬆感,我自己很喜歡——雖然偶有不太相信是自己寫出來的東西的奇異感觸。
大概猶如同一輪月亮,不過形狀稍稍改變就令觀者的感受截然不同。
也如同鬼,不過是一眼,就被誤以為是可怕、可恨。或如同千千萬萬個你我,不過是一句話,就被誤以為可惜或者可惡。
而其實完全來自我們的想像。
這個世界上既有各式各樣的人,那麼有各式各樣的鬼自也是合情合理。
明明什麼鬼也沒有見到,卻才燒完一炷香,就感覺被激勵了!確實有這樣的人吧,很可能還為數頗多!供桌上的香才燒了一半,那鬼卻已豪不戀棧生前至親,早已轉身,堅信來世會勝過此生,勢必也有這樣的亡者吧!
於是一切無法掌握的事況、人物,總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地最終都令世人不安,同時強烈地好奇。
「希望」也是這樣。
假使連想像中理應可怕的鬼都給予我們祝福的時候,那個「希望」要落實到什麼樣的程度才夠稱得上是一帆風順呢?我向湖面打了一個這樣的水瓢,並將這份不確定和慨歎悄悄夾進不同的篇幅中。
「希望」有時很討厭,存在著「即使盡了全力也無法獲得百分之百的回報」這樣的特質。正如同鬼,無論多想見或多不想見,不是拼命去做什麼就會有果斷的答覆。
於是鬼才令我們踹踹不安,那份不安並非來自鬼的可怕,而是我們心中那股作不了主的無從著力。
這本小說,寫的是這兩件事。說穿了,其實是同一件事。
至於…鬼是模糊而突兀的存在?是令人備感懷念的憧憬?是神思安心的寄托?…說到底,鬼是否真存在我們的四周呢?
只能說,不同的讀者想必各自心裡有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