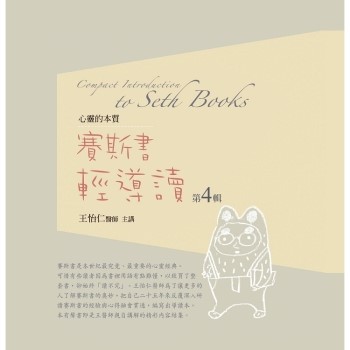對於法國,世人有太多偏見和想像——
法國女人無比時尚,而且不會胖,每個男人都有情婦,風流倜儻;
法國人不愛洗澡、頭上總頂著貝雷帽;他們餐餐蝸牛鵝肝,無酒不歡;
法國人工作懶散,而且罷工是絕對必然……
可是,在這些想像和偏見背後,法國,她究竟是什麼真實模樣?
世人對法國的印象往往建立在一連串的偏見和迷思上。這些謬解的矛盾讓法國人在外人心中總顯得神祕莫測,擁有世人無法理解的不可思議特質。不過,當扭曲成刻板印象的迷思變成一個國家的形象,那可就值得好好檢視了。法國女人無比時尚,而且不會胖,每個男人都有情婦,風流倜儻;
法國人不愛洗澡、頭上總頂著貝雷帽;他們餐餐蝸牛鵝肝,無酒不歡;
法國人工作懶散,而且罷工是絕對必然……
可是,在這些想像和偏見背後,法國,她究竟是什麼真實模樣?
《偏見法國》從法國的飲食、性愛、禮儀、政治、歷史、生活態度,以及法、英這兩個「最親密的敵人」的糾葛情仇觀點,破解世人無不熟悉的四十一個「偏見」,細膩呈現一個讓全世界愛恨交織的文化的真實面貌。
伊特薇筆下的觀察結合了淵博史實、大眾文化、精妙語言和個人第一手記錄,從幽默趣味和廣博知識切入,不見浮濫淺薄的老梗觀點,而有英式幽默特有的棉裡藏針口吻,深入剖析世人對於法國的各樣偏見和幻想的對與錯,內容敘述辛辣,妙趣橫生,而且解析細膩獨到,讓讀者能以各種「偏見」,去理解這個總教人又愛又憎的高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