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橡皮筋
就像天使遺失的光圈
小小的橡皮筋從天而降
套住了我們
像悟空戴了十五年的金箍
小小的橡皮筋舒適合身
帶著我們去取經
像圓環狀的鑰匙圈
小小的橡皮筋緊連著我們
從此有兩扇門
是可以開的
卻也像馬戲團的火圈
我們是被馴養的動物
一夕完成了訓練
也像不願再戴上的金箍
三藏也只是
念了一次咒
當我們都變成了只擁有負極的磁鐵
小小的橡皮筋
也只是像一個小小的橡皮筋
終於我讓你離開
讓橡皮筋彈回來
打我
住下的人
她只是住下了。
那時她說:「我要離開了。」,卻見她哪兒都沒去,也沒付租金,就賴在我這住下了。最初覺得她很快就會真正離去,沒想著要管她,好幾天過去看她還在原地,我才注意到事情不太對勁。
她是不愁吃喝的。跟她從前一起去的那家咖啡店後來竟有了外送服務,每天定時送上她那時點的蛋糕與咖啡,連桌椅都會送來,難以想像的良好服務。她也是不愁穿的。有時我見到路上行人穿的女裝,或是百貨公司女裝部的衣服,她竟是一雙巧手,瞬間照著縫了一件,瞬間穿上,穿上個一兩天也沒看她嫌膩。
有時她會裸身,跟一個我沒看過臉孔的裸體男人擁吻;或許有人會問,她就住在我這,為什麼會沒看過那男人的臉孔,其實這些資訊都是太陽與月亮偷偷跟我說的——他們擁吻的時候,我都在外頭,沒一次例外。
在那之後她竟也不會老了。本來想是她保養有方,但在一起的時候她就有些小小的老化,像是新長的兩三根白頭髮、肌肉鬆弛或是下腹起的一些皺紋,顯然是住所的影響。有時想這裡就像龍宮使人常保青春,定會有許多女性客戶,但她們鐵定會抗議她的存在:「憑什麼她住就不用租金?」。我想說因為是她所以我沒法跟她收租金,但這理由絕對會讓她們更憤怒,我就沒再動了這個念頭。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她的臉了。兩三個月之後,她的臉皮完全消失了。這本來是件對我沒有影響的事,但她偶爾就是死盯著我瞧,也不說話,持續好幾個小時,我只好翻了翻舊照片,暫時把上面的臉孔撕下來,丟給她當面具。
後來我真受不了,叫她出來到外面有陽光的地方親自跟她溝通,她卻開始像機關槍似地不停地說:「我要離開了。」,怪異的是,我見著她嘴在動,卻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她也像那時一樣,一點都沒有要搬走的樣子,我只好放棄了這個念頭。
就這樣整整一年,我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
如果 你是一種氣候
如果,你是一種氣候
你只是習於豪賭一場
在昨日擁有三十度C
在今日就給他輸個精光
你只是有一種冬天被窩的感覺
在晨間我不願離你而去
在夜裡我卻拚命忍寒
你讓我記得不要任意露出肌膚
讓我記得帶上備用的大衣
而你只是不願違背自然法則
在暖春愛上陽光
在嚴冬迎娶了雪
如果你只是一種氣候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木與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68 |
詩 |
$ 210 |
中文書 |
$ 221 |
詩 |
$ 246 |
現代詩 |
$ 252 |
華文現代詩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木與瑕
我不想寫詩,我想跟她說話。
《木與瑕》分為四輯,輯一「木與瑕」收錄短詩,大多僅使用單一主要意象,強化力量;輯二「斷尾」收錄組詩與中長詩,亦多以單一主要意象貫穿全詩,可說是輯一的強化版;輯三「玻璃鞋」主要收錄散文詩,也可以說一些意念難以寫成分行詩的都在這裡;輯四「記一隻一出店門便從我眼前竄走的貓」則收錄使用較多意象與部分難以明確分類的詩作,畢竟分類有其極限,詩作則無。
我一直認為所有我寫出來的東西,只是剛好可以被定義為詩,所有我使用的意象,早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已久;我只是剛好在場的人,我只是順手牽羊的盜賊。但盜賊的種類也有所區分:普通的賊盜取金銀財寶,所謂雅賊偷取藝術名畫,而我這種賊—偷的只是身邊之物。
只是我身邊有些什麼:麻雀、沒味道的口香糖、滯銷的商品、電腦裡沒寄出的信;我身邊還有些什麼:古典、現代、數學、邏輯、我的人生。我的身邊只沒有她――所以全部都是她。
就是這樣的一本詩集――只沒有她,全部都是她。
作者簡介:
木瑕
本名卓建甫,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碩士。2011年失戀,2011年開始寫詩,絕大部分詩作刊登於衛生紙詩刊+。不想寫詩,只能寫詩。不認為自己是個詩人,只是個找詩的人。
TOP
章節試閱
小小的橡皮筋
就像天使遺失的光圈
小小的橡皮筋從天而降
套住了我們
像悟空戴了十五年的金箍
小小的橡皮筋舒適合身
帶著我們去取經
像圓環狀的鑰匙圈
小小的橡皮筋緊連著我們
從此有兩扇門
是可以開的
卻也像馬戲團的火圈
我們是被馴養的動物
一夕完成了訓練
也像不願再戴上的金箍
三藏也只是
念了一次咒
當我們都變成了只擁有負極的磁鐵
小小的橡皮筋
也只是像一個小小的橡皮筋
終於我讓你離開
讓橡皮筋彈回來
打我
住下的人
她只是住下了。
那時她說:「我要離開了。」,卻見她哪兒都沒去,也沒付租金,就賴在...
就像天使遺失的光圈
小小的橡皮筋從天而降
套住了我們
像悟空戴了十五年的金箍
小小的橡皮筋舒適合身
帶著我們去取經
像圓環狀的鑰匙圈
小小的橡皮筋緊連著我們
從此有兩扇門
是可以開的
卻也像馬戲團的火圈
我們是被馴養的動物
一夕完成了訓練
也像不願再戴上的金箍
三藏也只是
念了一次咒
當我們都變成了只擁有負極的磁鐵
小小的橡皮筋
也只是像一個小小的橡皮筋
終於我讓你離開
讓橡皮筋彈回來
打我
住下的人
她只是住下了。
那時她說:「我要離開了。」,卻見她哪兒都沒去,也沒付租金,就賴在...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推薦序
宋尚緯
建甫是我研究所的同學。其實我一開始對建甫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的人,進教室就看到他坐在一邊,也不說話,看著筆電的螢幕做自己的事情。最開始的半年和他幾乎沒有交集,後來是因為修了同一門課的緣故,才知道他會寫詩。但也只是知道而已。我必須承認一開始讓我對建甫產生興趣的完全不是詩,而是我們都有玩同一款遊戲,藉由遊戲,我跟他之間的交流才變得多了起來。在研究所的期間我上課的樂趣就是調戲他。然而我是知道的,即使他是個看起來寡言,對其他事物都不感興趣的人,然而他本質上其實是對任何事物都觀察細微,且有自己...
宋尚緯
建甫是我研究所的同學。其實我一開始對建甫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的人,進教室就看到他坐在一邊,也不說話,看著筆電的螢幕做自己的事情。最開始的半年和他幾乎沒有交集,後來是因為修了同一門課的緣故,才知道他會寫詩。但也只是知道而已。我必須承認一開始讓我對建甫產生興趣的完全不是詩,而是我們都有玩同一款遊戲,藉由遊戲,我跟他之間的交流才變得多了起來。在研究所的期間我上課的樂趣就是調戲他。然而我是知道的,即使他是個看起來寡言,對其他事物都不感興趣的人,然而他本質上其實是對任何事物都觀察細微,且有自己...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木瑕
- 出版社: 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05 ISBN/ISSN:978986933759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44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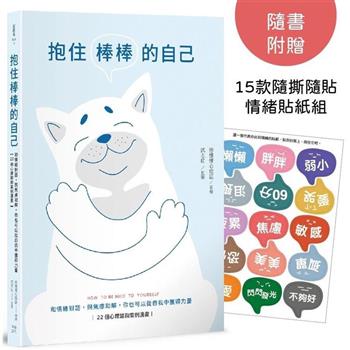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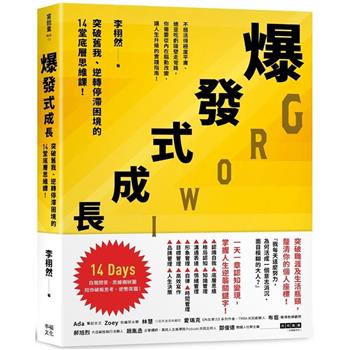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