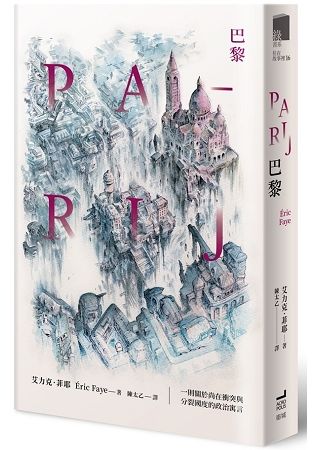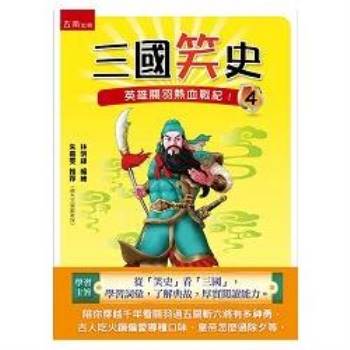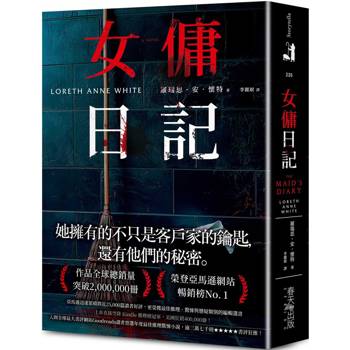作者序
艾力克.菲耶
「架空歷史」(uchronie)這個詞由哲學家查爾斯.雷諾維葉(Charles Renouvier)於十九世紀末提出之後,一種存在已久的文學種類從此有了名稱。這種文學的內容並不在於想像一個理想社會,藏在某個虛擬地方,或從未來出現;而在於設想,如果歷史在某個特定的時刻,走上另一條不同的道路,致使事件的發展出現「短路」,那麼,這個世界會以何種樣貌呈現。各國政權其實都是善於虛構的偉大「作者」,一直都喜歡竄改歷史,開先河者即為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下令焚毀所有史書,想必是因為那些書讚揚前朝的豐功偉業。歷史與時間應該要從他的時代起算,而且只能從他開始……很久之後,在拿破崙一世的要求之下,畫家大衛在加冕圖上添加了皇帝的母親,但其實她在加冕典禮上缺席。再看看大家較熟知的卡廷大屠殺(Massacre de Katyn)[注1],直到經濟改革重建期(perestroïka),克里姆林宮仍始終嫁禍給德國納粹。無論獨裁與否,當權者常試圖將歷史切分成片段,多多少少,暗中將各種事件移花接木,以顯示我們是多麼仰賴著他們才有美好的今天。只要想想時不時冒出頭來的那些否定主義者(négationnistes)和神創論者(créationnistes)[注2]就能明白:重建過去不僅僅是擺脫過去。
作家則明顯地做得更絕。他會將歷史斷章取義,強行插入自己製造出的括弧內容。「時間,是不動永恆之動態影像。」盧梭寫道。時間是作家的首要題材,與文字結合之後,偶爾產生出一種奇怪的合成物,稱之為文學。然而,文學為什麼要固定某段時間範圍,利用「架空歷史」的概念?為什麼要寫下《Parij》這部以一九四四年為歷史分歧點的小說,說一個紅軍成功推進到巴黎的故事?這部小說初版問世距今已十年,直到現在,我才真的想到這個問題。我努力避免去寫一篇寫實的文字,例如把背景放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間的柏林。柏林已經太為人所熟悉,從某方面來看,已被歷史淡化,對一本這樣的小說而言,並不很適當。我先前發表過一篇文章〈最惡實驗室〉(Les Laboratoires du pire),探討極權主義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希望用虛構小說的方式,再次探索這個領域。主角應該要是一位知名大作家,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他遺失了手稿。我的想法是去比較,身在分隔兩個文明的圍牆這邊和那邊時,文學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自然而然的,小說進駐人稱「光明之城」的都市,將城市一分為二;而那裡自古以來習慣自由,與所有極權主義唱反調。
弔詭的是,獨裁政權追蹤書寫,試圖駕馭,正因不敢掉以輕心,反而顯得十分尊敬重視。主政當局承認文字之豐功偉業及不可輕忽的威力。幾百公尺之外,圍牆的另一邊,在巴黎的「自由區」,文字書寫引發的反應只比冷漠好一點。文學頂多是眾多消遣之一。以自由之名,人們偶爾會把自由放在某種奇怪的用途上……書寫《Parij》之時,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逐漸遠離獨裁的東城,放棄斯巴達,選擇雅典。中心人物不再真的是大作家莫爾凡,而是負責監視他信件往來的探員諾維爾。很快的,後者將被夾在斯巴達和雅典之間,搖擺不定,難以抉擇。我借用了間諜小說常出現的俗套,刻意把玩,在敘述中處處布下傳聞軼事及「東歐國家」的稗官野史。在官方機構裡與頭號人物交手的莫爾凡,是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ïl Kadaré)。[注3]當時,在走史達林路線的阿爾巴尼亞,卡達萊正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室找資料,籌寫小說《極度孤寂之冬》(L’Hiver de la grande solitude),而且始料未及地認識了恩維爾.霍查(Enver Hodja)。[注4]莫爾凡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在東歐國家飽嘗噓聲倒采,則頗有一點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注5]的影子。這位作家曾長期遭受大規模毀謗。諸如此類。在今日,這一切宛如二十世紀版的《功勛之歌》(chanson de geste)[注6]情節。在蘇聯帝國瓦解後十五年,西方吞噬了東方;寫作普遍平庸,書本淪為一種產品,與各種產品無異,這是文學工業化後的必然現象。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九六年寫成的《Parij》,很顯然的,純屬現實。
艾力克.菲耶
二○一一年十二月
1一九四○年春天,蘇聯在卡廷森林對二萬多名波蘭軍官進行集體屠殺,卻一口咬定是德國納粹所為。波蘭歷屆由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府皆默認此說法。一九八九年,波蘭的非共產主義聯合政府宣布蘇聯罪行。直到一九九○年,戈巴契夫才承認,但仍拒絕公開檔案。二○一○年,波蘭總統應俄羅斯總理普丁之邀,前往莫斯科參加追悼卡廷大屠殺七十週年,卻連同多名政府機要官員墜機身亡。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訴說的即是此屠殺事件。
2 négationnistes是指否認二戰期間曾經發生猶太人大屠殺者,他們的論點經常傳達出最後解決方案並沒有要屠殺猶太人,只是要將猶太人驅逐出第三帝國,否認者並不認為自己在否認,而是一種歷史修正主義。créationnistes可譯成創造論者或神創論者,據說第一個使用這個名詞的是達爾文,用來指稱那些批評演化論的人。
3阿爾巴尼亞流亡詩人、小說家、二○○五年擊敗大江健三郎、格拉斯、納布吉、昆德拉和馬奎斯五位諾貝爾獎得主,獲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主要作品有《破碎的四月》、《亡軍的將領》等。其作品被譯成三十五種以上的文字,出版了六三七種以上不同版本。臺灣有先覺出版的《慾望金字塔》。
4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總書記,於一九四六年宣布成立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掌權四十年。
5俄羅斯詩人,一九五八年以《齊瓦哥醫生》獲得諾貝爾獎。
6中古世紀吟遊詩人流傳下來的法蘭西史詩,歌頌英雄戰鬥犧牲的事蹟,常為了誇大渲染騎士精神而改编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