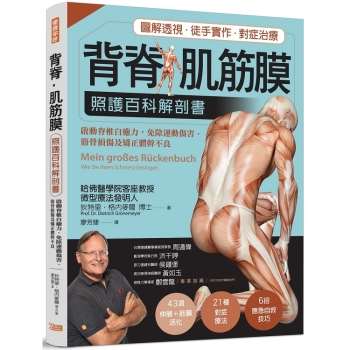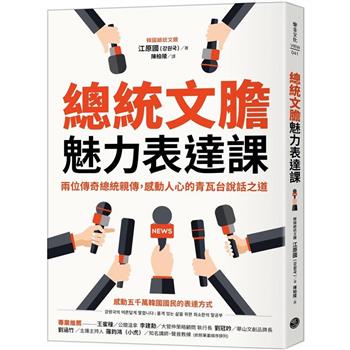前言
1853年4月8日倫敦《泰晤士報》上曾經刊載過一封署名C.T.先生的來信,信中提到他被位於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皇家義大利歌劇院拒於門外的事件:「因為門衛看我的穿衣風格不順眼。」由於極度的憤怒,他繼續寫道:
「我穿著亞麻材質的整潔晚禮服,完美配帶著可以讓我出入任何頂級場所的配飾……而且據那些當時在門口的目擊者說,如果我非要討回公道的話,他們會支持我。歌劇院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我入場。」在抗議了二十多分鐘,並且發現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之後,C.T.只好悻悻然地離開,取回自己的大衣並且到售票處打算索回他的七先令門票錢。但「剛才賣票的人現在卻不肯退錢了,理由是劇院已經入了賬」。同時他也注意到有些進入劇院的人穿著很舊的長大衣或者很厚的外套,還有些人的衣著甚至還很髒。他說他當晚的衣著足以讓他光顧倫敦和那不勒斯之間的任何歌劇院。「可是,我還是回家了」,C.T.氣急敗壞地寫道,「害我沒看成《馬薩涅洛》」。
故事還沒結束。第二天他直接跑去找柯芬園劇院的經理弗雷德里克・賈伊理論,堅持要索回自己的七先令門票錢外加五先令的路費。正如他所說的:「賈伊先生對我的大衣提不出任何拒絕的理由,但卻再一次將我打發到售票處。」
「該怎樣賠償呢,先生們」,C.T.最後火大地說,「也許我該去地方法院告他們,只有在那裡,才能為我失去的時間和激情討回公道與尊嚴。」
關於歌劇史的著作大多將討論集中在傳統的作曲家、作品和演員上。我的書架上也和大多數歌劇愛好者那樣擺滿了這類書籍,當然有許多著作讓我受益匪淺。然而歌劇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它也是一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這點可以從C.T.那封義憤填膺的信中窺見蛛絲馬跡。合適的裝束、門票的價格、觀眾的舉止、經理在圍攻之下表現出來的圓滑、採取法律途徑的威脅手段等等,構成了這整個故事。此外還有C.T.無緣欣賞到的那部作品。奧伯(Daniel Francois Auber,1782-1871,法國作曲家)的《馬薩涅洛》(Masaniello, 也稱《波爾蒂契的啞女》),這是一部鼓舞人心的作品,講述那不勒斯民主政治的崛起。當這部作品於1830年在布魯塞爾首演時,鼓舞了當地人的愛國情操,甚至因此成功地推動了比利時的獨立運動。在《鎏金舞台》這本書中,我們將探索更為寬廣的領域,包括歌劇藝術從創作到發展,到被贊助、聆聽、被感動的過程。我們的目標並不局限於歌劇本身所處的舞臺,還包括圍繞在這個舞台外所發生的一切;我們不僅關注供給,也同樣關注需求,除了歌劇的創作,它的消費情況也應該同樣被我們關注,包括那些將歌劇院、劇團經理、君主、商人、藝術家和觀眾聯繫在一起的關係紐帶。
有的時候我很想發起一場論戰,將「歌劇」一詞完全廢除。畢竟它只代表一部作品,但是對很多人來說,「歌劇」一詞往往被強加了排場、富裕和菁英主義(這是另一個我很想消滅的名詞)等壓力與負擔。我相信那些最偉大的作曲家們的靈魂都會與我站在同一陣線。蒙台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l,1567-1643)將四百年前首演的《奧菲歐》(Orfeo)稱作「音樂故事」(Favola in musica)或音樂的寓言集。據我所知,當時沒有人會以「歌劇」一詞來形容這種藝術形式;事實上它企圖將所有的藝術形式整合
在一起,跟古人甚至當今蓬勃興盛的電影和音樂片製作所追求的一樣。用華格納的話來說,它就是一部「綜合的藝術作品」(Gesamtkunstwerk)。華格納應該也同樣會站在我這邊。
毫無疑問,歌劇藝術在所有表演藝術中是最複雜的一種,它試圖整和太多的要素。鏈條拉越長,暴露薄弱環節的風險就越大,因此歌劇藝術的歷史充滿了傳奇。即使現在回顧其歷史看起來輕鬆,但真實情況卻並非那麼盛況空前。誠然,歌劇藝術的吸引力跟走鋼索或機車競賽一樣,現場演出時總是令人提心吊膽唯恐出現紕漏,無法預知演出能否盡善盡美。從一開始,歌劇藝術就展現了極大的野心,試圖集一切藝術形式於一身,創造出一種絕無僅有的美學成就,以至於無數人為之鼓舞、雀躍、投入心血,並深深著迷。所以,歌劇藝術確實是文藝復興至高無上的藝術遺產之一。
在《鎏金舞台》一書中,我們將隨著歌劇藝術的足跡,從義大利北部的城市開始踏遍歐洲、美洲,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探索其在數位時代的全球商機。本書並非想寫成一本歌劇藝術史,而是想從豐富多彩的故事裡重現當時的盛況。因此,我們的歷史專機將在歌劇版圖上飛越時空,在某處小憩片刻後便繼續飛往下一個目的地。我們將會路過很多小站,為我們直接還原當時的環境,那是一些傑出歌劇作曲家曾經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當然,專機也需要加油,我們也要在一些與歌劇文化有共鳴,但又與作曲者或作品沒有太多關聯的地方稍作停留。因此,我們的旅程會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飛到巴黎的路易十六和柏林的腓特烈大帝。然後,飛去看後拿破崙時代的政權,在試圖建立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時,卻在席捲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傾頹。19世紀中葉,在倫敦或巴黎的歌劇院裡觀看演出也許是一種時尚,但不久之後,大部分重要的作品卻傾向於在慕尼黑、米蘭、拜魯特、布達佩斯、布拉格或聖彼德堡搬上舞臺。
歌劇當然不僅僅屬於歐洲人。在美國的建國史中,一些知識份子曾鼓吹並效仿歐洲人的高雅品味,而莫札特暨羅西尼的劇作家阿瑪維瓦伯爵(Count Almaviva),也將歌劇帶往紐約、紐奧爾良和墨西哥。當那些礦業大亨在澳洲和美洲邊境上高調炫耀他們俗豔怪異的藝術主張時,我們也同時看到歌劇在那裡生根發展。19世紀末,在美國黃金時代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一位英國的贊助人,可能會在這座昵稱為「浮士德劇院」(Faustspielhaus)裡,觀賞一部由德國指揮家所指揮的法國歌劇作品,而演員陣容則可能來自捷克、波蘭和義大利。20年後,人們可能會聽到卡盧梭(Enrico Caruso,1973-1921)在哈瓦那演唱普契尼的作品,或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指揮華格納的作品。
卡盧梭和托斯卡尼尼想必也都無法想像20世紀末歌劇在全球蓬勃發展的情形。歌劇在全世界廣泛的流行的確值得慶幸,但也有人擔心歌劇藝術會陷入過度大眾化的危機中,擔心它的鋒芒會被泛消費主義挫傷,被只想從中獲利的人剝削而淪為商品。但也有人覺得歌劇已經開始變成博物館級的骨董藝術了,它只能吸引富人階級的參與,而這些有錢人卻只滿足於不斷重複地欣賞舊作品,而沒有人想去欣賞新創作。一個會閱讀歌劇史的人,會用心體悟歌劇在四百年發展軌跡中的變化。或許嚴肅的音樂戲劇文化在逐漸大眾化的過程中,和其他領域的藝術那樣,在嘗試著努力開發新的觀眾群時,還期待著能維護自己高貴的美學地位。這種種問題難免會讓我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歌劇將何去何從?在本書的最後,我們會推測在這個充斥著即時全球通訊、國際金融、數位技術的時代,歌劇所面臨的未來,並且以《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式的結局—─一個沒有被解決的和絃來結束本書。
在寫這本書時,我嘗試用兩種截然不同的史學研究方法來進行。首先是在歌劇史中,有大量且不斷增多的優秀學術資料,通常是來自專業的音樂理論家,包括描寫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員們的書籍和文章,內容詳盡。其次是在社會史中挖掘更多齊全的資料。在我首次涉略社會史時,這種研究方法才剛剛出現不久,但是在隨後的數十年裡不斷地發展壯大。直到不久前,這二者之間都還是以鐵柵欄來分開彼此的界限,雙
方都緊閉的大門缺乏通暢的溝通管道,對於在兩個領域各自辛勤工作的人來說這並不奇怪。在那些偉大的歌劇作曲家們的傳記中,往往會按慣例提及一些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社會環境:比如莫札特幼年時期的傑出天賦,或者威爾第在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的突出表現。但如果有人想透過閱讀傳記,去瞭解更多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情形,恐怕就比較困難了。
那些歷史學家而非音樂理論家,可能會固執地堅守在自己的領域中。當一個研究俾斯麥的學者被要求闡述對於腓特烈大帝的觀點,或者當一個中世紀史學家被問及文
藝復興時代時,他們通常會這樣說:「那不是我的研究方向與範圍」。同理,一個研究美國史的人會拒絕評論法國歷史,研究法國史的人又會對俄國史不屑一顧,而這些都涉及知識的完整性。我們沒有人能夠無所不知, 因此都得聽從某個領域的專家的見解,或許這也反映出對於歷史研究的本質與更深一層的態度問題。兩三代人之前,學院裡教授的歷史總是傾向於探討過去的大政治、大外交、大憲法和那些影響事件的人事物。這種局面在20世紀60至70年代開始轉變。伴隨著當時的新激進主義,史學研究的方向被撥向了迄今已被邊緣化或早已被遺忘的庶民歷史中。
當今,文化史的出現豐富了社會史研究的內容;歷史學家從人類學中受益匪淺,並且可以在性別、種族和宗教儀式等問題上大做文章。「文化」二字因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涵義。大部分歷史學家所不屑參與的事物,或許恰巧是他們的前輩們引以為傲的課題:繪畫、建築、文學和古典音樂。正如在音樂史中,往往會忽略作曲家和演員表演所處的社會大背景那樣,社會或文化史也傾向於忽略那些高雅的藝術。也許這是殘留的職業或階級歧視,因為史學家總是意圖想去提升平民的地位,而無法正視歌劇這類菁英娛樂,而歌劇史學家們卻更願意關心這種「偉大的藝術」。
近年來,多虧了那些傑出而有遠見的前輩們的努力,一些藩籬已經被移除,溝通也變得順暢了。本書是建立在他們研究基礎上的一種嘗試,將大故事下的一些要素整合起來。它並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但是讀者們必定會依據自己的喜好,發掘出種種被關注或被忽略的地點、時間或者人物。有時候,這架歷史專機也會降落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進行近距離的詳細報導,而在資料明顯貧乏的地方,就來趟走馬看花式的旅程。我們並不是非常瞭解蒙台威爾第最初創作《奧菲歐》的曼圖亞宮廷是如何生活的, 甚至連《奧菲歐》在皇宮的何處首演都無法確定。韓德爾和他的音樂在漢諾威時代的倫敦究竟有多麼著名?莫札特和他的音樂在哈布斯堡時代的維也納或者布拉格具有多大的影響力?在他們的管弦樂團演奏和在合唱團裡演唱的成員究竟是什麼樣的人?19世紀末紐約的義大利移民是否占據大都會歌劇院觀眾席的絕大部分?答案或許是肯定的,但又沒有任何準確的數據可以用來佐證或者反駁這種直覺。
因此,或出於編輯的需要,或因為證據不足,本書無可避免地在規模和取材範圍上會受到局限。假如這本《鎏金舞台》一定要被視作為一部綜合性的歷史紀錄,那麼我相信,它讀起來一定不會像那些由一個個無聊事件串聯而成、無休無止的編年史那般枯燥乏味。相反地,我在寫作的過程中堅持一個原則,就是把握應有的宏觀思維,引領整體敘事的開闊主題。
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書始終貫穿五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政治。貢薩格、維特爾斯巴哈公爵或者波旁君主推崇歌劇,其目的往往是給某些人(可能是一位競爭中的君主)留下印象,而「流行」歌劇通常更具顛覆性。莫札特辭去了大主教那裡的穩定工作,成為皇帝宮廷及其周邊的一位自由作曲家。在那裡,他邂逅了一生中最屬意的作詞者──在馬丁・范布倫時期的美國度過餘生的威尼斯猶太人。而拿破崙出現在歌劇院,則僅僅是因為他想向人民表示,他在異鄉為他們戰鬥。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中歐大部分地區逐漸淹沒在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這也成為很多經理人和觀眾青睞的歌劇主題,並且在惡名昭彰的第三帝國統治之下一直發展到20世紀。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有關歌劇的菁英主義或者流行性的輿論紛爭,有時也會導致猛烈的政治轉變。
政治之外是經濟。不以金錢和營利的觀點去討論一種企圖包羅萬象的藝術形式,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它真的很昂貴。想要瞭解早期歌劇演員和合唱團以及樂團的薪資狀況,除了近代,關於財務方面的詳細資訊是非常匱乏的,因此我們只掌握了零星的證據,且極有可能是被誇張
了的證據。我們的確知道付給有名的獨唱演員的薪水是多少,一個演出季裡租下劇院的包廂需要多少錢,或者單買一場演出的票價是多少。當然, 底層的「士卒」是我們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歷史記錄還是多半傾向於保留這個領域中「元帥級」人物的財務、債務和赤字紀錄。歌劇很少能在財務上自給自足,如果有一個問題像迴旋曲主題一樣不停地縈繞在我們的故事當中,那麼這個問題一定是:誰來付錢?或者說是由誰來填補財務赤字。所以,歌劇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系列貴族和君王的故事、風險運作的劇團經理的故事、慷慨的銀行家和企業家的故事、地方或中央政府撥款補助的故事,以及後來通過各種具有獨創性,或多或少的免稅方案,以及從贊助商和私人捐贈中籌錢的故事。
本書中也提及許多不同的貨幣,從威尼斯的達克特到法國的法郎,從義大利的里拉到現代的英鎊和美元。我們無法用比較的方式將它們都換算成單一貨幣,讓大家更容易理解。不過,我試圖透過引述來為大家提供直觀的幣值概念,例如,一個歌劇首席女歌手的出場費或者劇院的票價、當時一個典型工人的日薪、一個麵包或餐館裡一頓飯的價格。
歌劇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歌劇聽眾性質的轉變,或者說那些轉變的大致輪廓,很容易被清楚地描繪出來。隨著權力和金錢從貴族、教會以及更高的君王階層,向新興的中產階級和稍後更大範圍的社會階層轉移之後, 聽眾性質的改變也隨之產生。這種變遷可以從多種現象得到證實,例如歌劇院本身的外觀設計(像現代歌劇院中的包廂及其他突顯社會差異的元素已經相對淡化)、觀眾看歌劇時的行為舉止和衣著,還有價格政策、演出海報和節目單的設計風格、供應的食物和飲料等等。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歌劇的職業演員,特別是那些有天賦的女歌手,歌劇事業為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提供了罕見的機會。
在社會變遷的同時,我們還應該關注科技進步為歌劇帶來的影響。早期歌劇主要是在炫耀那些五花八門的神奇舞臺效果,例如:厄洛斯飛過頭頂、朱比特或朱諾自天界下凡,或是戲裡像唐璜那種十惡不赦的惡棍被打入地獄等等。佈景、機關與音樂、劇本同樣受到重視。事實上,許多歌劇經常將最先進的科技技術當成宣傳亮點,儘管難免有些誇大,例如《女人心》(Cosi fan tutte)中對麥斯默醫生的誇張描繪。我們也會談到蠟燭、煤氣和電氣照明,談到薄紗和一種在舞台上用來模仿人們在水中游泳的舞台道具:游泳機,還會提到鐳射和字幕的應用等等。另外,我們的故事還將包括打破劇院的局限來傳播歌劇(包括聲音和圖像)的新作法:音樂的出版與版權觀念的抬頭,以及隨後的新發明──照相、錄音、電影、電視、錄影和最新的衛星與數位技術等。
最後,歌劇當然是一種藝術形式,因此這本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一部文化史。關於這一點,有幾段重要的歷史軌跡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每段軌跡都和更加宏觀的歷史潮流相互對應。首先是那些讓歌劇藝術夢想成真的人;歌手也很重要,我們的故事將會給他們很多戲分,讓我們瞭解那些巨星們的生活、資金來源和藝術成就。但是在我們的故事從非嚴格界定的「贊助人的歌劇」(從曼圖亞的貢薩格公爵,到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到「作曲家的歌劇」(從格魯克和莫札特,到普契尼和理查•史特勞斯),再過渡到「指揮家的歌劇」(馬勒和托斯卡尼尼時代),繼而發展成近年來「製作人的歌劇」,每一個人物都輪流承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然而究竟誰才是觸發你去聽歌劇最首要而關鍵的吸引力呢?
最後才是藝術本身的變化。大體來說,有兩條線索交織在本書的故事裡。第一條,在我們邂逅的文藝復興晚期的義大利的宮廷內,如韓德爾、華格納、威爾第和布瑞頓的作品那樣,屬於我們所說的「嚴肅」歌劇,它們旋律各異、情緒高昂、技巧圓熟、格調高雅。另一類,則是一種更加「流行」的風格,有著戲謔的曲調和易懂的對白。從威尼斯人的即興喜劇,到《乞丐歌劇》和《魔笛》,再到維也納輕歌劇、吉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 II,兩位都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幽默劇作家)等等。早期,劇迷們總是希望能看到新作品,就像今天的電影觀眾那樣。但是到了20世紀初, 觀眾卻開始傾向於反覆觀看被認為是經典的標準劇目,這類正在形成的所謂經典,很難加入新作品。除了這種根本性的變化之外,歌劇的劇情和製作,也將注意力從幾個世紀以來高高在上的君主和神話般的英雄人物,轉移到普通人和「受害者」身上。同樣地,歌劇的音樂也漸漸從格式化的詠歎調和宣敘調,轉向更綜合性的音樂戲劇,因而有可能變成心理劇,或者是近年來流行的「音樂劇」。但這些是歌劇嗎?
或許,歌劇只是一個詞彙,我們用來稱呼在歌劇院中製作的音樂戲劇;如果《理髮師陶德》(Sweeney Todd,源自恐怖小說《一串珍珠的浪漫史》,1973年由克里斯多夫.龐德將它搬上英國史特拉福特皇家劇院,引起轟動。) 能夠在柯芬園劇院演出,便說明它的確是一部歌劇。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的說,歌劇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形式就在於它是現場演唱,而且要以一種恰如其分的「歌劇式」的唱腔來演唱,不借助任何電子擴音設備而能傳到劇院的任何一個角落。當我們聽到歌劇的特殊唱腔時,我們立刻就能分辨出來:布萊恩.特菲爾(Bryn Terfel,樂壇當紅的男中音)才有這樣的嗓音,而艾爾頓.強(Elton John)就沒有。歌劇,就如同瞎子摸象,當我們能看見它時就能辨認它,如同我們想向從未聽過歌劇的人描述歌劇的樣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樣。更或許根本就沒必要如此嚴苛的來定義歌劇的形式。因此,我不會去為歌劇尋求一個高度概括而萬全的新定義,而只是想建議讀者不要過於狹隘地去定義它。
因為我們無法避開這樣的結論:至少普遍認為,歌劇是一種在漫長的19世紀──從莫札特時代到普契尼去世為止的這段時間──達到發展巔峰的一種藝術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或許會被認為是一本關於這門菁英藝術從興起、衰微到沒落(甚至可能是湮滅)的記錄。根據這本書,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歌劇只不過變成了一種博物館級的藝術罷了。或許,我們是在記錄歌劇的大眾化進程,從一種曾經偉大的藝術形式,到漸漸洗去鉛華,或簡化成淪落到當今的境地。在藝術鑒賞家狹窄的世界之外,它所具有的吸引力,必然都是來自於無所不用其極的行銷手段所炒作出來的虛幻吸引力。但另一面,如果你是屬於樂觀積極的那群人,那麼儘管比吉爾達(Gilda,威爾第歌劇《弄臣》中的女主角)和崔斯坦(Tristan,華格納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中的女主角)更痛苦地掙扎,歌劇也絕不甘於死亡。相反地,我也要證明,歌劇作為一種最為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反而有了繁榮復甦的跡象。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鎏金舞台:你不可不知道的歌劇發展社會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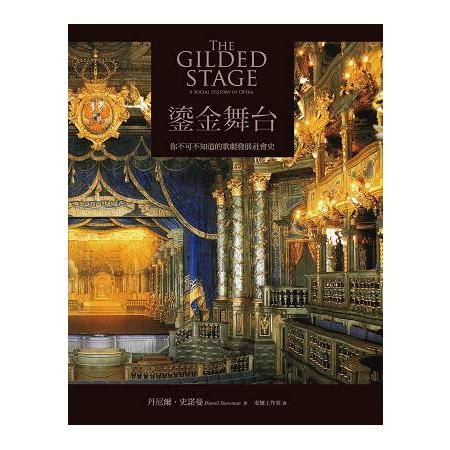 |
鎏金舞台:你不可不知道的歌劇發展社會史 作者:(Daniel Snowman) / 譯者:安婕工作室 出版社:華滋出版 出版日期:2017-01-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2頁 / 16.5 x 21.5 cm / 普通級/ 部份全彩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40 |
社會人文 |
$ 510 |
中文書 |
$ 510 |
戲劇 |
$ 522 |
戲劇總論 |
$ 52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鎏金舞台:你不可不知道的歌劇發展社會史
浩瀚的巨作,絕對媲美史上最佳的歌劇。——Tim Blanning
史上第一,也是目前唯一講述歌劇社會史的巨作
歌劇,世界上浪漫、絢麗、迷人,也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菁英藝術,
它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也是一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
無論是莫劄特在維也納的繁華、腓特烈大帝在柏林的喧囂、
頹廢巴黎的誘惑、澳洲內陸的荒蠻、新富美國的附庸風雅……
無論在哪裡,「歌劇院」都被視作是高度文明的象徵與政治的強力宣告。
透過《鎏金舞台:你不可不知道的歌劇發展社會史》,
我們將焦點從歌劇舞臺移至圍繞在其周遭的一切,探索更寬廣的領域。
本書除了歌劇的創作、供給與需求,
同樣也關注包括歌劇院、劇團經理、君主與商人、藝術家和觀眾,以及當時社會狀態等等。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作者講述了歌劇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北部,隨後迅速橫掃歐美大陸,
風靡世界各地,直至數位化普及至今日等經久不衰的歷史。
本書具備無可挑剔的學術性,
同時以歷史和世界的視角,重現曾經孕育歌劇的社會背景,既有宏觀論述,又有迷人的細節描寫。
作者簡介:
丹尼爾•史諾曼(Daniel Snowman)
社會文化史學家,現任倫敦大學歷史研究協會的高級研究員。
出生倫敦,先後就讀於劍橋及康奈爾兩所知名學府,年僅24歲便一躍成為薩塞克斯大學講師,教授政治學和美國研究方面的課程;29歲加入倫敦愛樂樂團,直到今日依然參加演出。1970年正式加入BBC,作為廣播節目的製作人,主要負責各種文化和歷史題材的節目,長達25年的媒體人生涯,為日後的著書立說積累了大量的材料。1995年後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寫作和演講,他的著述不僅有音樂家的研究,也有深層豐富的文化史研究與社會學領域的比較研究。正是這些複雜、多元的經歷在他身上的高度重合,才誕生出這樣一部《鎏金舞台》。
TOP
作者序
前言
1853年4月8日倫敦《泰晤士報》上曾經刊載過一封署名C.T.先生的來信,信中提到他被位於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皇家義大利歌劇院拒於門外的事件:「因為門衛看我的穿衣風格不順眼。」由於極度的憤怒,他繼續寫道:
「我穿著亞麻材質的整潔晚禮服,完美配帶著可以讓我出入任何頂級場所的配飾……而且據那些當時在門口的目擊者說,如果我非要討回公道的話,他們會支持我。歌劇院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我入場。」在抗議了二十多分鐘,並且發現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之後,C.T.只好悻悻然地離開,取回自己的大衣並且到售票處打算索回他的七先...
1853年4月8日倫敦《泰晤士報》上曾經刊載過一封署名C.T.先生的來信,信中提到他被位於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皇家義大利歌劇院拒於門外的事件:「因為門衛看我的穿衣風格不順眼。」由於極度的憤怒,他繼續寫道:
「我穿著亞麻材質的整潔晚禮服,完美配帶著可以讓我出入任何頂級場所的配飾……而且據那些當時在門口的目擊者說,如果我非要討回公道的話,他們會支持我。歌劇院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我入場。」在抗議了二十多分鐘,並且發現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之後,C.T.只好悻悻然地離開,取回自己的大衣並且到售票處打算索回他的七先...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從亞利安那到魔笛之旅(1600—1800)
義大利歌劇的誕生
義大利式歌劇的經營模式
飛越阿爾卑斯山和海峽
莫札特時代維也納的文化融合
第二章 大革命和浪漫主義(1800—1860)
拿破崙與貝多芬
後拿破崙時代:歌劇與政治、藝術和商業
歌劇抵達紐約及更廣袤的邊陲地區
巴黎歌劇院
倫敦大火
第三章 歌劇的復活(1860-1900)
中歐和東歐的文化與政治
紐約的黃金時代
首席女歌手
馴獅人:指揮的權勢
第四章 戰爭與和平中的歌劇(1900―1950)
歌劇走向西部
傳播訊息
戰爭的影響
獨裁統治下的歌劇
全面戰...
第一章 從亞利安那到魔笛之旅(1600—1800)
義大利歌劇的誕生
義大利式歌劇的經營模式
飛越阿爾卑斯山和海峽
莫札特時代維也納的文化融合
第二章 大革命和浪漫主義(1800—1860)
拿破崙與貝多芬
後拿破崙時代:歌劇與政治、藝術和商業
歌劇抵達紐約及更廣袤的邊陲地區
巴黎歌劇院
倫敦大火
第三章 歌劇的復活(1860-1900)
中歐和東歐的文化與政治
紐約的黃金時代
首席女歌手
馴獅人:指揮的權勢
第四章 戰爭與和平中的歌劇(1900―1950)
歌劇走向西部
傳播訊息
戰爭的影響
獨裁統治下的歌劇
全面戰...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丹尼爾•史諾曼
- 出版社: 華滋出版 出版日期:2017-01-26 ISBN/ISSN:978986935489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32頁 開數:16.5x21.5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