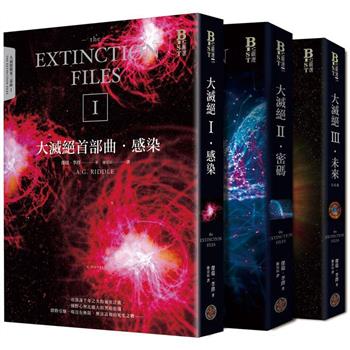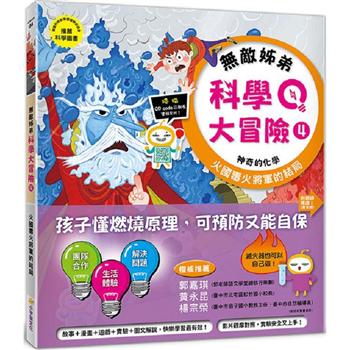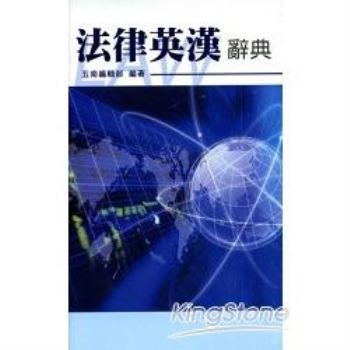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路有多長:差事劇團二十週年紀念文集的圖書 |
 |
路有多長:差事劇團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作者:策劃:鍾喬 出版社: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25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劇場實務 |
$ 405 |
中文書 |
$ 405 |
戲劇家傳記/文集 |
$ 405 |
劇場實務 |
$ 405 |
表演藝術 |
$ 405 |
藝術設計 |
$ 405 |
戲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文集收錄差事劇團團長鍾喬、文化工作者、文字工作者、劇團成員等,共計32篇文章,內容包含差事劇團的發展、差事民眾戲劇的特色,以及差事劇團廿年以來所參與的各項文化工作。在廿年的時光中,回顧、探索民眾戲劇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本書特色
差事劇團自1996年成立,是台灣少數運用民眾戲劇(People’s Theatre)的訓練方法暨理論系統,針對現實的思考出發,融合在地的歷史與生活經驗,在現代劇場中探索表演美學。
除了常規年度性的演出外,並且透過經常性的社區/教育劇場工作坊,與學校、社區和弱勢團體間共同發展戲劇環境。在冷戰/戒嚴的體制性延伸下,開啟了第三世界的身體行動劇場,在這樣的脈絡下,以探索前行的霧之旅程,摸索著全然轉換了場景與腳色的亞洲第三世界民眾戲劇。
作者簡介:
策劃:鍾喬
生於一九五六年,「差事劇團」負責人,亦是劇作家、導演、詩人。
一九八○年代中期,接觸了「鄉土文學論戰」與左翼思潮,深受陳映真先生影響,先後參與《夏潮》雜誌與《關懷》雜誌,曾擔任《人間》雜誌主編;九○年代後,和菲律賓、南韓等亞洲第三世界與民眾劇場工作者接觸,成立「差事劇團」,並推動具有民眾戲劇性質的社區及市民劇場。
鍾喬的戲劇理念受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影響甚深,無論是寫詩或劇場演出,他想傳達的主題都是:讓弱勢者能用身體表達,發出自己的聲音。
曾編導小劇場作品《記憶的月台》、《海上旅館》、《霧中迷宮》、《潮喑》、《敗金歌劇》、《另一件差事》、《台北歌手》等。作品曾受邀前往日本、澳門演出,並赴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出。劇場相關作品有《邊緣檔案》、《亞洲的吶喊》、《觀眾,請站起來》等文集與劇作集《魔幻帳篷》,小說有《戲中壁》、《阿罩霧將軍》、《雨中的法西斯刑場》,報導文學有《回到人間的現場》,散文集有《靠左走:人間差事》等。已出版詩集有《在血泊中航行》、《滾動原鄉》、《靈魂的口袋》及《來到邊境》。
編者:
范綱塏,桃園人,1988年生,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
1997年參與了差事劇團的學生戲劇營,從此便於差事有了不解的連結,直至今日。
嘗試寫過三篇劇評,也都是關於差事的戲。
編有《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運動30週年記錄文集》一書。現為自由工作者。
鍾喬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再提魯迅的散文詩〈影的告別〉了!這文字裡頭,埋著很深很深的針,刺痛著我們夸夸然、並總以為前進的人生步伐。它這麼簡單卻森然地說著,對麻木而茫然的我們說著:「朋友,時候近了。我將向黑暗裡徬徨於無地。」
我總想,作為一個以民眾戲劇為出發的劇團,說我們在行成一種「眾志」的同時;恰如其職志地,也在展開走向社會或世界底層的文化行動。但,詭奇的是,這職志本身,卻也潛藏著諸多不那麼理所當然的世態!這是必須去面對的經常性撞擊,通常以意識或潛意識狀態,倏忽便雷擊般閃過社會或心靈...
鍾喬回顧:二十年後,回首看「差事」……
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
文化行動的入徑
石岡媽媽劇團
少年哪吒的變身
文化行動:「差事」的劇場與社會實踐
李秀珣-迴盪在換幕到真實的裂縫中
楊珍珍-石岡媽媽劇團走過十七年
洪滿枝-在劇場實踐異鄉姊妹的「差事」
高琇慧-從這裡到那裡
許立儀-不論何處是鄉關
李慈湄-製造琥珀的人
曾伯豪-走過台西村
劉逸姿-一場重返土地的文化行動
吳文翠-以藝術來呼應人與土地
范綱塏-接續歷史的休止符
穿越的視線:他人眼中的「差事」
于善祿-給布雷希...
- 作者: 策劃:鍾喬
- 出版社: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11 ISBN/ISSN:978986936004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64頁
- 商品尺寸:長:200mm \ 寬:150mm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