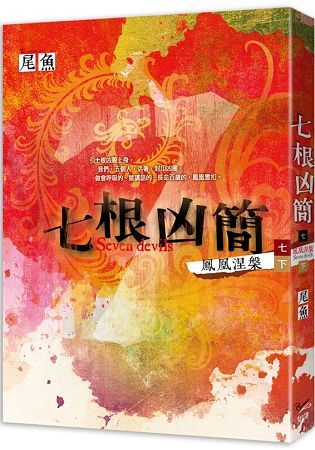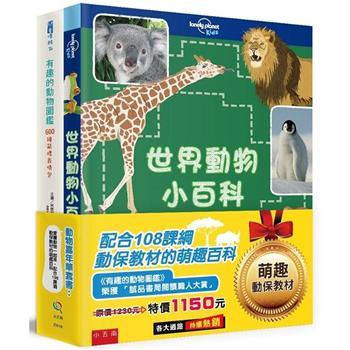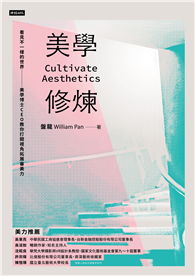鳳凰鸞扣,七根凶簡。
長久以來一直念叨的東西,忽然間這麼大剌剌地出現在眼前。
為了解開所有的謎團,找出最後一根凶簡,
鳳凰別動隊加上神棍等一行人想了又想,
居然得出這第七根凶簡,可能就在他們這五個人身上的結論。
可……不是說擁有鳳凰鸞扣的人,不會被凶簡附身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了封印凶簡,一行人決定帶著凶簡上鳳子嶺,
在完全未知的情況下,他們想出了一個封印的方式,
那就是……
「神先生,我要是回不來,你就把解放放生,可別吃了牠啊!」
最後凶簡的下落,沒有結果的悖論。
封印凶簡的方式,鳳子嶺上的犧牲。
他們的旅途,終於進入了尾聲。
本書特色
◎華文驚悚懸疑小說新銳第一人──尾魚最新作品
◎百萬點擊,網路讀者搶讀追捧之作,繁體版搶先出版!
◎知翎文化繼《凶宅筆記》之後,強力推薦之優秀長篇小說!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七根凶簡七 鳳凰涅槃 下(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4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小說 |
$ 190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216 |
中文書 |
$ 234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七根凶簡七 鳳凰涅槃 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