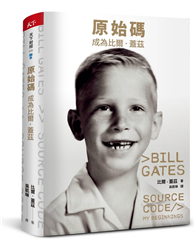一個女孩,突由痴傻轉為聰穎,含苞待放;
一名老人,帶著女孩回到老宅,與世隔絕;
一樁祕聞,三十年前的竊玉案,牽出三家名門的愛、恨、情、仇……
一名老人,帶著女孩回到老宅,與世隔絕;
一樁祕聞,三十年前的竊玉案,牽出三家名門的愛、恨、情、仇……
她是蔣府的四小姐,亦是翠玉軒的新頭家!
祖父託予她的世代傳承與未了心願,她統統都會替他完成──
如花似玉,含苞待放。
三十年前,一樁私吞官玉的案子,讓蔣、徐、周三家名門有了難解難分的愛恨恩仇。
蔣欣瑤從祖父身邊的老人聽聞往事,也終於明白蔣府內那正室外室、嫡庶罔倫的糟心事由。
祖父年邁,卻一生為著情愛浮沉,勞心傷神,最終只能離開偌大的蔣府,與病弱的她來到老宅休養,與世隔絕。
他可是她來到這兒最親近的人!那段如在世外桃源般悠閒生活的時光,真真切切的彌補了她初來乍到的不適與被迫與家人分離的情感。
如今,她得了祖父的人脈與資產,決心為他查清真相、尋回摯愛,她定要讓欺他至此的惡人,付出代價。
她,蔣四,再不是任人欺凌揉捏的嬌弱千金!
本書特色
☆起點女頻人氣作家包子才有餡佳評如潮的種田經商宅鬥好文,總點擊數超過66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