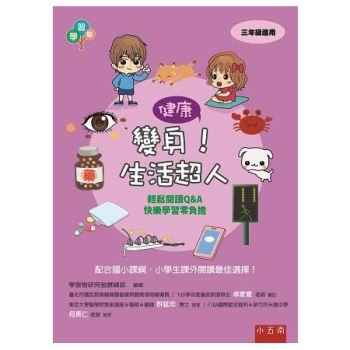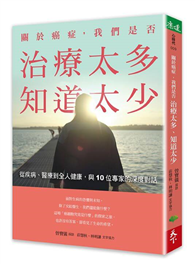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我過去相信、現在依舊相信人人皆手足,都值得幫助。
我想幫助阿富汗人,我以為憑著善意與些許膽識就夠了。」
《窮人》作者、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威廉・福爾曼報導寫作原點。
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三年後,遠在美國、年方二十三的福爾曼決定用自己的方式幫助阿富汗人——他打工攢錢,自費從家鄉輾轉前往阿富汗。他要加入聖戰士行列,與當地人一同對抗蘇聯。
從巴基斯坦一路前進阿富汗,這段看似天真、勇敢,卻又近似荒謬的歷程也成為一個年輕人對於戰爭與人性的發現之旅。
目睹巴基斯坦收容營內的阿富汗難民景況,與流亡異地的將軍、政客,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的觀察、訪談、互動,福爾曼態度抽離、但情感飽滿的觀察文字不僅記錄下個人複雜的道德與情緒反應,更捕捉到戰爭與流亡中的眾生人性景象。
《阿富汗幻燈秀》的採訪記錄兼具影像感和自傳元素,囈語、跳躍、自我嘲諷的敘事充分展現福爾曼獨有的報導風格,細膩刻劃一個少年服務他者的信念,以及在暴力陰影下糾纏於理想主義的頑固意識。
作者簡介:
威廉‧福爾曼 William T. Vollmann
二○○五年曾以《歐洲中央》(Europe Central)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福爾曼著有探討貧窮問題的《窮人》(Poor People)一書,以及多部長篇小說及故事集 ,當中包括批判暴力的七冊巨著《暴起與沉淪》(Rising Up and Rising Down),探索美國「火車扒客」地下文化的《行向無窮處》(Riding Toward Everywhere),記述性別跨越經驗的《朵蘿瑞絲之書》(The Book of Dolores) 等作品。
此外,福爾曼亦曾獲國際筆會美西中心小說獎(PEN Center USA West Award for Fiction)、席瓦‧奈波爾紀念獎(Shiva Naipaul Memorial Prize)、懷丁作家獎(Whiting Writers' Award)等獎項。他的報導和小說創作亦常見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君子》(Esquire)、《Spin》、《格蘭塔》(Granta)等雜誌。現居加州沙加緬度 。
譯者簡介:
張家綺
畢業於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英國新堡大學筆譯研究所,現任專職譯者,譯作十餘部。
章節試閱
【序】節選
二〇〇〇年,踏入當時是塔利班政權的阿富汗前夕,我去探訪了早先招待過我的N將軍,他的名字將在《阿富汗幻燈秀》大量曝光。老人家如今是更加老了,腦袋不若往常靈活,我從一九八二年就收著的名片上那組電話號碼如今都多了兩碼。他歡天喜地迎接我,沒忘記我,我帶著愛與敬意握住他的手。
踏上參與戰事之路並寫下《阿富汗幻燈秀》,曾令我自以為是長篇冒險故事裡悲欣交纏的主角。事實上,真正的主角是N將軍。他供應我庇護所,讓我衣食無虞,把我裝束成帕坦人,安排我進出阿富汗的安全通道;更重要的,是他在我思想完全封閉之前進入我的大腦。我們是一輩子的朋友,他說。確實如此。雖然僅以信件為交流管道,甚至在數年後這項連繫還是斷了,我深深明白這位大好人之所以記認著我並不是因為我的美國人身份,也不是因為他認為我無所不能或無所不學,而是因為,在他漫長的接濟史當中,我佔有數頁篇幅。
進入巴基斯坦我至少預想到:要帶著對照版的《可蘭經》。這本《可蘭經》至今仍留著,每次前往穆斯林國度都隨身攜帶。與東道主一起讀《可蘭經》,對於我這種非穆斯林人士而言,是一種表達興趣、展現誠意與尊重的好方法,還可以對當地習俗增長見識。我曾經和N將軍一起讀《可蘭經》,這跟我在共產國家讀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作品的理由相當。二〇〇〇年回頭拜訪時,我請他解說一段經文,兩人都感到相當愉快。我在這段經文有所學,也再次更瞭解他。
依舊歷歷在目,一九八二年酷夏與N將軍一起讀《可蘭經》,也還記得那棵萊姆樹。他的孩子們如今都已長大成人遠走他鄉。我確知並深信他不同反響的好。我恐怕永遠都不會成為穆斯林,也不可能成為帕坦人,但我或多或少可以感覺到,身為N將軍這樣的人是如何滋味。他與我如此南轅北轍,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交戰難休,為此我無比傷心,但絕不放棄信念,會持續努力讓眾人看見兩方親如手足。嗯?這不是廢話嗎?我還真希望夠廢話!
如同我在《阿富汗幻燈秀》裡所寫,將軍告訴我,要實踐任何事業,必須有一組大腦、一顆心和一雙手。單單就最值得投入的事物而言,一般水平的大腦已經很夠用,也就是說,本書讀者至少有一半在這方面達到水平以上。很多人也都行事用心,都想把事做好(我自認曾有此貞)。而雙手卻是另一回事,N將軍口中的雙手其實是能力──你擅長甚麼?更明確一點說,假如你擁有充足資源,甚麼事會被做到最好?在覓得一堵合適的牆面之前,是否已在腦中勾勒一幅傾訴良善和真相的壁畫?與九一一事件相關的恐怖議題,不會在我們人生中自行消弭,每個人都必須竭盡所能去理解他人的傷痕,以愛以誠,以正當手段,協助他們獲取所需。此舉不僅點明慈善者的必須作為,更指出恐怖主義威脅之下所有個體的焦點所在。 W.T.V(二〇一三)
【第三章 創造奇蹟何其難】節選
少年A在國王餐廳吃午餐,點的是炸雞配饢餅。說穿了,雞肉不過雞油包雞骨吧,顯而易見上桌這一隻被反覆熬湯榨得很乾。在場正好有人點湯。餐廳送來刀叉給這位老外顧客,服務生和餐廳老闆一致用近乎虔誠的興致盯著,看他如何吃食。這些西式餐具他可不是沒見過。也從不曾用得這麼綁手綁腳。雞翅骨在湯裡心不在焉地(希望這個形容還算準)游晃像在泡澡,他虎視眈眈舉起叉子逼近,把叉子弄得溼漉漉的。每回叉子在湯裡浸淫過,尖端都停著一滴水噹噹的油脂。他時不時將之冷然送入嘴,若有所獲,吸吮著,嚐起來簡直像內臟和雞毛也下鍋煮了。他小心翼翼撈尋軟綿綿的血塊或雞冠,又一個不小心雞翅骨翻了面,驚見有塊肉,可惜刀叉攻不下,畢竟他不是法國或義大利長大的;那兩地的老先生會在下午持銀製器具給水蜜桃剝皮,剝得皮是皮、肉是肉,絲毫不浪費。少年A是美國人啊。逼得他只好徒手探入不冷不熱的油膩湯水直擊雞翅骨,迎著關節處折斷,才闖關成功取得那塊肉。硬梆梆的雞骨回頭彈在盤上,他的餐桌為之一震,服務生嘖嘖出聲──出於同情還是挑釁,這就不好說。
「真是不好意思,先生,」餐廳老闆站在櫃台後,「很新鮮的。」這老闆是個身穿印度軍隊制服的禿頭佬,他從後邊觀望著這間幾乎無人的餐廳,重複播放著一捲卡帶。卡帶播到底,翻面,音質猶如包覆在靜電中的靜電,發出悶悶嗡鳴,汽笛風琴殘音的證據,妓女的處女膜一般。
好吧,少年A心想。把雞肉放棄,少年A抓起幾塊饢餅沾油。至少他們卑躬屈膝,沒多管閒事溜舌頭,也道歉了。好吧好吧。好──吧。當一千名服務生奮不顧身,在你彈指或揮舞一張盧比大鈔時飛奔幫取水、幫點菸,你不得不相信:再沒有更動人的畫面。在扇葉刮出的風中,餐巾紙宛如賽車旗幟般飄揚,他壓碎另一塊雞骨頭為食慾引航,又疾行前去。驕傲偉大的美國少年A就要來拯救第三世界。
【第五章 至少可在此久留】節選
步步逼近阿富汗
此刻少年A正要前往開伯爾隘口,從此就能對別人說我去過。在邊境有人告訴他,可朝蘇聯警衛招手,對方會回禮,拍照也行,但等等──他還沒到邊境啦。公車載著他穿過沙漠,直上龜裂似的紅色山脈,灰塵從敞開的窗口撲進來,行進中拂過車身。在檢查站,男孩們透過車窗兜售老舊汽油桶盛裝的水,飲用後歸還容器。少年A臨座的乘客買了一些水請他喝,味道很棒。繼續挺進山巒,途經三個穿連身罩袍在樹下蹲踞的女人,烏鴉休憩一般。當公車進入部落區,幾個男人開始抽起哈希什,鄰座遞來一撮,還為他示範使用。抵達有著古舊矮房的詭祕小鎮蘭地科塔,在此換車,邊境小鎮托克哈姆就在五公里外了。換上的這台是老爺休旅車,其他乘客都是遊牧民族,老人鬍鬢皆雪白,孩童手中有雞提著,罩紅袍的女人蓄長辮、戴銀耳環、面部無紗。他說的普什圖語簡直雞同鴨講。「喀布爾?」乘客問。少年A搖頭。「托克哈姆。你們全要去喀布爾?」「對,喀布爾。」有個男孩帶著鴉片來賣,被父親拍打制止了。繼續前往托克哈姆,遇上例行檢查,官員以棍棒戳弄糧食袋,東張西望,一注意到少年A便頓時停下動作,大叫起來,拉拉扯扯的把他拖下車。少年A一如既往,覺得歡樂是最佳的防衛措施,於是手一揮,笑咪咪地向其他乘客道別,當場鴉雀無聲。公車繼續開往喀布爾。在防空洞,官員謹慎查看他的護照,他像一般美國人那樣問可否拍照,神色友善卻茫然,直到終於放行。對方帶他上貨車後座,回蘭地科塔,放他在公車站又一語不發揚長而去。
山區邊緣有很多防空洞。在決定該如何處置少年A時,官員的專注被不時打斷,視線投向天空的飽滿湛藍,向著阿富汗的方向。遠方轟鳴傳來,是一架飛機。
可能得去難民營的男人
少年A與伊斯蘭大會黨政治辦事處的納吉卜博士,進行了另一場沒有結論的訪談,結束後少年A招了人力車回沙達。那位「羅得西亞僑民」宣稱美國中心是個好所在,有空調設備,有雷根總統的彩色肖像,少年A決定到此一遊。他想獨自窩著一小時──《時代》雜誌、《新聞週刊》,甚至《黨派評論》,那裏都有,全都拿一本。先找了張乾淨的圓桌坐下,最終還是去到室外,穿著寬鬆棉白衣褲的男人盤腿坐在刷白漆的小店內,衝著他笑咪咪或注視他,賴以為生的織布機索然乏味地閒置,他們的手亦靜止不動,每個人似乎都長著一張黝黑面孔、暗色頭髮、深邃黑眼、落腮鬍和潔白牙齒。夏日般亮白的牙齒猶如粉筆灰,抑或白沙瓦的英國軍營樹下的滾滾路塵。想到這些畫面,他的快樂就像鍍上金子。你來我往欣賞打量的儀式結束後,他回到飯店裡自己的房間,每一面骯髒牆壁都如烤箱門般熱燙,即便在晚上,螞蟻生態依舊歡樂不斷,不疾不徐爬過他的床。浴室裡,一隻蟋蟀帶頭歌唱,這情況已經持續多日。送來烤焦空氣的風扇,時不時跟電燈一起陣亡(白沙瓦的電力反覆無常),但在美國中心,情況是再好不過。他先是拾起《時報》雜誌。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有所動作,他發現另一張桌子坐了個阿富汗人,目光不斷射來,他故意視而不見,繼續閱讀《新聞週刊》。《新聞週刊》似乎也贊同《時報》雜誌的說法。
停電了,起初只是一片烏暗,不到五分鐘變得又熱又黑。多數人已經離開,員工為其他人拿來火光曖然閃爍的燈籠,少年A留下來,指望電力能盡快復甦,否則也無法讀報章雜誌。他抬眼,那阿富汗人對他微笑,他也回以笑臉,阿富汗人旋即過來加入他,拿燈籠開開小玩笑。「好像回到我父親那個年代。」他說。
阿富汗人是一名外交官的弟弟(當然也已是前外交官),痛恨巴基斯坦。「阿富汗曾經統治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大聲嚷著,神色猖狂地環顧四周,「他們什麼都不是,只是個愛錢的奴隸國度!他們不肯幫我們!」他帶少年A去一間冰淇淋店,買一罐雪碧給他,口乾舌燥的少年A馬上整罐乾掉。「上個月,這罐雪碧才兩盧比又五十派沙,」阿富汗人說,「但現在要價三盧比又五十派沙,擺明要我們日子難過。」
阿富汗人說,他晚上會吞鎮定劑。他今年三十歲,頭髮已開始灰雜。要是阿富汗自由了,他一定即刻返國。「但我也喜歡美國,」他用安撫人的口吻說,「美國是非常好的國家。」有人告訴他,去那裡可以立刻交到女朋友、獲得一間公寓和一輛凱迪拉克轎車。他請少年A打電話給領事館,幫忙安排他明天離開。
他不敢相信少年A辦不到。「那你說,自由是什麼?民主是什麼?」
他說因為他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女孩不能跟他約會,他非常孤單。他問少年A有沒有女朋友,少年A說他就快結婚了。「很好,」這名阿富汗人用低沈嗓音說,「你有超能力,無所不能。反觀我,一無是處。」
少年A不知該回什麼。
他央求少年A幫他申辦簽證。
「拿不到簽證會怎樣?」少年A像丟一個大禮包般將問題扔回去。
「要是不能,我就……」聲音不確定地消逝飄走,「我幾個月就會把錢花光……」
「接著呢,怎麼辦?」
他笑了:「我──我也不確定。」
他清清喉嚨:「我也試著找工作,就是找不到。」
「你覺得,」少年A繼續追問,「錢花光就得去住難民營?」
「對,對,我勢必得去。」
「那接著會怎樣?」
「不知道。可是對我來說美國是很好的過家,是非常大的國家,要是能找到人幫我辦簽證,就能去了。」
「謝謝你。」少年A關掉錄音機。
【第六章 加州的幸運難民】節選
美髮師
「所以今天要剪加燙囉?」安吉拉說。珍妮速速點頭,雙腿交叉著。安吉拉取出顧客資料卡。珍妮在座椅上瞪鏡子玩頭髮。寬袍套上。
「蠻長的,」珍妮說,「我剪髮都會順便燙,那就燙一燙唄。」
「蠻乾的,」安吉拉說,「若沒意見,我就上點乳液囉。」她帶珍妮到後面洗頭。
美髮師部門是個明亮的場所,切分成二,一邊是寬闊走道,另一邊是角度彎向窗子的數個半隱密隔間。安吉拉的隔間在室內中央處,窗明几淨,井然有序,瓶瓶罐罐分立在鏡子底緣。櫃子頂端一塵不染,閃著光卻不刺眼。
珍妮的一頭濕髮從額頭往後收攏,笑咪咪地回到座椅。站在她身後的安吉拉,穿著藍色絲質襯衫,膚色棕亮,黑髮茂密,濃眉毛加上烏溜溜大眼,樣貌很標緻。珍妮說,覺得安吉拉看上去蠻有波斯人風韻。安吉拉一邊上捲子,一邊開心聊著祖母下個月會從印度過來一起度假的事。那上滿捲子的一顆頭簡直像穿山甲。安吉拉接著在珍妮頭上纏繞一圈棉花,加燙髮藥水,然後罩上一層膠膜。
「看來你樂在工作?」珍妮說。這話我聽來根本挾帶惡意。安吉拉也曾衣食無虞。
安吉拉身子一僵:「還行。」
安吉拉和珍妮都想當醫生,兩人都是亞洲移民,珍妮已成功當上醫生。安吉拉抵達美國後退而求次,只想當護士,可惜仍事與願違。她弟弟想當工程師,找到的工作是技師,她妹妹呢,牙醫系所出身,沒找到工作。總之,安吉拉在這裡安身立命了。
燙髮工程告終,安吉拉向著珍妮彎身:「有需要別客氣。我去幫你拿乾毛巾。」
如何成為美髮師
安吉拉的父親曾坐擁三棟房子。一家人住喀布爾,有一個園丁,和兩個僕人負責打掃及洗衣。她伯伯在自家屋外遭槍殺,事情發生後,他們就來到這裡。
還記得那時翻山越嶺進入阿富汗,天氣炎熱,艷陽高照,我們在岩石間前行,約莫是上午十點總算抵達山脊巔頭。俯瞰足下的蓊鬱草野,以及鄰近處山肩上的冰雪,群峰在眼前似無止盡地緜延,而一組人馬正朝我們靠近:一名傲然美麗的年輕女子和她家人攀上分界線,正離開阿富汗,其中一名男子領著一頭驢,驢背上承載所有家產。達達聲聽來很疲憊。那組人馬攀爬上我們佇立的位置,靜默擦身而過,然後下山進入巴基斯坦成為難民。
他們得走過堆壘的粉筆色鵝卵石,從懸崖邊側爬下,穿越林間,跋涉無數溪流,直到抵達巴勒吉納爾。賣掉驢子,搭公車或計程車穿越沙漠,繼續前往白沙瓦登記申請簽證,住進一間人滿為患、一晚要價二十盧比的飯店(以當時匯率來看,花我兩元,等於花他們兩百元),然後靜候佳音。美國簽證的等候期通常是兩年,幾週內就會散盡家財,若不試著在巴基斯坦或印度找工作,只能去難民營。在難民營,天氣熱起來小孩會流鼻血、發高燒,也因為擁擠不堪,加上伊斯蘭對端莊禮俗的沿襲成性,女性不分年紀總是入夜才能釋然外出。她用來洗便盆的運河水,難民也飲用,並且在公廁裡流動。(「阿富汗諺語說,」有人告訴我,「凡經三次流轉,水便潔淨。」)她會像某個身穿棕色與紅色的女子,在白得尖銳的石岸上坐著,看河水與她衣服同樣的顏色;家人的衣服洗妥了擱在一旁,扭扭身,為自己按摩後腦勺。她會像某個為《阿富汗幻燈秀》耐性擺姿勢的男人,蒼蠅停在嘴邊也不揮手趕走。她會像某個眼深處收納著歲月的微笑男孩。她會像某個脖子上掛著心形墜鏈的男人。安吉拉終歸是幸運的,她和家人飛往西方。
【第七章 規格正式的難民營】節選
規格正式的難民營
若我現在能對少年A說句話,要跟他說什麼?無可否認,現在的我確實感受到枯槁死氣,少年A擁有某種興奮,是現在的我所沒有。話又說回來,雖然人生滋味疲乏,我卻滿意於這種疲乏。我很成功,唯有在我偶爾閱讀他的文字時,會感覺到某種東西猶如柔軟的衣料般刷拭著我,接著是一股刺痛。我是否失去什麼?要是我現在就動身協助他人,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有效率,付出更多,索求更少。少年A曾經讓我丟臉,即便無知如他,現在的我對他或多或少還是有些景仰。我希望能更像他,但,當我還是他的時候,我遍體鱗傷。那聖賢之輩怎麼辦?阿爾伯特.史懷哲怎麼辦?那些人的存在證明了,是可以帶給他人啟發,也可以有所貢獻的。可是,他們自己受到啟發嗎?啟發是一種耽溺嗎?
令我厭倦的,主要是少年A的用功紀錄,他從不聽故事:他要如假包換的真實。那些真實如今看來多無意義。我手邊僅存的,是他那實事求是態度所無法消化的東西:碎瓦殘片,以及多彩多姿卻不值寸銀的小古玩。正如那名患有肺結核的老嫗,坐在自家旁邊堅硬的黏土地板上,放任他注視,火紅披肩在她的灰髮周圍彷彿燃燒,她的手指上套著一只銀戒指,臉龐幾乎爬滿不可思議的線條與皺紋,飽經歲月摧殘。他怎麼也無法率直看穿她的心,也猜不透她的思緒,或者任何屬於她的故事,只看見她回視凝望他。她的嘴唇帶著情緒皺起──是哪種情緒?那真的是情緒嗎?幾個男人佇立在後方,排成一列,他望著那名老嫗,他們對著他面露怒容。除了被我惹惱,甚至遭受我的多事折騰,她對我而言有什麼意義?她是我的什麼人?我對她無法忘懷,她卻已不在人世。然而,那隻在破舊筆記本中寫下這些紀錄的手,在眼前電腦鍵盤上飛舞的黝黑手指,令我目眩神迷:它踏上一個我不曾開始的旅行,見識過我不曾涉足的國度。
這雙手自然亦有可鄙之處。
善心人士想做好事,他想要療癒異國的不幸。因此,發現情況不如預想,失落感油然而生。對他那雙無知眼眸而言,要分辨難民和本地人的狀況,並非如往常容易:因為這兩者都不符合他的想像!(泰國的難民營倒確實設有鐵絲網,少年A在電視上看過。)
這些故事──沒錯,令人傷心欲絕的故事,他以為自己相信,實則不然,他做了好幾年惡夢。阿富汗人可自由進出難民營,營養不良的狀況很猖獗,飢餓無處不見。男性仍保有自己的武器,經常穿越邊境溜回去加入聖戰士之列。在他看來,難民營完全不像苦難的化糞池,反倒歡天喜地,充滿「民族色彩」,就像帕坦貨車司機精心改裝過的福特大型車,要是沒比任何一輛喀拉蚩公車更華麗,絕不善罷甘休,旗幟耀武揚威地朝下指,墨黑中見得到色彩繽紛的輪圈及藍金雙色的清真寺畫作,標題文字是盤繞白蛇或片片浪花般的普什圖語,全都排列在計程車頂部,由金黃波浪框出架構,太陽與塵埃讓鮮艷色彩蒙上一層白,褪成乳製點心的顏色,貨車則變成來自夢幻波斯的茶罐子,擋風板上的貨車彩帶一路向下垂墜,有對父子倚在引擎罩上,瞇著眼打量少年A。頭髮別上花卉圖案長布條的小女兒,以純真坦然的眼神,愣愣地凝望少年A,她一手抓喉嚨,另一手握飯鍋,地平線上除了塵土飛揚的山脊,什麼也看不見──難民營亦然。那裡有身著亮色圖案服裝的年輕女孩、為泥土屋增色不少的太陽花、人們超凡的力與美、艷陽與萬里無雲的青空。在這裡,我難得不願嚴厲批評少年A。假如聖喬治千里迢迢跨過厄運之山,卻發現無龍可屠又怎樣?當然他會很開心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不是嗎?
【序】節選
二〇〇〇年,踏入當時是塔利班政權的阿富汗前夕,我去探訪了早先招待過我的N將軍,他的名字將在《阿富汗幻燈秀》大量曝光。老人家如今是更加老了,腦袋不若往常靈活,我從一九八二年就收著的名片上那組電話號碼如今都多了兩碼。他歡天喜地迎接我,沒忘記我,我帶著愛與敬意握住他的手。
踏上參與戰事之路並寫下《阿富汗幻燈秀》,曾令我自以為是長篇冒險故事裡悲欣交纏的主角。事實上,真正的主角是N將軍。他供應我庇護所,讓我衣食無虞,把我裝束成帕坦人,安排我進出阿富汗的安全通道;更重要的,是他在我思想完全封閉之前進...
目錄
增訂新版序
序幕
摘自與布里茲涅夫的訪談
從白沙瓦望向正北方
第一部 邊境
第一章 上帝自有安排
他站在夜中央,直到眼睛適應黑暗,兩耳聽見耐性而恭敬的呼吸聲,以及衣袍摩擦的沙沙窸窣。航廈前的行人專用道,兩側均設有低矮圍籬,看上去彷彿運送已屠宰動物的履帶。圍籬被數百男子倚著,他們低聲喧嘩著:「施捨五分錢好嗎?」「先生搭車嗎?」祈盼垂憐。他從沒來過亞洲。接下來呢?
第二章 床罩國
「我還是不懂,為何要去阿富汗,」父親說,「大概永遠不會懂。」其實很簡單。我想了解那裡發生甚麼事,並親自幫助人。是出於善意。也已經準備就緒。
第三章 創造奇蹟何其難
這少年A在火傘高張之下,為一張前往白沙瓦的火車票,數個小時疲於張羅,有人開高價想坑他。嚎啕大哭的女乞丐比手畫腳說快餓死了,嚇壞他。面帶微笑的娼妓撫摸他的臉,因為他不讓身穿紅色軍官制服的男人幫提行李,他們便朝他怒罵。
第四章 旅長
棺木被抬著穿過泥牆圍繞的街道,旅長深鎖的眉頭放鬆,閱讀《可蘭經》時表情柔和。他邁步穿越人群,肩膀扛著棺木一角。喪禮前,他們在清真寺放下逝者,揭開他臉上的布塊,讓親戚親吻其頰。他年紀很大,蓄著一把白色長鬍,嘴巴張著,頭顱猶如捷泳選手扭向一側。
第二部 難民
第五章 「至少可在此久留」:當地的難民
當你走在世上最大樁難民案件之中,大家全淚眼婆娑求你幫忙,你到底能怎麼做?起先,你會在白沙瓦遇見一個,然後你遇見一家子難民,接著是難民營裡滿坑滿谷的人。
第六章 幸運者:在加州的難民
他們得走過堆壘的粉筆色鵝卵石,從懸崖邊側爬下,穿越林間,跋涉無數溪流,直到抵達巴勒吉納爾。賣掉驢子,搭公車或計程車穿越沙漠,繼續前往白沙瓦登記申請簽證,住進一間人滿為患、一晚要價二十盧比的飯店,然後靜候佳音。
第七章 「規格正式的難民營」:女人
「我想,得花一點時間才能讓阿富汗男人明白,女人也是人。」他遙望焦土矮牆外的井邊,有幾個女子,一棵枝葉扶疏的樹為她們遮蔽日光。她們往汽油錫桶和牛奶壺裡打水,身上的洋裝帶是著橘花的湛藍,或以黃色盛開花朵綴飾的嬌紅。
第八章 「規格正式的難民營」:貪腐
少年A、B和計程車司機下車,在高溫中伸展筋骨,環顧乾枯週遭與褪色的帳篷帆布,以及地上曾裝有食用油的閃亮空罐(另一項歐洲經濟共合體的贈禮),這時難民清出一條路。所有人駐足觀看,默不作聲瞪著少年A。
第九章 猶記阿拉斯加
我們身處之地,美得咋舌驚人,我身後的日光與河川聲響,以及眼前未知的無垠遼闊,令我驚嘆不已。這一切都使我感嘆連連。現在想,若說我前去阿富汗的目的是正面的,那肯定就是學習怎麼助人渡河——如我所說,我沒有幫上他們,是他們幫了我。
第三部 反叛者
第十章 政治啊政治:賽事
也許這說明了,為何跟我交談的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幾乎都相信,我是無所不能的中情局操縱高手。幾乎每一個阿富汗人或巴基斯坦人都認為自己受到控管。在白沙瓦,他們反覆說蘇聯已完成祕密交易,可以繼續掌控阿富汗,而美國人將接手中東。
第十一章 政治啊政治:友善為敵
當然,阿富汗人現在很團結。少年A知道他們肯定很團結,他不斷在報紙上讀到,他們甚至組成一個共同組織,叫作阿富汗聖戰士伊斯蘭聯盟。好啦,其實非也,有兩個敵對組織明明恨對方入骨,好死不死又都是這個名字。
第十二章 紅色山丘
一名聖戰士拿到焦黑的火箭炸彈殘骸後,高舉過頭面對少年A,他的眼睛閃著熱烈光芒,像是在說:這就是你此行的目的!現在看啊,快看!你來這裡的工作就是看!看看這個,瞭解情況,永遠不要忘懷!
第十三章 太陽照常升起
要是我買一瓶蘇打飲料請所有人會如何?——畢竟這是我唯一能為他們做的事——但他卻為了無私的理由而有所保留,例如在阿富汗時,聖戰士坐在樹下,想要用他的錄音機播放印度搖滾樂的卡帶,卻遭到拒絕。理由是,他要保留電池用在記錄訪談,這是唯一能在來日幫助他們的方法。
第十四章 後話
「基於這一點,我希望給您機會閱讀評論我這本書的手稿。任何建議或對事實陳述的錯誤指正,我都心懷感激收下。」
附錄
年表
致謝辭
增訂新版序
序幕
摘自與布里茲涅夫的訪談
從白沙瓦望向正北方
第一部 邊境
第一章 上帝自有安排
他站在夜中央,直到眼睛適應黑暗,兩耳聽見耐性而恭敬的呼吸聲,以及衣袍摩擦的沙沙窸窣。航廈前的行人專用道,兩側均設有低矮圍籬,看上去彷彿運送已屠宰動物的履帶。圍籬被數百男子倚著,他們低聲喧嘩著:「施捨五分錢好嗎?」「先生搭車嗎?」祈盼垂憐。他從沒來過亞洲。接下來呢?
第二章 床罩國
「我還是不懂,為何要去阿富汗,」父親說,「大概永遠不會懂。」其實很簡單。我想了解那裡發生甚麼事,並親自幫助人。是出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