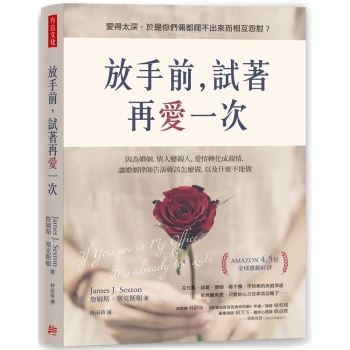四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
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受虐童年,
因為愛,而徹底改變的人生連結……
美國人最喜歡的「都會浪漫小說天后」諾拉.羅伯特
切薩皮克灣最令人期待的昆恩家四兄弟隆重登場!
‧AMAZON書店讀者4.5顆星熱感推薦!
人的運勢有起有落,而此刻坎默隆的運氣正旺。
他開著水翼船贏得世界冠軍,拿到榮耀和滿滿荷包,
香檳、一路長紅的賭局,加上沒有羈絆的放縱性愛。
直到一張傳真信函毀了這一切,
令他握過幾十艘船、飛機、賽車方向盤的手開始顫抖。
他最敬愛的養父雷蒙因為嚴重車禍瀕臨死亡,
還留下一個不明身分的十歲男孩賽斯有待收養……
因此,坎默隆遇上了他這輩子最詭異的一個星期。
此刻他應該飛到義大利參加機車越野障礙賽。
結果他卻困在海岸老屋和兄弟伊森、飛力浦唇槍舌戰,
爭奪不用照顧沒禮貌十歲小孩的卑微機會。
一般而言,小屁孩的腳步聲只會搞砸性生活,
沒想到卻為坎默隆帶來了長腿大美女社工安娜,
以及對他監護人資格的種種質疑:
單身男人、沒有穩定工作、沒有長期住處、沒有家務經驗。
瘦弱叛逆的賽斯,讓坎默隆不斷想起自己同樣受虐的童年,
而不裝腔作勢、不做承諾的安娜,讓他熱火焚身、野蠻激烈。
而把他救出罪惡泥淖的養父雷蒙,卻留下一堆讓他頭痛的謎團:
師生戀性醜聞、婚外情、私生子、自殺、詐騙保險賠償金?
見鬼的,他該拿這一切怎麼辦!
而當一切塵埃落定,他還能夠重拾原本的生活嗎?
作者簡介:
諾拉‧羅伯特 Nora Roberts
1981年開始創作,至今超過30年,已出版逾200本書。從1991年開始,她的每本小說都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沒有一本例外,盤踞超過1000週,其中53本更空降Top1,至今有超過165本《紐約時報》暢銷書,更是第三位亞馬遜電子書銷售達100萬冊以上的作者。
她的書在全球35個國家發行,印刷量超過4億冊,光是美國就佔了2億冊。曾有多本小說被改拍成電視電影。
2007年,她被《時代》雜誌選為百大影響人物之一,說她「檢視、剖析、拆解、探究、解釋並讚揚人類內心的熱情」,重量級雜誌《紐約客》更說她是「美國人最喜愛的小說家」。
她曾贏得多種寫作與出版獎項,為美國羅曼史小說作家協會(Romance Writers of America, RWA)的創始會員,更是獲頒「美國羅曼史作家名人堂」的第一人。她也用筆名「J.D.羅伯」寫科幻懸疑小說。
譯者簡介:
唐亞東
又名梨陌,羅曼史作者、譯者及研究者。政治大學英美文學碩士,正職從事文創行銷與智慧財產領域工作。著作有《拾戀》、《透明奇蹟》、《落月滿屋》等小說,譯作有瑰絲莉‧寇爾《迷夜烈愛》、《嗜血危情》、《冷月魔戀》、羅莉塔.雀斯辛家兄弟系列、伊洛娜‧安德魯斯魔法傭兵系列等作品。
臉書專頁:www.facebook.com/peartrail
陌路歸人部落格:www.peartrail.idv.tw
章節試閱
序曲
坎默隆.昆恩沒真的醉。如果他想要,大可直接喝到不省人事,不過此刻他覺得這種將醉未醉的微醺還不錯。他喜歡認為這樣的千鈞一髮正是他能一直走運的原因。 他完全相信人的運勢有起有落,而此刻他的運氣正旺。不到一天前,他才開著他的水翼船贏得世界冠軍,以一個船頭的距離險勝對手,同時打破了時間和速度的紀錄。 他拿到了榮耀,和滿滿的荷包,然後帶著兩者到蒙地卡羅,看看他的好運能維持多久。 他的運氣旺得不得了。 幾手百家樂、擲幾次骰子,加上一局紙牌,他的皮包變得更飽滿了。就算在狗仔隊和《運動畫刊》的記者間,他的光環也毫無黯淡的跡象。 命運之神繼續微笑——不,是大拋媚眼,坎默隆想——帶他在時尚雜誌拍攝泳裝特輯的同時來到這處地中海的勝地。 而上帝創造的那群長腿尤物之最將那雙宛如夏日晴空的藍眸轉向了他,噘翹的豐唇彎起,邀請的微笑就連瞎子也看得懂,知道應該多留幾天。 而她表示得非常清楚:他不必多費吹灰之力,就能更加走運。 香檳、一路長紅的賭局、沒有羈絆的放縱性愛。真的,坎默隆沉思,幸運女神非常眷顧他。 當他們從賭場踏入宜人的三月夜色,無所不在的某個狗仔隊跳了出來,拚命按快門。那女人噘起嘴——畢竟,那是她的招牌表情——不過還是熟練地甩了甩那頭長得不可思議的白金色直髮,致命的曼妙身材擺出專業的姿勢,薄得簡直像人體彩繪的罪惡紅禮服足以令人在踏進天堂之門前心旌動搖。 坎默隆只是咧嘴一笑。 「那些人真討厭,」她說話時口齒有點不清,或該說是帶有法國腔,坎默隆永遠分不清這其中的差異。她嘆氣,測試那身單薄絲綢的強韌度,任由坎默隆引她沿月光輕灑的街道走下去。「我到哪裡都會看見鎂光燈,我厭倦了老是被當成男人的玩物。」 喔,是啊,說得跟真的一樣,他想,覺得他們兩個和旱災後的枯溪一樣膚淺,於是他大笑,將她拉入懷中。「我們何不給他一些可以放在頭條的題材,蜜糖?」 他低頭吻上她的唇。她的滋味刺激他的荷爾蒙、撩起他的幻想,讓他慶幸飯店距離這裡只有兩個街區。 她的手指往上滑過他的頭髮。她喜歡頭髮多的男人,而他的頭髮又濃又密,黑得有如圍繞他們的夜色。他的身體堅實,充滿了強韌的肌肉和訓練有素的瘦削線條。她對候選情人的身體非常挑剔,而他遠遠超越她嚴苛的標準。 他的手比她偏好的更粗一點,不是力道或動作的粗魯——那恰到好處——而是觸感粗糙。那是雙工人的手,但她很樂意為了它們擁有的技巧,忽略欠缺的格調。 他的臉很迷人。不漂亮,她絕對不會和一個比她漂亮的男人站在一起,更別說一起入鏡。他的臉上有一份狠勁,那份強硬不僅止於緊貼在鮮明輪廓上的深褐肌膚,還包括那雙眼睛透出的神色,她想,一邊輕笑著掙脫。那雙眼睛是灰色的,有如燧石的灰,而不是煙霧,而且藏著秘密。 她喜歡有秘密的男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人能隱瞞她太久。 「你是個壞男孩,坎默隆。」她最後一個字帶著口音,伸出一根手指輕點他的唇,那雙嘴唇毫無柔軟可言。 「大家都這樣說——」他搜索了半晌記憶,回想她的名字。「瑪婷。」 「或許,今晚,我會讓你使壞。」 「我非常期待,甜心,」他轉身走向飯店,轉頭一瞥,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她幾乎可以和他平視。「去我的房間或妳的?」 「你的,」她軟語輕喃:「如果你再點一瓶香檳,或許我會讓你引誘我。」 坎默隆彎起一道眉,向櫃台拿鑰匙。「我需要一瓶水晶香檳、兩個杯子和一朵紅玫瑰,」他吩咐櫃台人員時,視線始終不曾離開瑪婷。「馬上。」 「好的,昆恩先生,我會處理。」 「一朵玫瑰,」兩人走向電梯時,她機動地對他說:「真浪漫!」 「噢,妳也想要一朵嗎?」她不解的微笑警告他幽默不是她的強項,所以調笑和談話就免了,他決定,直接切入重點。 電梯的門一關上,他便將她拉靠到身上,嘴唇貼上那雙不悅的唇。他很飢渴,這陣子一直很忙,忙著他的船、忙著準備比賽,沒時間消遣娛樂。他想要柔軟的肌膚、芬芳的肌膚、曲線、豐滿的曲線,一個女人,任何女人,只要她心甘情願、有經驗,而且明白分寸。 所以瑪婷是完美的人選。 她發出不完全是為了討好他的呻吟,接著將喉嚨拱向他咬嚙的牙齒。「你的動作好快。」 他的手沿著絲綢往下滑,又往上。「那就是我的謀生之道:加快速度,任何時候、任何方式。」 他抱著她不放,繞出電梯,沿著走廊走向房間。她的心跳劇烈地抵著他跳動,屏住呼吸,而她的手……喔,他認為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如此誘人。 他打開門鎖推開,將瑪婷壓在門板關上門,推開她肩膀上只有兩根線那麼寬的肩帶,注視著她,手自動滑向那雙雄偉的乳房。 他認為應該頒一枚獎章給她的整型醫生。 「妳想慢一點?」 沒錯,他的手觸感粗糙,但老天,卻令人興奮。她抬高一條長得嚇人的腿,勾住他的腰。他不得不讚嘆她絕佳的平衡感。「我現在就要。」 「很好。我也一樣。」他沿著那條幾乎算不上裙子的衣料下方往上探,撕掉底下輕薄的蕾絲。她的眼睛睜大,呼吸急促。 「動物。野獸。」而她咬住他的喉嚨。 正當他伸手探向拉鍊時,她頭後方的門傳來謹慎的敲擊。他腦袋裡每一公克的血都已經流進了腰帶下方。「老天,這裡的服務不可能那麼有效率。把東西留在門外。」他命令道,準備在門板上佔有這位瑪婷尤物。 「昆恩先生,請見諒,剛剛傳來了一張給你的傳真,註明是緊急文件。」 「叫他走開,」瑪婷伸手像鉗子一樣緊緊扣住他。「叫他下地獄去,狠狠操我。」 「等等。我的意思是,」他繼續說,將她的手指扳開,讓他的視線恢復清明。「給我一分鐘。」他將她在門後調整一下姿勢,花了一秒鐘確認拉鍊是拉上的,然後打開門。 「很抱歉打擾——」 「沒關係,謝謝。」坎默隆伸手進口袋拿出一張鈔票,沒費事確認金額,然後拿給服務生,交換他手上的信封,沒理會服務生對高額小費的大驚小怪,當他的面將門關上。 瑪婷做了一次她招牌的甩頭動作。「你對一張無聊的傳真比對我還有興趣,對這個——」她熟練地拉下衣服,像蛻去舊皮的蛇一樣扭脫。 坎默隆認為無論她為那具身體付了多少錢,每一分錢都值回票價。「不,相信我,寶貝,不是這樣。這花不到一秒鐘。」他撕開信封,免得自己忍不住直接把它揉成一團,往背後一扔,直接撲上眼前那具動人女體。 然後他看了那則訊息,而他的世界、他的人生、他的心臟就此停頓。 「喔,老天,他媽的。」這一整個晚上暢飲下的酒精在他腦中歡欣地晃蕩、在胃中洶湧,讓他的膝蓋化成一灘水。他不得不靠在門板上,穩住身子,才能再看一次。 坎默,媽的,你為什麼沒回電?我們已經打了好幾個小時電話找你。爸在醫院裡,情況很糟,糟到不能再糟了。沒時間說細節,我們就快失去他了,快回來。 菲力浦 坎默隆舉起一隻手——那隻握過幾十艘船、飛機、賽車方向盤的手,那雙可以令女人輕顫著瞥見天堂的手,而那隻手此刻顫抖著扒過頭髮。 「我得回家。」 「你已經在家了。」瑪婷決定再給他一次機會,上前用身體磨蹭他。 「不,我得出發。」他推開她,走向電話。「妳必須離開。我打打幾通電話。」 「你以為你可以叫我走?」 「抱歉,改天吧,」他的大腦無法運作。他不假思索地伸一隻手從口袋掏出鈔票,另一隻手拿起電話。「計程車費給妳。」他說,忘了她也住在同一間飯店。 「你這隻豬!」她全身赤裸,憤怒地撲到他身上。如果在正常狀態下,他早就閃過了攻擊,但巴掌甩上了他的臉,拳腳交加。他的耳朵嗡嗡作響,臉頰刺痛,耐性繃斷。 坎默隆直接伸手箍住她,發現她以為那是前戲時感到一陣厭惡,將她帶到門口,先撈起她的衣服,接著將女人和衣服一起扔進走廊。 他拉上門鎖時,她的尖叫讓他的牙齒在腦袋裡搖晃。「我會宰了你,你這隻豬!雜種!我會為此殺了你。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你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是!」 他不理會死命尖叫搥門的瑪婷,走進臥室,將一些必需品丟進袋子。 看來運氣剛剛耍了一手最惡劣的大翻盤。
1
坎默隆討人情、動用關係、請人幫忙、朝十幾個地方砸錢,在凌晨一點要搞定從蒙地卡羅到馬里蘭州東岸的交通並不容易。 他開車前往尼斯,沿海濱公路一路狂飆到一座小機場,有個朋友答應載他飛到巴黎——以一千美金的微薄代價。他在巴黎租了一架飛機,租金同樣是行情的一半,在橫渡大西洋的一路上不斷與疲憊和折磨人的恐懼糾纏。 他在東岸標準時間六點稍後抵達了華盛頓杜勒斯機場,預約的車已經在待命,所以他在黎明前黑暗的寒風中開車前往切薩皮克灣。 來到橫跨海灣的長橋時,燦爛朝陽已經升起,在海面上閃耀,映亮已經出海撈捕當日漁獲的船隻。坎默大半的人生都在世界這一角的海灣、河流和港口中航行,他此刻奔往探視的男人教導他的不只是港口和右舷。他所擁有的一切,任何能夠引以自豪的成就,都是雷.昆恩給他的。 當雷和史黛拉將他從社會福利系統拉出來時,他才十三歲,正一頭闖向地獄,累累的少年犯前科足以充當職業罪犯根源的個案研究。 搶劫、破門私闖、未成年飲酒、逃家、毆打他人、破壞公物、惡意搗亂,他一直為所欲為,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時常享受逍遙法外的好運,不過他這一生最幸運的一刻,卻是被逮到的那次。 十三歲,瘦得跟欄杆一樣,身上還留著他父親最近一次留下的瘀傷——家裡的啤酒喝光了,你說一個父親還能怎麼辦? 那個炎熱的夏夜,他臉上的血還沒乾,坎默向自己發誓他絕對不再回到那輛破拖吊車裡、那種生活、社福系統不斷把他扔回去的那個男人身邊。他要到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好,加州也好,墨西哥也好。 儘管拜黑眼圈所賜,他的視線一片模糊,他的夢想始終宏大。他身上有五十六元和一些零錢,揹在背上的衣服,加上爛透了的禮貌。他決定自己需要交通工具。 他溜上一輛從巴爾的摩出發的火車貨艙。他不知道火車開到哪裡也不在乎,只要能離開這裡。他在黑暗裡縮成一團,每一次震動都讓他的身體哀鳴,他對自己發誓就算要殺人或去死,也不要回來這裡。 當他鑽出火車,聞到了水和魚的氣味,懊惱自己剛剛沒想到要弄點食物,他的胃空到咕嚕作響。他頭昏腦脹又不知道方向,開始往前走。 這是個小地方。荒涼小鎮街上的商店入夜都已經打烊,船隻撞擊凹陷的甲板。如果他的腦袋清楚,或許會想到偷偷闖進海岸線那一排商店的某一間,但一直到走出鎮外,他發現自己正繞著沼澤前進時才想到。 沼澤的陰影和聲響令他毛骨悚然,陽光開始從東方天際透出,將泥濘的沼地和高大潮濕的野草映成金色。一隻大白鳥起身,令坎默的心猛跳一下,他以前從沒見過蒼鷺,覺得那就像是從書裡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像真的。 但那隻鳥雙翅一振,高高飛起。因為說不出的理由,他沿著沼澤邊緣跟牠走,直到牠消失在茂密的樹林裡。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又該往哪個方向去,但直覺告訴他繼續沿著狹窄的鄉間小路走,這樣只要有警車經過,他就能輕易躲進茂密的草叢裡或樹後面。 他非常想找個有陰影的第方,可以縮起來睡覺,忘記飢餓的痛苦和黏膩的暈眩感。然後陽光更炙,空氣因熱度變得沉重,他的上衣黏到背上,兩腳開始哀嚎。 他先看到車子,一輛閃亮的白色雪佛蘭,馬力強勁,造型優雅,在迷濛的晨曦中看起來有如一座大獎。旁邊有一輛小卡車,生鏽破舊,在那輛氣勢不凡的高級車旁看起來俗氣得可笑。 坎默在盛放的繡球花叢後面蹲下,仔細打量那輛車,垂涎三尺。 這輛他媽的帥車可以帶他到墨西哥,沒錯,還有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操,照這台機器的速度,在任何人發現它不見以前,他就已經在半路上了。 他改變姿勢,用力眨眼,釐清模糊的視線,盯著房屋看,其他人整潔的居住環境總是令他訝異。有彩色百葉窗的整齊房舍、庭院裡花朵盛開,灌木經過修剪,前廊放著搖椅,窗戶有紗窗。他覺得這棟房子好大,像一座有著淡藍邊框的現代白色宮殿。 他們很有錢,他決定,厭惡和飢餓鑽磨胃壁。他們住得起漂亮的房子、開高級的車、過舒服的生活,而一部分的他,由那個靠憎恨和百威啤酒維生的男人養育的那一部分渴望破壞,剷平所有的樹叢、打破每扇閃亮的窗戶,將那些上過漆的漂亮木板拆成碎片。 他莫名地想傷害他們,因為他們擁有一切,他卻一無所有,但當他站起身,苦澀的狂怒晃漾成噁心的暈眩。他壓下那股感覺,緊咬牙關,直到牙齒也跟著作痛,但思緒恢復了清明。 那些有錢的混蛋繼續睡吧,他想。他會幫他們解決這輛酷車。連車門都沒鎖,他發現到,對他們的無知嗤之以鼻,一邊拉開門。他父親教會他的一個比較有用的技能是如何迅速安靜地用電線發動車子,對一個收入主要來自偷車賣給銷贓商的男人來說,這樣的技能非常有用。 坎默探進車裡,鑽到方向盤下,開始動工。 「光明正大跑到別人的車道上偷車,這膽量可不小。」 坎默還來不及反應,連咒罵都還沒出口,一隻手已經勾住他的牛仔褲後緣,一把將他撈出來。他揮拳,結果揮出的拳頭彷彿撞上了石頭。 他第一次看見了巨人昆恩。那個男人很高大,至少有兩百公分高,壯得像巴爾的摩小馬隊的美式足球防守線一樣。他的臉寬大而飽經風霜,豐厚的金髮末端閃爍銀光,銳利的藍眼充滿盛怒。 然後那雙眼睛瞇了起來。 逮住這個男孩不費吹灰之力。如果這小子是他從海上釣到的魚,不可能超過四十五公斤,昆恩想。他髒兮兮的臉被打得很慘,一隻眼睛腫到幾乎張不開,另一隻深藍灰的眼睛透出不該在任何小孩眼中看到的苦澀,不顧一切冷笑的嘴角留著乾涸的血跡。 憐憫和憤怒在他的心中翻騰,但他緊緊抓住他,很清楚這個兔崽子一定會逃。 「看來你找錯了對象打架,小子。」 「你他媽的不要碰我,我什麼都沒幹。」 雷只是抬起一道眉。「你在星期六早上七點剛過,溜進我太太的新車裡。」 「我只是在看地上有沒有掉零錢,幹,那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得避免養成濫用『幹』當語助詞的習慣,否則會錯過這個字更多采多姿的用途。」 略帶說教的語氣完全超過坎默的理解能力。「聽著,傑克,我只是想找個幾毛錢硬幣,你根本不會發現。」 「不,不過如果讓你用電線發動車子,史黛拉會非常想念這輛車,而我的名字不叫傑克,是雷。好了,照我看來,你有幾個選擇,讓我們來條列,第一:我踹著你的大屁股進屋,打電話報警。你覺得在專門關壞蛋的少年感化院裡待個幾年如何?」 坎默臉上僅存的血色褪去,空蕩蕩的胃往下沉,掌心突然濡滿汗水。他無法忍受籠子,一定會死在牢裡。「我說過我沒要偷這輛該死的車,這是四檔變速,我他媽的怎麼可能會開一輛四檔變速車?」 「喔,我覺得你絕對沒問題。」雷鼓起臉頰,思考半晌,然後吁出氣。「再來,選項二——」 「雷!你在外面對那個孩子做什麼?」 雷看向門廊,一個有著火紅頭髮,穿著破爛藍裙的女人雙手扠腰站在那裡。 「只是討論一些生涯選擇的問題,他剛剛想偷妳的車。」 「喔,看在老天分上!」 「有人痛打過他一頓,我敢說是沒多久以前。」 「好吧,」史黛拉.昆恩的嘆息在露濕草坪的另一端都清晰可聞。「帶他進來,讓我看看。一早碰到這種事真是糟透了,真的很糟。不行,給我進屋去,笨狗,你真了不起,看著我的車被偷連叫也不叫一聲。」 「我太太史黛拉,」雷的微笑燦爛地擴大。「她剛剛給了你選項二,餓嗎?」 聲音在坎默的腦中嗡嗡作響。一隻狗在好幾哩外的遠處開心地高聲吠叫,鳥兒歡唱啁啾又貼得太近。他的皮膚燙得難受,然後又冷得要命,而他什麼都看不見。 「別動,小子,我會撐著你。」 他墜入濃濁的黑暗中,根本沒聽見雷的低聲詛咒。 他醒來時,躺在某個房間裡的熨平被單上,微風撥亂單薄的窗簾,送入花香和水氣。羞愧和慌亂湧上心頭,正當他打算起身,兩隻手將他壓躺回去。 「再乖乖躺一下。」 他看見那張瘦長的臉,俯視他的女人在他身上到處戳碰。那張臉上有上千個金色雀斑,不知怎地令他看得入迷,她有一雙深綠色的眼睛,眉頭皺緊,嘴唇緊抿成一條嚴肅的直線。她的頭髮往後梳,身上有淡淡的爽身粉味道。 坎默突然發現自己被脫到只剩下他那件破爛的內褲,羞愧和慌亂的情緒爆發。 「他媽的別碰我!」他發出的聲音充滿恐懼的嘶啞,激怒了自己。 「別緊張,放心,我是醫生。看著我,」史黛拉的臉逼近。「眼睛看著我,你叫什麼名字?」 他的心臟在胸口轟隆作響。「約翰。」 「我猜你還姓史密斯。」她挖苦地說:「好吧,如果你有辦法說謊了,狀況不會差到哪裡去。」她用手電筒照他的眼睛,嘟囔:「我敢說你有點輕微的腦震盪,你挨揍之後暈倒過幾次?」 「剛剛是第一次,」他覺得自己在她瞬也不瞬的盯視下開始臉紅,努力不要蠕動身體。「我猜啦,我不確定。我得走了。」 「對,的確,到醫院去。」 「不。」恐懼給了他力量在她起身前抓住她的手。如果他到了醫院,就會有人問問題,問題會引來警察,警察會引來社工,然後莫名其妙地,在整件事結束之前,他又會回到那個充滿污穢啤酒和尿液氣味的拖車,回到那個以揍身高不到他一半的小孩當最大消遣的男人身邊。 「我哪間醫院都不去,絕對不去。只要把我的衣服還我,我有一點錢,我會補償對你們造成的麻煩。我必須走。」 她再次嘆氣。「把名字告訴我,真正的名字。」 「坎默,坎默隆。」 「坎默,是誰對你做這種事?」 「我沒有——」 「別對我說謊。」她厲聲說。 而他辦不到。他的恐懼太過強烈,頭痛欲裂到差點忍不住嗚咽。「我爸。」 「為什麼?」 「因為他高興。」 史黛拉伸手指按按眼睛,接著放下手,看向窗外。她可以看見夏日般湛藍的海水、枝葉茂密的樹木和無雲的美麗蒼穹。在如此美好的世界裡,她想,卻有父母毆打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高興,因為他們可以,因為孩子就在旁邊。 「好吧,我們一步一步來。你一直頭暈,看不清楚。」 坎默謹慎地點頭。「可能有一點,但我有一陣子沒吃東西了。」 「雷正在樓下處理那個問題,讓他下廚比讓我好。你的肋骨附近有瘀血,但沒斷,眼睛是最糟的,」她喃喃說,手指輕柔地碰觸腫起的部位。「我們可以在這裡處理,把你清理乾淨,做點治療,看看狀況如何。我是醫生,」她又對他說一次,一邊微笑,一邊用觸感清涼的手將頭髮往後撥。「小兒科醫生。」 「那是看小孩的醫生。」 「你還是符合資格,狠角色。如果我不喜歡你的狀況,你就要去照X光。」她從袋子裡拿出消毒藥水。「這會有一點痛。」 當她開始為他的臉消毒時,他臉一皺,倒抽口氣。「妳為什麼要這麼做?」 她忍不住,伸手撥開他髒兮兮的濃密黑髮。「因為我高興。」
序曲
坎默隆.昆恩沒真的醉。如果他想要,大可直接喝到不省人事,不過此刻他覺得這種將醉未醉的微醺還不錯。他喜歡認為這樣的千鈞一髮正是他能一直走運的原因。 他完全相信人的運勢有起有落,而此刻他的運氣正旺。不到一天前,他才開著他的水翼船贏得世界冠軍,以一個船頭的距離險勝對手,同時打破了時間和速度的紀錄。 他拿到了榮耀,和滿滿的荷包,然後帶著兩者到蒙地卡羅,看看他的好運能維持多久。 他的運氣旺得不得了。 幾手百家樂、擲幾次骰子,加上一局紙牌,他的皮包變得更飽滿了。就算在狗仔隊和《運動畫刊》的記者間,他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