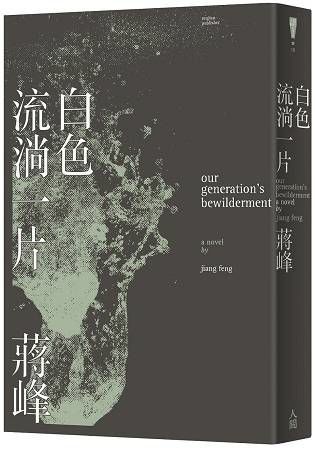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消失
谷立立(自由撰稿人)
我相信,蔣峰是理想至上的。當他的同齡人在用力描繪白富美、高富帥們不食人間煙火的夢幻戀情時,他正一筆一畫地描繪著另一種人生。和前作一樣,新作《白色流淌一片》(以下簡稱《白色》)很懸疑,也很悲情,甚至不乏草根;他寫理想,也寫現實,有時無限接近於生活,有時又似乎隔了一層紗。或者不妨說,往前一步是現實,往後一步是理想,可《白色》偏偏卡在了當中。
關於戲劇寫作,契訶夫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如果第一幕牆上掛著一把槍,那在第三幕時就一定要讓槍打響。」蔣峰酷愛「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寫作,也精於此道。《白色》是一部典型的蔣峰式懸疑小說。一開篇,他就布下一個局。小說首章〈遺腹子〉以交叉敘事講述了兩個遺腹子出生前的家庭紀事。這是男主角許佳明的首度亮相,只是還未及現身,蔣峰就殘忍地宣告了他的死訊。至於事件的前因後果卻隻字未提。在其後的諸章,蔣峰延續著同樣的神祕。他帶著我們沿著許佳明的人生軌跡兜兜轉轉地走了一圈:〈遺腹子〉寫出生;〈花園酒店〉是童年。〈六十號信箱〉和〈手語者〉兩章並行,記錄下學生時代或叛逆、或張揚的往事。
這就像是一次漫長而艱難的告別。自始至終,蔣峰不斷提醒我們去關注許佳明最後的結局。隨著人物逐一登場、場景逐漸鋪開,壓抑氣氛也在緩慢地醞釀著、上升著,情緒飽滿得似要溢出紙面,終於在最末一章〈和許佳明的六次星巴克〉裡盡數爆發而出。此時,故事又回到了起點,蔣峰採取旁觀角度、以友人的回憶抽絲剝繭細數許佳明的從藝歷程。敘述如慢鏡般緩緩推進,將其一生掃視了一遍,同時鐵板釘釘地將死訊落到了實處。如此,從死到生,再回到死,就像一次輪迴。一個人的一生也就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從本質上說,《白色》還是青春敘事,只是蔣峰的青春更帶著些現實的諷喻。小說標題所指的「白色」是一個人精神世界的高度濃縮,同時隱隱投映出其命運的走向。眾所周知,青春就像雪一樣純潔,有著最純粹的情感和揮霍不盡的激情。但青春又是脆弱的,易於被周遭世界所侵蝕、同化。一旦步入成人世界,見識了永遠不能端上台面的齷齪勾當,且與現實的髒汙交織纏繞,即便是雪花也不能獨善其身。這就好比天邊飄著的一朵雲襯著碧藍的天空,本來是一幅絕美的畫面,卻偏偏被風吹散,化成雪,紛紛揚揚落入人間。誰知剛一落地就遭人踐踏,轉眼之間變成深深淺淺的灰色。等到殘雪化去,原形畢露,大地還是單調一味的黑色,而許多醜事、惡事也在此時浮出了水面。
既然是青春敘事,當然少不了愛情。蔣峰慣於在環環相扣的懸疑故事裡加入愛情的元素,這無疑更凸現出凶手的殘暴和凶案的血腥。《白色》裡同樣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糾葛,只是在現實的語境下,這種感情明顯變了味。《白色》寫了一個人的成長,也寫了很多人的墮落。以主流的價值觀念來評判,蔣峰的世界裡活躍著的全都是非常規的人物。他們大都有破碎家庭的背景,身體或者心靈留有不同程度的殘缺,曾經有過夢想,也試圖以非常規的手段獲取世人眼中的成功:名校背景、談吐不凡,有讓人仰視的地位、有可供揮霍的財富。只是要成功,先要付出常人無法想像的代價,諸如青春、夢想、愛情,乃至於做人的尊嚴,都是必須的籌碼。
以許佳明的三段愛情為例。〈六十號信箱〉和〈手語者〉兩章分別寫了兩種學生時代的戀情:高中時暗戀「學霸」房芳、大學時與藝術系女生譚欣交往。到了〈我私人的林寶兒〉一章,故事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此時許佳明已經成年,是一位尚未成名的畫家,與三流演員林寶兒有了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房芳、譚欣、林寶兒三個人性格不同、經歷迥異,唯一的共同之處在於她們都是拜金女,在生命的某一階段都曾止步於現實的泥沼。為了擺脫困境、攀上高枝,過上令人豔羨的幸福生活,許佳明的女神們各顯神通,最後也都無一例外地投入了老男人的懷抱:自視甚高的房芳攀附上教委的高官;尊崇藝術的譚欣為「藝術」而「藝術」地和大師上了床;林寶兒美其名曰「私人」,其實早就是幾個男人的公共情婦了……
其時,白花花的銀兩像鏡子一般映出她們貪婪的本性。一旦被財富、權勢俘虜,所謂的理想也便跟著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諷刺的是,當初極具理想意味的「白色」從高天上的流雲,一路降級為一勺廉價的奶精、一張實用的面膜,甚至是淌了一床的精液(不厚道地說,也可以是散落一地的銀子)。如此演變,是道德的淪喪、理想的嬗變,也是變革中國的一大悲哀。
出生於破碎家庭的許佳明,從小被教育著長大後要做一個高尚、正直、坦蕩蕩的人。他天真地以為等到有朝一日長大成人,一切都會變得很美好,他會擁有「特別幸福的一生」。但事實是,長大了才知道,光明是沒有的,幸福也談不上,「這個世界其實特別冷」。是的,世界不但很「冷」,而且還透著蝕骨的「寒」。事實上,蔣峰是悲觀的,他並不抱有盲目的樂觀,而是用全部心力為我們炮製了世界的冷酷與人情的涼薄。
《白色》記錄了一個人、一個家庭的三十年,這也是變革中國的三十年。在過去三十年間,世界日新月異、變化多端,且正在以誇張、扭曲的形式,加速旋轉著向下墜落。極富理想主義情懷的許佳明以自身的成長見證了當代中國近三十年諸多怪現象:要當一個畫家,首先要五毒俱全,要會賣乖,更要會拍馬;美協官員滿腦子貓膩,只知官場三字經,對有才之士大加排擠;要當優等生,成績好不好不要緊,會不會體察上意、能不能討好老師才是正經事;重點中學的辦學宗旨不是教書育人,而是更多更好地收取贊助;高級酒店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供富人嫖娼宿妓、包養小三……凡此種種,始作俑者恐怕還是一個「利」字。
與之相對應的是文藝的式微。在金錢至上的時代裡,文學、藝術遠遠沒有權勢、財富有用。這世界很勢利,奉行一條無往不利的硬道理:誰出錢,誰就是主子;誰出錢,就得按照誰的規則來玩。在大多數場合裡,才華一無是處,往往淪為創作者的恥辱。現實裡,蔣峰一再感受到這種恥辱,比如在某些舊書店裡,圖書被當作白菜蘿蔔一樣論斤賤賣。這些習焉不察的細枝末節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反映到寫作中,也就有了《白色》裡高度神似的一幕:許佳明的朋友李小天去他家探訪,進得門來,只見一屋子人圍著滿地的畫作,東挑西撿、討價還價。蔣峰借人物之口說出了他的厭惡,「我當時感覺不好,看他們這麼幹,好像快打烊的超市,一幫大媽圍著打折處理的青菜,五毛一斤還得掰掉菜幫子再上秤。」
因此,儘管蔣峰還是一如既往地寫著懸疑,但此懸疑不是彼懸疑,《白色》濃重的現實諷喻讓人讀出了另一番滋味。如果要給《白色》加一個副標題的話,莫過於〈論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消失〉了。在經歷過太多失敗之後,許佳明等來了理想隕滅的那一天。他因何喪命、又死於誰手,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當一個青年藝術家無聲無息地消失之後,他得到了什麼?回到《白色》裡,世界照舊一派繁忙:官員們忙著加官進爵,忙著出國考察,早將藝術的本義置於腦後;林寶兒哭過痛過之後,緊接著打掉了腹中胎兒,轉眼沒事人一樣尋找下一個男人……除了美協檔案裡的二十五個字生平介紹之外,許佳明的人生的確什麼也沒有留下。誰都不願意相信這是現實,但不得不承認,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即便如此,理想至上的蔣峰不相信文藝會死,不相信夢想的盡頭會是再也無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既非中庸,也不極端,他無意質疑體制,也不刻意粉飾什麼。我手寫我心,他不過是記住了他眼中的世界。骯髒的依舊骯髒,殘酷的還是殘酷。總有人為了利益將理想狠狠地踩在腳下,直到一地狼藉。也總有人願意相信夢想,相信在殘酷世界的另一邊有一個美麗城堡,城堡裡的水蜜桃公主正等著他去營救。即便為此做了白骨又何妨,就像《白色》裡的許佳明一樣。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白色流淌一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 356 |
現代小說 |
$ 383 |
小說/文學 |
$ 405 |
小說 |
$ 405 |
現代小說 |
$ 405 |
文學作品 |
$ 405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白色流淌一片
本書記錄了一個人、一個家庭的三十年,這也是變革中國的三十年。在過去三十年間,世界日新月異、變化多端,且正在以誇張、扭曲的形式,加速旋轉著向下墜落。極富理想主義情懷的許佳明以自身的成長見證了當代中國近三十年諸多怪現象。
從本質上說,《白色》還是青春敘事,只是蔣峰的青春更帶著些現實的諷喻。小說標題所指的「白色」是一個人精神世界的高度濃縮,同時隱隱投映出其命運的走向。
——谷立立(自由撰稿人)
作者簡介:
1983年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2002年獲得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由此開啟寫作之路,2004年出版長篇處女作《維以不永傷》,迄今為止出版的長篇小說為《一,二,滑向鐵軌的時光》、《去年冬天我們都在幹什麼》、《淡藍時光》、《戀愛寶典》、《為他準備的謀殺》、《白色流淌一片》。
TOP
章節試閱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消失
谷立立(自由撰稿人)
我相信,蔣峰是理想至上的。當他的同齡人在用力描繪白富美、高富帥們不食人間煙火的夢幻戀情時,他正一筆一畫地描繪著另一種人生。和前作一樣,新作《白色流淌一片》(以下簡稱《白色》)很懸疑,也很悲情,甚至不乏草根;他寫理想,也寫現實,有時無限接近於生活,有時又似乎隔了一層紗。或者不妨說,往前一步是現實,往後一步是理想,可《白色》偏偏卡在了當中。
關於戲劇寫作,契訶夫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如果第一幕牆上掛著一把槍,那在第三幕時就一定要讓槍打響。」蔣峰酷愛「草蛇灰線...
谷立立(自由撰稿人)
我相信,蔣峰是理想至上的。當他的同齡人在用力描繪白富美、高富帥們不食人間煙火的夢幻戀情時,他正一筆一畫地描繪著另一種人生。和前作一樣,新作《白色流淌一片》(以下簡稱《白色》)很懸疑,也很悲情,甚至不乏草根;他寫理想,也寫現實,有時無限接近於生活,有時又似乎隔了一層紗。或者不妨說,往前一步是現實,往後一步是理想,可《白色》偏偏卡在了當中。
關於戲劇寫作,契訶夫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如果第一幕牆上掛著一把槍,那在第三幕時就一定要讓槍打響。」蔣峰酷愛「草蛇灰線...
»看全部
TOP
目錄
【目錄】
序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消失——谷立立
第一章 遺腹子
第二章 花園酒店
第三章 六十號信箱
第四章 手語者
第五章 我私人的林寶兒
第六章 和許佳明的六次星巴克
後記 我為什麼還要寫作
附錄 蔣峰創作年表
序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消失——谷立立
第一章 遺腹子
第二章 花園酒店
第三章 六十號信箱
第四章 手語者
第五章 我私人的林寶兒
第六章 和許佳明的六次星巴克
後記 我為什麼還要寫作
附錄 蔣峰創作年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峰
- 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2-08 ISBN/ISSN:978986940461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96頁 開數:寬14.80cm × 長 21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