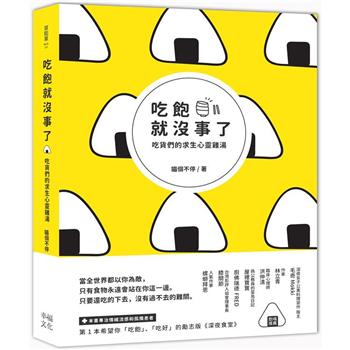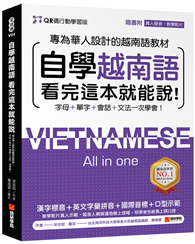本書特色
《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前後歷時兩年寫作而成,集約了近一段時期作者主要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他的批判對象由近代日語的歷史形成、戰後近代天皇制的免責式倖存,直至當代日本文學界最具國際品牌號召力的村上春樹,從這一條清晰的軌跡可以看出,他所選擇的無一不是意識形態領域內具有本質意義的關鍵性課題。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增訂版)的圖書 |
 |
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增訂版) 譯者:秦剛 出版社:人間 出版日期:2017-05-2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8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0 |
小說/文學 |
$ 180 |
日本文學 |
$ 180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增訂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小森陽一
1953年生於東京。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畢業,獲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學位。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日本及亞洲(或東亞)知識界廣受關注的學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重讀夏目漱石》、《「搖擺」的日本文學》、《小森陽一、與日語的遭遇》、《日本近代國語批判》、《歷史認識與小說--大江健三郎論》、《天皇的玉音放送》、《後殖民》、《種族歧視》、《心腦控制社會》等。
譯者簡介
秦剛
1968年生於長春。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碩士課程畢業。1999年獲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日本語言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編著《感受宮崎駿》,譯著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等。曾獲「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日本研究論文獎。
小森陽一
1953年生於東京。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畢業,獲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學位。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社會活動家,日本及亞洲(或東亞)知識界廣受關注的學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重讀夏目漱石》、《「搖擺」的日本文學》、《小森陽一、與日語的遭遇》、《日本近代國語批判》、《歷史認識與小說--大江健三郎論》、《天皇的玉音放送》、《後殖民》、《種族歧視》、《心腦控制社會》等。
譯者簡介
秦剛
1968年生於長春。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碩士課程畢業。1999年獲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日本語言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編著《感受宮崎駿》,譯著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等。曾獲「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日本研究論文獎。
目錄
簡短的推薦/呂正惠
譯者序——《海邊的卡夫卡》現象及其背後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海邊的卡夫卡》與俄狄浦斯神話
俄狄浦斯神話之主題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
《海邊的卡夫卡》與《俄狄浦斯王》的相似性
俄狄浦斯情結的三角形
四歲時被母親拋棄意味著什麼?
語言的掌握與「自我」的誕生
肛門期與「為什麼?」的疑問
卡夫卡少年「為什麼?」的質疑
卡夫卡少年的暴力衝動
母親難道不愛自己嗎?
排便教育與愛情的悖論
卡夫卡少年的禁忌觸犯應該得到寬恕嗎?
第二章 甲村圖書館與書籍的迷宮
圖書館的母性空間
為何首先閱讀《一千零一夜》?
山魯佐德故事的內涵
卡夫卡少年論述卡夫卡《在流放地》
《一千零一夜》與《在流放地》的接合
「行刑機器」的構造
《在流放地》的權力問題
《海邊的卡夫卡》是一部處刑小說?!
對佐伯和三本文稿的「處刑」
法與暴力
瓊尼.沃克的真面目
殺貓與殺人——二者擇一的偽命題
對於艾希曼的「想像力」意味著什麼?
第三章 卡夫卡少年為何閱讀夏目漱石
——甲村圖書館與書籍的迷宮Ⅱ
卡夫卡少年閱讀《礦工》與《虞美人草》
「近代教養小說」的視角
《礦工》與《海邊的卡夫卡》的關係
《礦工》的人性觀
追溯記憶的小說與消解記憶的小說
作為處刑小說的《虞美人草》
《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女性憎惡
與「生魂」的戀愛
一語不發的佐伯「生魂」
擬似俄狄浦斯神話的完結
卡夫卡少年強姦「姐姐」
拿破崙戰爭、前日軍士兵與「強姦」的鄰接
「戰爭」是「無奈之舉」嗎?
《礦工》對思維停滯是怎樣表述的
《礦工》與《海邊的卡夫卡》的差異
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第四章 中田與戰爭的記憶
中田的身世
記憶缺失與識字能力的喪失
導致中田記憶喪失的岡持老師的暴力
創傷與解離
「日本正在打一場大戰爭時候」時的記憶
丈夫的陣亡是否是岡持老師的「罪過」?
「打了中田君的那天」在《萊特戰記》是怎樣記述的?
中田的行刑和佐伯之「罪」
女性之「罪」的框架
「入口的石頭」和「三本文稿」
歷史否認與女性憎惡的結合
第五章 《海邊的卡夫卡》與戰後日本社會
卡內爾.山德士講述的「天皇《人間宣言》」的真偽
「生魂」與《菊花之約》的蘊涵
天皇的戰爭責任與弒父
田村浩一象徵了「團塊世代」
《海邊的卡夫卡》的逆向俄狄浦斯構造
「兩個士兵」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軍事演習與解離
「戰爭」.「強姦」.隨軍慰安婦
「作為擁有精神世界的人而呼吸的女性」的記憶
《地下鐵事件》與《海邊的卡夫卡》
卡夫卡少年十五歲的含義
「9.11」之後的文學想像力
【附錄】村上春樹為什麼迷人——兩封信/黃文倩、呂正惠
譯者序——《海邊的卡夫卡》現象及其背後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海邊的卡夫卡》與俄狄浦斯神話
俄狄浦斯神話之主題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
《海邊的卡夫卡》與《俄狄浦斯王》的相似性
俄狄浦斯情結的三角形
四歲時被母親拋棄意味著什麼?
語言的掌握與「自我」的誕生
肛門期與「為什麼?」的疑問
卡夫卡少年「為什麼?」的質疑
卡夫卡少年的暴力衝動
母親難道不愛自己嗎?
排便教育與愛情的悖論
卡夫卡少年的禁忌觸犯應該得到寬恕嗎?
第二章 甲村圖書館與書籍的迷宮
圖書館的母性空間
為何首先閱讀《一千零一夜》?
山魯佐德故事的內涵
卡夫卡少年論述卡夫卡《在流放地》
《一千零一夜》與《在流放地》的接合
「行刑機器」的構造
《在流放地》的權力問題
《海邊的卡夫卡》是一部處刑小說?!
對佐伯和三本文稿的「處刑」
法與暴力
瓊尼.沃克的真面目
殺貓與殺人——二者擇一的偽命題
對於艾希曼的「想像力」意味著什麼?
第三章 卡夫卡少年為何閱讀夏目漱石
——甲村圖書館與書籍的迷宮Ⅱ
卡夫卡少年閱讀《礦工》與《虞美人草》
「近代教養小說」的視角
《礦工》與《海邊的卡夫卡》的關係
《礦工》的人性觀
追溯記憶的小說與消解記憶的小說
作為處刑小說的《虞美人草》
《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女性憎惡
與「生魂」的戀愛
一語不發的佐伯「生魂」
擬似俄狄浦斯神話的完結
卡夫卡少年強姦「姐姐」
拿破崙戰爭、前日軍士兵與「強姦」的鄰接
「戰爭」是「無奈之舉」嗎?
《礦工》對思維停滯是怎樣表述的
《礦工》與《海邊的卡夫卡》的差異
夏目漱石與村上春樹
第四章 中田與戰爭的記憶
中田的身世
記憶缺失與識字能力的喪失
導致中田記憶喪失的岡持老師的暴力
創傷與解離
「日本正在打一場大戰爭時候」時的記憶
丈夫的陣亡是否是岡持老師的「罪過」?
「打了中田君的那天」在《萊特戰記》是怎樣記述的?
中田的行刑和佐伯之「罪」
女性之「罪」的框架
「入口的石頭」和「三本文稿」
歷史否認與女性憎惡的結合
第五章 《海邊的卡夫卡》與戰後日本社會
卡內爾.山德士講述的「天皇《人間宣言》」的真偽
「生魂」與《菊花之約》的蘊涵
天皇的戰爭責任與弒父
田村浩一象徵了「團塊世代」
《海邊的卡夫卡》的逆向俄狄浦斯構造
「兩個士兵」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軍事演習與解離
「戰爭」.「強姦」.隨軍慰安婦
「作為擁有精神世界的人而呼吸的女性」的記憶
《地下鐵事件》與《海邊的卡夫卡》
卡夫卡少年十五歲的含義
「9.11」之後的文學想像力
【附錄】村上春樹為什麼迷人——兩封信/黃文倩、呂正惠
序
推薦序
簡短的推薦
呂正惠
有一陣子常常聽到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我這個從來不看暢銷書的人竟然也問我兒子,「村上春樹哪一本書最有名?」我兒子說,「好像是《海邊的卡夫卡》」,於是我就買了大陸林少華的譯本,但一直擺在書架上,從來沒有翻過。
去年北京清華大學的王中忱教授來臺灣客座,在隨便亂聊中,他提到了日本的左翼評論家小森陽一教授,說他寫過一本《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我有一點意外,沒想到這本書會引起這麼著名的評論家的注意。不久我到北京,王教授介紹我認識本書的中譯者秦剛先生,承他送我一本。我抽出時間來看,原本想大致翻一下,沒想到欲罷不能,竟然一口氣讀完,一本文學評論的書籍具有這麼大的吸引力,真是太神奇了。
小森陽一教授告訴我們,日本右派的政治宣傳技術如何與商業媒體結合,運作出驚人的暢銷紀錄,並以此麻痺社會人心,讓他們在充滿問題與焦慮的情境下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下去。這種作法,我以前在台灣也不是沒有感覺到,但看到小森教授的精細分析,我才恍然了解,現在的政治操作原來可以如此的精密,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對於這樣嚴密設計的作品,要把它的每一點佈置一一拆解,讓它大白於天下,並讓許多人看得懂,這實在是非同小可的工作。這需要極大的耐性、豐厚的學識,還有極清晰的文筆。要是我,我才不願意浪費我的時間,去仔細梳理這樣一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書。然而,小森陽一卻為它花了兩年的工夫。他在中文版的序裡說:
然而,精神創傷決不能用消除記憶的方式去療治,而是必須對過去的事實與歷史全貎進行充分的語言化,並對這種語言化的記憶展開深入反思,明確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責任所在,並且令責任者承擔了責任之後,才能得到不會令同樣事態再次發生的確信。小說這一文藝形式在人類近代社會中,難道不正擔當了如此的職責麼?因此,我要對《海邊的卡夫卡》進行批判。
這一段話讓我深為感動。一個關懷人類前途的評論家,不只要推薦好書,還要指出蓄意欺騙的作者如何罔顧人類正義而玩弄讀者。小森陽一這麼義正詞嚴的強調小說的道德性,真如空谷足音,讓我低迴不已。在文學已經成為某一形式的遊戲與玩樂的時代,連我都不再敢於嚴肅的宣告文學的正面價值了。他的道德的誠摰性始終貫注在我的閱讀過程中,讓我不敢掉以輕心。
除了這種道德性之外,作為一個左翼評論家,小森陽一還有一個極大的優點。任何艱澀的知識和複雜的小說,在他筆下都可以成為井然有序、易於閱讀的文字,讓我們好像在享受獲得知識的欣喜。譬如在第一章裡他對佛洛伊德理論的分析,第二章裡他對伯頓譯本《一千零一夜》裡所蘊含的強烈東方主義色彩的揭露,第三章裡對夏目漱石小說《礦工》與《虞美人草》的解說,都非常吸引人。在第五章裡,他把《海邊的卡夫卡》和戰後日本社會聯繫起來,對一直企圖逃避戰爭責任的右派進行了強烈的抨擊,讓我這個對歷史不是毫無所知的人,都有突然憬悟之感。我第一次感覺到,小說評論是可以和知識傳達完美的結合在一起的。
關於《海邊的卡夫卡》的意識形態傾向,秦剛的譯者序和小森陽一的兩篇序都作了簡要的說明,這裡就不再重複。我想以小說中的一、兩個情節為例,以最簡明的方式呈顯小說想要把讀者引導到哪個方向和哪些心態上。
小說的主角田村卡夫卡,四歲時母親帶著姐姐(養女)離家出走,父親不理他,像個孤兒似的成長到十五歲,這時候他決定離家出走,獨立生活。他從小被父親詛咒,說他會「殺死父親,同母親和姐姐交合」,他一直身懷恐懼,但深心中卻又受到誘惑。離家後他到了高松市,找到了甲村圖書館,每天在那裡看書。圖書館的負責人佐伯雖然已年過五十,但仍然容貌美麗,身材苗條,身上還可以覓出十五歲少女的姿影。田村少年既把佐伯看成他的母親,又每天迷戀她的身影。終於有一天晚上,佐伯以沈睡狀態來到田村的房間(也是以前佐伯和她的情人幽會的地方)和他發生了關係。後來,在田村的懇求下,佐伯以清醒的意識又和他同床兩次。這樣,田村就擬似「同母親交合」了。
這件事發生後,佐伯就不再有生命意志,她在死前跟別人懺悔說:
不,坦率地說,我甚至認為自己所做的幾乎都是錯事。也曾和不少男人睡過,有時甚至結了婚。可是,一切都毫無意義,一切都稍縱即逝,什麼也沒留下,留下的唯有我所貶損的事物的幾處傷痕。
這樣,這一樁擬似「母子交合」的責任就由佐伯承擔下來(因為她貶損了事物,敗壞了世界),她必需死,她也就死了。而那個從頭到尾對佐伯充滿性幻想的、又一直把她假設是母親的田村少年卻一點責任也沒有。
另一個例子是田村少年和櫻花的關係。櫻花是田村在到達高松的旅途中認識的、比他年長的女孩子,像姐姐一樣的照顧他。田村也一直對她充滿了幻想,有一天在夢中強姦了櫻花。在小說結尾時,田村打電話跟櫻花告別,這個情景以這一句話結束:
「再見,」我說。「姐姐!」我加上一句。
最後加上去的「姐姐」這個稱呼就是有意要做實他「奸污」了姐姐。所以田村根本不只被詛咒要「同母親和姐姐交合」,他根本就是有意要犯這個錯。他認為,只有踐行這個詛咒,他才能從命定的重擔下解脫出來,獲得自我與自由。很難形容這是怎麼樣的邏輯。
這樣的田村卻被稱為是「現實世界上最頑強的十五歲少年」,並被勸告要「看畫」、「聽風的聲音」,就是順著感覺走。這樣就是活著的意義,不然,你會被「有比重的時間如多義的古夢壓在你身上」,怎麼逃也逃不掉。這是勸告人要這樣的成長:既然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重擔壓在你身上,你就只能左閃右躲,就只能聽著、看著、幻想著(特別是性),可以這樣悠遊自在,而你沒有任何責任,因為這些都是別人「詛咒」到你身上的。這樣的人生觀,只能令人浩嘆,怪不得小森陽一教授決定加以批判。
最後,感謝王中忱教授讓我接觸這本書,感謝本書的譯者秦剛先生,他為了臺灣的繁體字版又把譯文修訂了一次,同時他的譯文還修正了林少華的誤譯,漏譯之處。當然要感謝小森陽一教授,不論對大陸的簡體版,還是對臺灣的繁體版,他都無償的提供出版權。
簡短的推薦
呂正惠
有一陣子常常聽到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我這個從來不看暢銷書的人竟然也問我兒子,「村上春樹哪一本書最有名?」我兒子說,「好像是《海邊的卡夫卡》」,於是我就買了大陸林少華的譯本,但一直擺在書架上,從來沒有翻過。
去年北京清華大學的王中忱教授來臺灣客座,在隨便亂聊中,他提到了日本的左翼評論家小森陽一教授,說他寫過一本《村上春樹論──精讀海邊的卡夫卡》,我有一點意外,沒想到這本書會引起這麼著名的評論家的注意。不久我到北京,王教授介紹我認識本書的中譯者秦剛先生,承他送我一本。我抽出時間來看,原本想大致翻一下,沒想到欲罷不能,竟然一口氣讀完,一本文學評論的書籍具有這麼大的吸引力,真是太神奇了。
小森陽一教授告訴我們,日本右派的政治宣傳技術如何與商業媒體結合,運作出驚人的暢銷紀錄,並以此麻痺社會人心,讓他們在充滿問題與焦慮的情境下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下去。這種作法,我以前在台灣也不是沒有感覺到,但看到小森教授的精細分析,我才恍然了解,現在的政治操作原來可以如此的精密,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對於這樣嚴密設計的作品,要把它的每一點佈置一一拆解,讓它大白於天下,並讓許多人看得懂,這實在是非同小可的工作。這需要極大的耐性、豐厚的學識,還有極清晰的文筆。要是我,我才不願意浪費我的時間,去仔細梳理這樣一本沒有什麼價值的書。然而,小森陽一卻為它花了兩年的工夫。他在中文版的序裡說:
然而,精神創傷決不能用消除記憶的方式去療治,而是必須對過去的事實與歷史全貎進行充分的語言化,並對這種語言化的記憶展開深入反思,明確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責任所在,並且令責任者承擔了責任之後,才能得到不會令同樣事態再次發生的確信。小說這一文藝形式在人類近代社會中,難道不正擔當了如此的職責麼?因此,我要對《海邊的卡夫卡》進行批判。
這一段話讓我深為感動。一個關懷人類前途的評論家,不只要推薦好書,還要指出蓄意欺騙的作者如何罔顧人類正義而玩弄讀者。小森陽一這麼義正詞嚴的強調小說的道德性,真如空谷足音,讓我低迴不已。在文學已經成為某一形式的遊戲與玩樂的時代,連我都不再敢於嚴肅的宣告文學的正面價值了。他的道德的誠摰性始終貫注在我的閱讀過程中,讓我不敢掉以輕心。
除了這種道德性之外,作為一個左翼評論家,小森陽一還有一個極大的優點。任何艱澀的知識和複雜的小說,在他筆下都可以成為井然有序、易於閱讀的文字,讓我們好像在享受獲得知識的欣喜。譬如在第一章裡他對佛洛伊德理論的分析,第二章裡他對伯頓譯本《一千零一夜》裡所蘊含的強烈東方主義色彩的揭露,第三章裡對夏目漱石小說《礦工》與《虞美人草》的解說,都非常吸引人。在第五章裡,他把《海邊的卡夫卡》和戰後日本社會聯繫起來,對一直企圖逃避戰爭責任的右派進行了強烈的抨擊,讓我這個對歷史不是毫無所知的人,都有突然憬悟之感。我第一次感覺到,小說評論是可以和知識傳達完美的結合在一起的。
關於《海邊的卡夫卡》的意識形態傾向,秦剛的譯者序和小森陽一的兩篇序都作了簡要的說明,這裡就不再重複。我想以小說中的一、兩個情節為例,以最簡明的方式呈顯小說想要把讀者引導到哪個方向和哪些心態上。
小說的主角田村卡夫卡,四歲時母親帶著姐姐(養女)離家出走,父親不理他,像個孤兒似的成長到十五歲,這時候他決定離家出走,獨立生活。他從小被父親詛咒,說他會「殺死父親,同母親和姐姐交合」,他一直身懷恐懼,但深心中卻又受到誘惑。離家後他到了高松市,找到了甲村圖書館,每天在那裡看書。圖書館的負責人佐伯雖然已年過五十,但仍然容貌美麗,身材苗條,身上還可以覓出十五歲少女的姿影。田村少年既把佐伯看成他的母親,又每天迷戀她的身影。終於有一天晚上,佐伯以沈睡狀態來到田村的房間(也是以前佐伯和她的情人幽會的地方)和他發生了關係。後來,在田村的懇求下,佐伯以清醒的意識又和他同床兩次。這樣,田村就擬似「同母親交合」了。
這件事發生後,佐伯就不再有生命意志,她在死前跟別人懺悔說:
不,坦率地說,我甚至認為自己所做的幾乎都是錯事。也曾和不少男人睡過,有時甚至結了婚。可是,一切都毫無意義,一切都稍縱即逝,什麼也沒留下,留下的唯有我所貶損的事物的幾處傷痕。
這樣,這一樁擬似「母子交合」的責任就由佐伯承擔下來(因為她貶損了事物,敗壞了世界),她必需死,她也就死了。而那個從頭到尾對佐伯充滿性幻想的、又一直把她假設是母親的田村少年卻一點責任也沒有。
另一個例子是田村少年和櫻花的關係。櫻花是田村在到達高松的旅途中認識的、比他年長的女孩子,像姐姐一樣的照顧他。田村也一直對她充滿了幻想,有一天在夢中強姦了櫻花。在小說結尾時,田村打電話跟櫻花告別,這個情景以這一句話結束:
「再見,」我說。「姐姐!」我加上一句。
最後加上去的「姐姐」這個稱呼就是有意要做實他「奸污」了姐姐。所以田村根本不只被詛咒要「同母親和姐姐交合」,他根本就是有意要犯這個錯。他認為,只有踐行這個詛咒,他才能從命定的重擔下解脫出來,獲得自我與自由。很難形容這是怎麼樣的邏輯。
這樣的田村卻被稱為是「現實世界上最頑強的十五歲少年」,並被勸告要「看畫」、「聽風的聲音」,就是順著感覺走。這樣就是活著的意義,不然,你會被「有比重的時間如多義的古夢壓在你身上」,怎麼逃也逃不掉。這是勸告人要這樣的成長:既然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重擔壓在你身上,你就只能左閃右躲,就只能聽著、看著、幻想著(特別是性),可以這樣悠遊自在,而你沒有任何責任,因為這些都是別人「詛咒」到你身上的。這樣的人生觀,只能令人浩嘆,怪不得小森陽一教授決定加以批判。
最後,感謝王中忱教授讓我接觸這本書,感謝本書的譯者秦剛先生,他為了臺灣的繁體字版又把譯文修訂了一次,同時他的譯文還修正了林少華的誤譯,漏譯之處。當然要感謝小森陽一教授,不論對大陸的簡體版,還是對臺灣的繁體版,他都無償的提供出版權。
2012/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