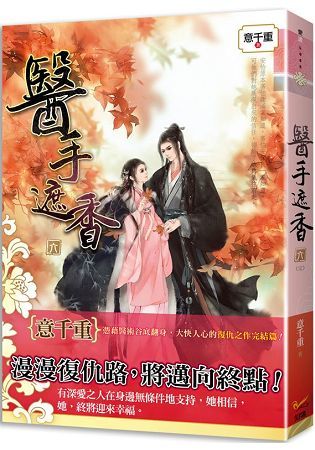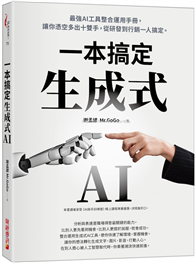對於不知悔改的人來說,永遠不應該有寬恕兩個字。
安怡撒下的復仇之網,已至收網階段,
報應,已離張欣與田均這對陰毒夫妻不遠了。
可即使安怡與張欣的交手,安怡回回都不見輸,
張欣卻仍是掐中了她的一處弱點──她,即是安九。
即便這樣的事情說出去也不見得有人信,
但謠言便是這般可怕的東西,一旦傳言四起,
懷疑便會如瘟疫般擴散開來。
安怡原本害怕謝滿棠知道,害怕安保良一家知道,
可他們對她展現出來的信任,卻給了她勇氣往前走。
復仇之路即將走到終點,
而有謝滿棠牽著她的手,安怡相信,
她要接著走下去的,是一條名為幸福的道路。
本書收錄番外〈花中不知日月短〉。
本書特色
意千重 憑藉醫術谷底翻身,大快人心的復仇之作
一個人,究竟要歷經多少次背叛?
妳何苦,把我帶來這苦難的人世間!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醫手遮香 六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華文羅曼史 |
$ 205 |
古代小說 |
$ 205 |
言情小說 |
$ 234 |
古代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24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醫手遮香 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