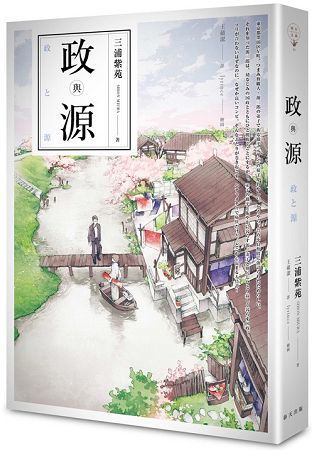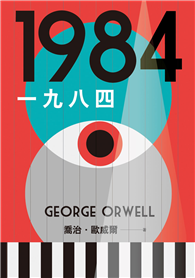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社區的爺爺需要彼此!」──
.圍繞著小社區起舞的超.友誼故事,三浦紫苑的全新境界!
.爺爺們的魅力不容小覷,充滿人情味與老東京氛圍,讓人會心一笑!
.直木賞、本屋大賞得獎作家三浦紫苑,繼《哪啊哪啊神去村》、《啟航吧!編舟計畫》後溫馨療癒新作!
「你有膽就來阻止我的失控行徑啊!」
「什麼!你以為我會輸給你嗎?!」
就是這種老爺爺哥倆好的故事。請多多指教。——三浦紫苑
不要以你的石頭腦袋當作基準!
聽你在那裡放屁!你的腦袋裡才裝滿磚塊呢!
從小一起長大的兩個老頭在下城區放肆撒野!
「我們能夠看到明年的櫻花嗎?」
「天知道。」
東京都墨田區Y町。
都過了七十歲還染著紅髮的花簪工藝師源二郎,和一路走來,始終一板一眼的退休銀行行員國政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兩人性格南轅北轍,互看不爽的時間比惺惺相惜的日子多了好幾倍。某日,源二郎發現,曾經當過混混的徒弟徹平舉止相當異常,似乎遭到了以前狐朋狗友的勒索,於是源二郎和國政決定插手處理,兩名年齡相加百餘歲的老爺爺打算好好逞兇鬥狠一番;就憑手上這把裁布圓刀,爺爺們決定重出江湖!
三浦紫苑一向擅長刻畫人與人間的關係,不論是年輕角色、不善言詞的字典編輯,每個人物印象總能深刻留在讀者心中。本書也不例外,描寫兩個自幼便是死黨的老爺爺的人生與老後生活。兩人個性大相逕庭,卻又巧妙地互補、相互照顧。兩人經常賭氣鬥嘴,卻又深深地了解對方,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說出口,存在於他們腦中的無線電便能交換訊息,兩人深刻的友情深深地令人著迷。
書中字裡行間淡淡地透出溫暖,不把老年生活刻意描寫的艱苦、難熬,反而透過一對好兄弟的互相扶持,點出了老人們的內心世界。看完後仍會想著這對可愛的老人家今後的豐富生活。
作者簡介:
三浦紫苑
一九七六年生於東京,一九九五年進入早稻田大學就讀。二○○○年以長篇小說《女大生求職奮戰記》踏入日本文壇。二○○六年以《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獲得直木賞。二○一二年又以《啟航吧!編舟計畫》獲得本屋大賞。
著有:《強風吹拂》、《星間商事株式会社社史編纂室》、《哪啊哪啊神去村》、《真幌站前》系列、《木暮莊物語》等。
譯者簡介:
王蘊潔
樂在一個又一個截稿期串起的生活,用一本又一本譯介的書寫下人生軌跡,旁觀譯著數字和三高指數之間的競賽。
譯有《永遠的0》、《解憂雜貨店》、《空洞的十字架》、《哪啊哪啊神去村》、《名叫海賊的男人》等多部作品。
著有:《譯界天后親授!這樣做,案子永遠接不完》
臉書交流專頁:綿羊的譯心譯意
章節試閱
徹平在廚房洗好碗後,對他們說: 「我要告辭了。」 「今天很早嘛,要和真彌約會嗎?」 源二郎調侃道,徹平「嘿嘿嘿」地笑了起來。 「我跟她說好,她下班的時候我去接她,然後一起回我家。」 「搞什麼啊,他媽的!」 源二郎抓著紅色的頭髮,不知道是在抱怨徹平,還是在數落巨人隊的打擊始終不見起色。 「回家的路上要小心。」 國政代替心不在焉的源二郎說道,徹平露出有點嚴肅的表情。 「我知道,我真的該小心,最近……」 「發生什麼事了嗎?」 國政催促吞吞吐吐的徹平,但徹平似乎改變了心意,搖了搖頭說: 「沒事。晚安。」 國政走去水泥地,送徹平離開後,鎖好面對巷子的玻璃門,拉起用來遮蔽的窗簾。 「怎麼回事?徹平到底怎麼了?」 國政回到客廳,問源二郎,但源二郎正熱衷於即將進入尾聲的比賽,心不在焉地「嗯」了一聲。 「喂!」 國政推了推源二郎的肩膀,源二郎的視線終於從電視上移開了。 「別管他,徹平已經是大人了。如果真的遇到困難,他會找我們商量。」 巨人隊最後輸了比賽。源二郎走去二樓三坪大的臥室,從壁櫥內用力拉出一床客用被褥。 「唉,真是王八蛋。」 「你看棒球比賽,竟然可以這麼生氣。」 洗完澡的國政看著揚起很多灰塵的源二郎,語帶佩服地說道。 「你說什麼?」 源二郎鑽進兩床並排被褥中的其中一床,生氣地背對著國政躺下了。「唉,太生氣了,我明天的工作效率一定會大幅降低。」 我看你才該拜徹平為師,學習趕快長大。國政拉著日光燈垂下的繩子關了燈,房間內只剩下一個小燈。 「對了,上次的小學生有沒有來?」 「沒來。」 躺在旁邊被褥中的源二郎似乎已經一腳踏進了睡眠的國度,慢條斯理地回答。 「他們真的來了也很傷腦筋,因為這裡和我們小時候完全不一樣,不知道該怎麼應付他們。」 不一樣?是這樣嗎?無論哪一個時代的小孩子,不是都會為相同的事感到高興,為相同的事傷心落淚嗎?國政回想起兩個女兒當年還很可愛時的笑容和吵架的樣子,忍不住偏著頭。 半夜在別人家裡上廁所很辛苦。國政在狹窄的走廊上摸索著,眨著發花的眼睛確認樓梯,在廁所和被褥之間往返了兩次。 第一次去上廁所時,聽到源二郎發出「噗嘶、噗嘶」好像吹泡泡般的呼吸聲,睡得很香甜。國政的腳不小心撞到門檻,叫了一聲:「痛死了」,也沒有把源二郎吵醒。 當國政第二次小解回來後,源二郎顯然在做噩夢。國政蹲在被子旁,思考著到底是怎麼回事。 仰躺的源二郎好像忍受著痛苦的野獸般,小聲地發出悲傷的呻吟。 雖然把他叫醒算是為他好,但夢境也是回到過去的秘密通道,是和在這個世界上再也無法見到的人交談的時間,即使再怎麼悲傷和痛苦,也不想受到任何人的干擾。國政之前因為曾經有過親身體會,瞭解這件事,所以不敢貿然把源二郎從夢中叫醒。 他正在猶豫,源二郎自己醒了。 源二郎在橘色的昏暗空間內看著天花板,然後可能發現了自己臉上的光線被遮住了,將視線移向蹲在他身旁的國政。 「啊,」源二郎說:「是我家被燒毀那天的晚上,我媽坐在矮桌對面。」 雖然他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依依不捨,但又像是鬆了一口氣。國政輕輕地點頭說了聲:「是喔」的時候,源二郎又睡著了。 國政鑽進了客用被子,聽著隔壁傳來的鼻息聲。呼吸並不急促。源二郎似乎終於得到了完全擺脫記憶羅網的數小時。 原來他並沒有忘記。國政想道,但又隨即覺得當然不可能忘記,不由得感到一陣難過。 國政並不瞭解東京大空襲的情況,因為當時他和母親一起疏散到長野的親戚家。當他得知東京發生了可怕的大空襲時,最先想到了源二郎。 當時,源二郎已經是附近花簪工藝師的徒弟。源二郎的哥哥年幼時因病夭折,父親也戰死在沙場,必須靠源二郎和母親兩個人養家。當時還在讀小學的源二郎有一個弟弟,和幾乎還是嬰兒的妹妹,所以源二郎沒有疏散到外地,當然也無法疏散。 源二郎從來沒有親口提起那天晚上的詳細情況,國政只知道源二郎救了上了年紀的師父後拚命逃,但無論家人和房子都被燒成了灰。 國政在大空襲過了半年,戰爭結束之後,才終於回到了Y町。運河上漂浮著垃圾和木材,一排棚屋的上方是一片蒼茫的天空。國政茫然佇立,面對著已經完全變了樣的故鄉。 就在這時,源二郎從街角臨時搭建的小屋內走了出來。國政什麼話都沒說,就跑了起來。源二郎也丟掉手上的臉盆,朝向國政跑了過來。兩個人站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緊緊握著手。 「原來你還活著,」源二郎說:「原來你還活著,真是太好了。」 這是我該說的話吧。國政心想。他的雙眼眼皮發熱,只能拚命咬著嘴唇,總算強忍住了,看著源二郎肩上還殘留著夏日味道的陽光。 國政在被子裡翻了身,尋找睡起來比較舒服的姿勢。 源二郎對在河畔遇到的小學生說:「沒有改變。」但他剛才又說,他不知道該怎樣應付小孩子。 源二郎和家人的緣分似乎比較淺,他獨自在這個家裡,出發前往夢境的世界時,知道會被噩夢糾纏嗎? 我也沒有忘記。那是難以忘記的記憶。國政暗想道。我不會忘記源二郎經歷了如此痛苦的經驗,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關心我;不會忘記源二郎跑過來時燦爛的笑容,不會忘記他握著我的手時多麼用力。 國政保護著疼痛的腰,在被子裡翻了身,最後終於覺得身體縮成一團的姿勢最舒服。源二郎身上的被子規律起伏著。 雖然離天亮還很久,但國政想起自己並不討厭Y町平靜的夜晚。 國政和源二郎分享著切片的烤鮭魚,正把納豆飯扒進嘴裡,真彌打開玻璃門,探頭進來打招呼說:「早安。」 「喔,怎麼了?」 源二郎一臉奸笑地向真彌招手,「徹平這傢伙難得打電話來說:『我感冒了,今天要請假』,我和國政剛才還在說,那傢伙一定是昨晚賣力過頭了。」 「是你一個人嘰哩呱啦,我什麼都沒說。」 國政對源二郎的說法表達了抗議,然後拿了坐墊給真彌。 真彌好像比徹平大幾歲,頭髮染成了栗色,衣著總是乾淨俐落。聽說徹平看到真彌來購買髮廊用的花簪時,立刻陷入了情網。即使別人沒有問,源二郎和徹平也逢人就說,所以舊城區內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的交往過程。 「就是這件事啊。」真彌說著,在坐墊上坐了下來。 「哪件事?」 源二郎用筷子夾斷了納豆的絲。 「徹平請假的理由,那是謊話。」 「偷懶蹺班可不太妙啊。」 聽到國政這麼說,真彌搖了搖頭。 「不是偷懶蹺班……是徹平今天鼻青臉腫。」 源二郎大吃一驚,手上的茶杯掉在矮桌上。 「喂喂,昨晚還好好的,他得了什麼重病嗎?」 「不是,是被人打的。」 國政覺得真彌反應有點遲鈍,說話不得要領。憑她這樣還能夠成為店裡的紅牌美髮師,可見她的手藝真的很厲害。 源二郎從額頭到頭頂部都氣得通紅,和僅剩的頭髮變得一樣紅了。 「敢對我的徒弟動手,是不想活了嗎?到底是哪裡的哪個傢伙幹的?」 「我也不太清楚。」 真彌說,昨天晚上,他們從髮廊回家的路上,突然被兩三個年輕男人包圍。那幾個年輕人想把他們拖進投幣式停車場的暗處,徹平挺身迎戰,讓真彌先逃走了。 「有沒有報警?」 國政問。真彌再度無力地搖了搖頭。 「徹平說,絕對不要通知任何人。我聽徹平的話,一路逃回他的公寓,坐在那裡等了半天,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回來了。當時,我也說要報警,但徹平很生氣地說,不可以報警。」 國政難以想像徹平發脾氣的樣子,因為每次看到他,他都露出親切的表情「嘿嘿嘿」地笑著。 「對了,昨天他說話的口氣也很不對勁,源二郎,你覺得呢?」 「嗯,我不知道。」 雖然前一刻還神氣地說什麼「我的徒弟」,但源二郎似乎並不瞭解徹平的情況,「我們先去看看他再說。」 徹平住在離源二郎家走路五分鐘距離的木造公寓,公寓有兩層樓,從房門的數量推測,每層樓各有三戶,所有的窗戶都掛著窗簾。雖然這棟公寓很舊,但似乎住滿了人。 國政和源二郎跟著真彌走在公寓的狹窄外側走廊上。徹平住在一樓東側角落的房間。真彌沒有按門鈴,拿出備用鑰匙直接開了門。 站在玄關就可以看清楚室內所有的情況。廚房內的碗盤都洗得很乾淨,T恤晾在窗邊。傢俱非常少,只看到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小電視,和折起後豎在牆邊的小型矮桌而已。衣物和製作花簪所需的工具應該都放在壁櫥內。空蕩蕩的三坪大房間看起來很寬敞。 房間中央鋪著一床被子,徹平躺在被子中發出呻吟。他的臉腫得好像凹凸不平的岩石。徹平看到了走進房間的人影,立刻從被子裡跳了起來。 「師父!」 「你躺著吧。」 源二郎傲慢地揮了揮手,國政把帶來的冰塊放在徹平的臉上。徹平再度躺進了被子,源二郎語氣沉重地對他說: 「徹平,真彌已經把事情全都告訴我了。」 「對不起,我原本想隱瞞不說的……」 「嗯,雖然我全都聽說了,但還是搞不清楚狀況。」源二郎說,「徹平,到底是誰幹的?」 徹平躺在被子裡,似乎陷入了猶豫,但最後開了口。 「師父,對不起。我在看到師父的花簪,有幸成為師父的徒弟之前幹了很多壞事。」 「壞事?」源二郎靈巧地挑起了右眉,「像是強暴女人,然後逼良為娼。把老人活埋,還把他們的存款捲走嗎?」 「不,沒這麼誇張啦……」徹平有點慌了手腳。 「所以說,」國政試圖修正軌道,「你以前是小混混。」 「小混混……嗯,對啊。」 「昨晚攻擊你的是你的同夥嗎?」 「以前的同夥。」徹平明確地回答,「我是在葛飾出生,他們越過荒川來這裡找我,似乎很不爽我擅自離開他們,開始認真工作。」 「認真工作哪裡有問題了!」 國政突然怒吼道,源二郎、徹平和真彌都將視線集中在他身上。上了年紀,很容易動怒,實在很不妙。國政反省了自己的暴躁,乾咳了幾下。源二郎開始向徹平發問。 「所以,他們是因為要制裁你從良了,所以才揍你嗎?」 徹平又不是吉原的遊女,從什麼良啊。雖然國政這麼想,但徹平和真彌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句話有什麼不對勁,勉強對「制裁」這兩個字產生了反應。 「是啊。」徹平點了點頭,「但我不想把事情鬧大,因為我之前和他們一起做了很多蠢事。」 「但我可不會善罷甘休。」源二郎抱著雙臂,「好不容易找到的繼承人被揍,有損於我這個師父的名聲。」 「徹平,他們不是還拿走了你的錢嗎?」真彌擔心地說:「他們一定還會再來勒索你。」 很有可能。徹平雖然想要對以前的同夥講義氣,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心存不善的傢伙,看到別人想要認真過日子,就想要動歪腦筋。國政想了一下後說: 「好,徹平,你把他們找來Y町。」 「找他們來幹什麼?」 「我和源二郎會好好說服他們,叫他們別再來找你麻煩。」 「嗯,就這麼辦。」源二郎也點著頭。 「什麼!」 徹平和真彌一臉驚訝地看著他們兩個人。 「說服他們?師父和有田先生嗎?你們加起來已經一百五十歲了欸。」 「是一百四十六。」 國政和源二郎異口同聲地說。 沒有月亮的夜晚。 臉終於消腫的徹平站在不見人影的小巷投幣式停車場。 徹平還沒有聯絡以前的同夥,那些人就又打電話給他,要他再拿錢給他們。他們也沒有忘記撂下「難道你不擔心你的女人會出事嗎?」這句了無新意,卻又讓人無法置之不理的狠話。國政和源二郎聽了勃然大怒,要求徹平約他們在河邊的投幣式停車場見面。 徹平故意比約定的時間遲到五分鐘出現在停車場。背對著運河等待徹平出現的三個年輕男人一看到他,立刻嘲笑他。 「這麼晚才來啊,徹平弟弟,我們還以為你嚇得逃走了。」 「錢帶來了嗎?嗯?」 「我一分錢也不會給你們。」 徹平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冷若冰霜,和平時判若兩人,「我今天來這裡,是要告訴你們別再來找我了。不好意思,讓你們特地跑一趟。」 「王八蛋,你說什麼!」幾個男人激動起來,「徹平,我勸你別不識時務逞強了!」 三個男人向徹平逼近,推了他一把,徹平仍然沒有退縮。他們每次對徹平動粗,掛在身上的鐵鍊就噹啷作響。 完全就是小混混。國政忍不住嘆氣。 「源,走吧。」 「好。」 原本站在停在河面的小船上待命的兩個人,用稱不上是敏捷的動作走上護岸,跨過投幣式停車場的鐵網。徹平露出不安的眼神看著他們,似乎在說:「師父,你們真的要這麼做嗎?」那幾個男人還沒有察覺從背後慢慢逼近的年邁勢力。 國政和源二郎舉起手上的木條,猛然打向站在兩側的混混的肩膀。那兩個男人發出呻吟,當場跪在地上。中間那個混混還不瞭解發生了什麼狀況,慢了一拍之後,才回頭看向國政和源二郎。 「搞什麼啊,死老……」 源二郎不等他把話說完,就用木條斜斜打向他的肩膀。徹平小聲地說:「師父,出手太重了啦!」 「沒這回事!」 源二郎用木條輪流打向蹲在那裡的三個男人的肚子。國政當然也不可能手下留情。一旦那三個人站起來反擊,自己在體力上就輸了,所以他依次在三個男人的小腿骨上打出一片瘀青。 「你們也未免太狗眼看人低了,啊?」源二郎粗聲喝斥道,「你們現在知道對我的徒弟動手,會有什麼下場嗎?」 「下次再看到你們來這裡,就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你們。」 國政打完了他們的小腿骨後放話說道。他開始有點喘,但那幾個混混也有他們要顧及的面子。 「你們從背後來陰的,太卑鄙了。」 站在中央的男人吼道,然後抱住了國政的腿。國政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撞到了腰。雙方立刻陷入了混戰。 「打架哪有卑鄙不卑鄙這種事!」 「老頭子閃一邊去!」 混混開始反擊,源二郎用木條應戰。另一個混混想要加入戰局,徹平從背後架住了他。國政仰躺在地上,騎在他身上的混混打向他的左側臉頰,但國政沒有畏縮,用手上的木條揮向混混的屁股和後背。已經是即使死了,也可能會被說是「壽終正寢」的年紀,自己到底在幹嘛?國政既覺得自己很沒出息,又覺得很滑稽,忍不住想要哭,甚至想不起已經有幾十年沒有體會過快哭的感覺了。 但是,姿勢上的不利還是讓人無能為力。他的腹部受到壓迫,又被接連甩了幾記耳光,立刻感到頭昏眼花。這傢伙竟然對老人毫不留情。國政忍不住感到憤慨,但發現騎在自己身上的混混雙眼通紅,心想恐怕不妙,不由得感到害怕起來。 「政!」 他聽到源二郎的叫聲,隨即感受到一陣風,源二郎從背後把什麼東西抵在騎在國政身上的混混喉嚨上。 「別動!」 源二郎吼道。因為他的聲音太有威力,在投幣式停車場內打鬥的所有影子都靜止了。 「看這個。」 國政抬頭一看,發現源二郎手上拿的木條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了閃著銳利光芒的金屬。 「這可不是吃大阪燒的鏟子,而是圓刀。」 即使不需要源二郎說明,國政一看就知道了。那是把羽二重綢布裁成小塊時使用的銳利刀子。源二郎應該插在長褲的皮帶上帶來這裡。他到底想幹嘛?國政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坐在國政身上的男人僵在那裡,喉嚨因為緊張而緊繃著,喉結上下活動著。 「聽好了,趕快給我滾,不要再過河來這裡。」 源二郎全身散發出震撼空氣的殺氣,「否則,我就要讓這傢伙現在血濺三步。」 一個混混甩開了徹平的手說: 「老頭子,別說大話了!」 「你以為我在說大話?」 國政仰躺在地上,用平靜的口吻插嘴說道。另一個混混原本準備衝過來,但立刻停下了腳步。 「我勸你們趕快離開,」國政用懇求的語氣說道,「事到如今,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了,你們還是乖乖離開吧。他是瘋狗,想當年,他趁戰後混亂,在黑市殺了五個黑道分子。」
徹平在廚房洗好碗後,對他們說: 「我要告辭了。」 「今天很早嘛,要和真彌約會嗎?」 源二郎調侃道,徹平「嘿嘿嘿」地笑了起來。 「我跟她說好,她下班的時候我去接她,然後一起回我家。」 「搞什麼啊,他媽的!」 源二郎抓著紅色的頭髮,不知道是在抱怨徹平,還是在數落巨人隊的打擊始終不見起色。 「回家的路上要小心。」 國政代替心不在焉的源二郎說道,徹平露出有點嚴肅的表情。 「我知道,我真的該小心,最近……」 「發生什麼事了嗎?」 國政催促吞吞吐吐的徹平,但徹平似乎改變了心意,搖了搖頭說: 「沒事。晚安。」 國政走去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