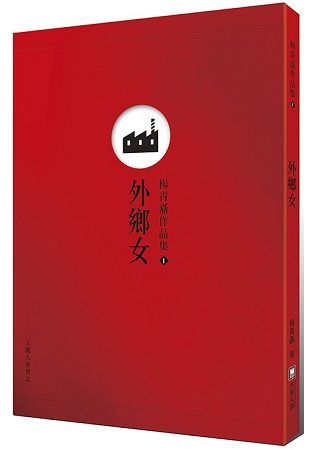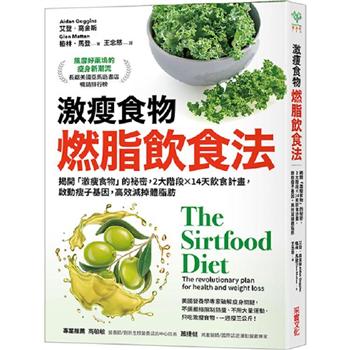★民視自製單元劇「外鄉女」原著小說首次集結成冊
★「工人作家」楊青矗撰寫,「工廠系列」第三部作品
在農業轉型到工業時代,農村許多女子離鄉背井到外地打工討生活,每個女子背後都有許多故事與原因。宿舍裏的女工來來去去,為了孩子生存、為了幸福追尋、為了父母掙扎……每個人都有著屬於她們自己努力打拼的理由。
博士班研究生邱錦鳳為了寫論文,隱瞞自己的學歷與家境,到工廠去打工、到宿舍去租居,記錄下她身邊女工們的故事。
民視自製單元劇「外鄉女」之原著,由被稱為「工人作家」的楊青矗老師所撰寫的短篇系列小說,刊登於1984年至1985年間的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等刊物上,首次收錄為單行本。
本書收錄有:〈澀果的斑痕〉、〈大都市〉、〈剪掉半邊像〉、〈父母親大人〉、〈初出閨門〉、〈老芋仔新蕃薯〉等六篇小說。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外鄉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現代小說 |
$ 238 |
小說/文學 |
$ 252 |
小說 |
$ 252 |
中文書 |
$ 252 |
現代小說 |
$ 252 |
文學作品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外鄉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青矗
1940年出生於臺南縣七股鄉一個世代務農的貧困家庭。後來父親到中油高雄煉油廠任消防隊員,所以11歲隨父母遷居高雄。1961年父親不幸殉職,被以撫恤遺族身分進入高雄煉油廠工作了19年,在此寫下《在室男》、《工廠人》、《工廠女兒圈》等以農民、工人為主角之小說著作,並跨足工運及政治,1979年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四年,出獄後專注臺語語文與研究,編著有《台華雙語辭典》、《台灣俗語辭典》、《台詩三百首》等。
楊青矗
1940年出生於臺南縣七股鄉一個世代務農的貧困家庭。後來父親到中油高雄煉油廠任消防隊員,所以11歲隨父母遷居高雄。1961年父親不幸殉職,被以撫恤遺族身分進入高雄煉油廠工作了19年,在此寫下《在室男》、《工廠人》、《工廠女兒圈》等以農民、工人為主角之小說著作,並跨足工運及政治,1979年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四年,出獄後專注臺語語文與研究,編著有《台華雙語辭典》、《台灣俗語辭典》、《台詩三百首》等。
序
葉天倫推薦序
歷史的容顏,台灣媽媽的少女時代
早在一九八五年,我父母已經將楊青矗老師的作品《在室女》改編為電影,至今我對主題曲還朗朗上口。一九九七年民視開播,公司又製作了另一部楊老師作品《在室男》,並以全台語演出,也是我第一次進公司劇組擔任助理,還演出其中一個角色。因此我對於楊老師的作品特別有一種親切感。
《外鄉女》一直是父母與楊老師的遺珠之憾,因為楊老師的視力受腦疾影響,雖然深知外鄉女系列故事埋藏在舊報章中,卻苦無機會出版成書。看著這麼好的著作被埋沒,深感可惜,於是我們決定製作連續劇《外鄉女》。我們與老師一同整理,到國家圖書館找出當年的報紙,老師也提供他當年書寫的手稿給我們,讓一部代表台灣七、八○年代的時代縮影之著作,重新以影像的方式展現在大眾面前。
《外鄉女》描述的是一群社會底層女工的故事,從作品中我感受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年間,台灣經濟起飛時,台灣人的拼勁,以及快速膨脹的經濟,造成的社會現象及階級問題,在時代的擠壓感下,感受到台灣最珍貴的人情味。不管是不同省籍還是不同階級,互相較勁,互相幫助,一同前進。女工在工廠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也呼應最近社會上討論得沸沸揚揚的勞資問題。長年下來,勞工很少發聲,因為他們想著的可能是「惹火老闆就會失去工作」、「如果工廠倒了我們就沒飯吃」……等關於生存的問題,當生存都可能有危機,她們如何談論權益?從楊老師文字裡流露出來的,不只是大時代裡小人物的痛,更是台灣社會一路走來的傷。
有一天,和年輕的剪接師吃著便當聊天,他說在家裡和家人一起看《外鄉女》播出的時候,他的媽媽突然說:「這就就是我以前的故事啊!」她說著和同學們是如何在國中畢業典禮結束後,整台遊覽車載著大家分配進北部不同工廠,以前是如何論件計酬……說著說著媽媽眼底淚光閃閃,而這部戲劇意外成了母子更瞭解彼此的一個契機。
我想,這就是將這樣刻劃時代的文學作品,翻拍成影像作品最大的意義。
作為以台灣為養分的影像創作者,我們從楊老師這樣有血有肉的作品中得到力量。現在看到這樣好的作品,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集結成書,心中有種說不上的踏實。你我的母親阿姨阿嬸姑姑婆婆,都可能曾經是「外鄉女」。這是一本能看見「媽媽的少女時代」的小說,請大家和家中長輩一起回味當年。
歷史的容顏,台灣媽媽的少女時代
早在一九八五年,我父母已經將楊青矗老師的作品《在室女》改編為電影,至今我對主題曲還朗朗上口。一九九七年民視開播,公司又製作了另一部楊老師作品《在室男》,並以全台語演出,也是我第一次進公司劇組擔任助理,還演出其中一個角色。因此我對於楊老師的作品特別有一種親切感。
《外鄉女》一直是父母與楊老師的遺珠之憾,因為楊老師的視力受腦疾影響,雖然深知外鄉女系列故事埋藏在舊報章中,卻苦無機會出版成書。看著這麼好的著作被埋沒,深感可惜,於是我們決定製作連續劇《外鄉女》。我們與老師一同整理,到國家圖書館找出當年的報紙,老師也提供他當年書寫的手稿給我們,讓一部代表台灣七、八○年代的時代縮影之著作,重新以影像的方式展現在大眾面前。
《外鄉女》描述的是一群社會底層女工的故事,從作品中我感受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年間,台灣經濟起飛時,台灣人的拼勁,以及快速膨脹的經濟,造成的社會現象及階級問題,在時代的擠壓感下,感受到台灣最珍貴的人情味。不管是不同省籍還是不同階級,互相較勁,互相幫助,一同前進。女工在工廠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也呼應最近社會上討論得沸沸揚揚的勞資問題。長年下來,勞工很少發聲,因為他們想著的可能是「惹火老闆就會失去工作」、「如果工廠倒了我們就沒飯吃」……等關於生存的問題,當生存都可能有危機,她們如何談論權益?從楊老師文字裡流露出來的,不只是大時代裡小人物的痛,更是台灣社會一路走來的傷。
有一天,和年輕的剪接師吃著便當聊天,他說在家裡和家人一起看《外鄉女》播出的時候,他的媽媽突然說:「這就就是我以前的故事啊!」她說著和同學們是如何在國中畢業典禮結束後,整台遊覽車載著大家分配進北部不同工廠,以前是如何論件計酬……說著說著媽媽眼底淚光閃閃,而這部戲劇意外成了母子更瞭解彼此的一個契機。
我想,這就是將這樣刻劃時代的文學作品,翻拍成影像作品最大的意義。
作為以台灣為養分的影像創作者,我們從楊老師這樣有血有肉的作品中得到力量。現在看到這樣好的作品,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集結成書,心中有種說不上的踏實。你我的母親阿姨阿嬸姑姑婆婆,都可能曾經是「外鄉女」。這是一本能看見「媽媽的少女時代」的小說,請大家和家中長輩一起回味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