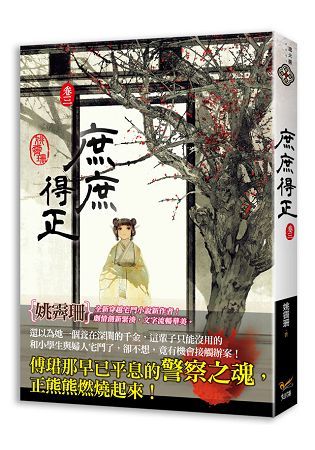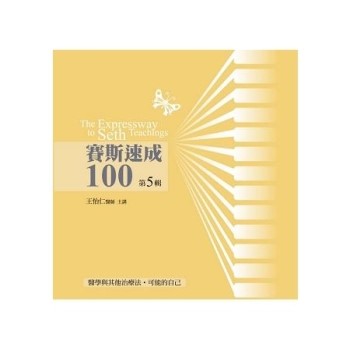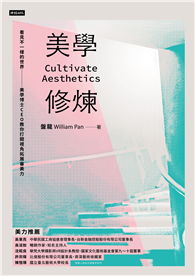第一章
五月的天光明亮鮮麗,這一路行來,綠樹森森、花香渺渺,微斜的日影將傅珺與涉江的影子拉得很長。
傅珺緩步而行,不多時便來到小石橋邊。卻見清溪之上,水波蕩蕩,偶爾一隻蝴蝶飛過,停落在溪邊的野草上,那絢麗的蝶翅一張一合,似是在和著微風舞蹈。待歇了一歇,便又振起雙翼,翩翩地跳著舞,飛得遠了。
傅珺立在橋邊,信手攀住橋邊垂下的柳條,心緒亦跟著那蝴蝶一同,飛去了極遠的地方。
三年前,亦是這樣一個明媚而溫暖的季節裡,在那個離別的渡口邊,她將一封信悄悄交給了傅庚。
在那封既無抬頭、亦無落款的信中,傅珺那稚嫩的筆鋒落下的第一句話便是:「千萬不要忽視小人物的存在。須知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隻蝴蝶搧動翅膀所產生的微風,很可能便會引發蛟江的一場風暴。」
那是傅珺第一次給傅庚寫信,也是她兩世人生中,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與親人進行溝通。而那封信中的內容,卻是冰冷而嚴肅的。在信中,她沒有寫離別時的牽掛,更不曾留下分毫思念與親情。
她只是在那封信裡,對王氏疑被人投毒致死一案,進行了清晰的陳述與細緻的分析,並做出了合理的推斷。
她不會忘記,在王氏離開後的那段時間裡,幾乎每一個夜晚,她都會在夢中重回到那個淒惶的午後。在夢裡。她反覆刻印著那些畫面,寒冷的風、枯瘦的木樨樹、面目模糊的親人,還有那個腳印凌亂的東角花壇。
她對王氏之死的一切懷疑,便從花壇邊的腳印開始。
在被她「拍」下的記憶中,她發現的第一個疑點,便是腳印。
在許多混亂的、雜著煤灰的腳印中,有一行模糊的腳印,從小書房的窗下延伸至此,盤旋回轉後又回到了原處。
那腳印在窗下時還是乾淨的,於未曾掃淨的殘雪上留下了一痕潔白。而隨著腳印行至花壇邊。腳印的顏色便漸漸染了灰黑。等到回至書房院牆的窗下時,便留下了一個腳尖朝著窗子的黑印。
由此傅珺斷定,這腳印的主人一定不是秋夕居的人。因為,那段時間王氏有孕在身。沈媽媽怕雪天路滑。便在秋夕居中庭的露天地面上都鋪了煤灰。秋夕居各人的鞋底上。多多少少會沾些灰黑色。卻唯有那行腳印,開始時潔白如新,直到後來才沾了灰。在小書房院牆外的窗下亂成了一團。
而第二個疑點,便在於那腳印的起始位置。
眾所周知,傅庚小書房院牆上的窗子是被釘死了的。然而,傅珺卻發現,那窗臺上的雪被人碰掉了好些,上頭還有一個不甚明晰的手印。
那是屬於成年女人的手印,手掌秀氣、五指纖長。
傅珺由此大膽推斷,一個從外面來的神祕女人,由這扇窗子翻窗而入,進入了秋夕居,一路行至花壇邊又回轉了來,再由這窗子進入了小書房。
可是,那窗子釘得很死,傅珺當時在現場是查過的。那麼,那個神祕女人是如何於此處出入的呢?
帶著這個疑問,傅珺自昏迷中醒來之後的第二天,便去勘查了那扇窗子。
而隨後她發現,那窗子確實是釘死的,無論從內還是從外都無法打開。可是,再細查下去,另一個疑點便又浮出了水面。
那釘住窗戶的釘子,是新的,釘子旁邊還有一個鏽蝕了的釘眼。
傅珺由此推斷,這釘子是新釘上去的。原先的那枚釘子,不知何時被人起動了,所以那個神祕的女人,才能從窗子裡翻進院中。
而後,這扇窗子又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重新釘牢了,只是那釘窗子的人大約十分慌亂,將原先的釘眼留了下來。
傅珺對那留下的鏽蝕釘眼進行了仔細的查看,發現那釘眼四周木質鬆動,卻沒有明顯的折裂痕跡。這表示著,鬆動窗子之人用的不是蠻力,而是一點一點的水磨工夫,很可能是花費了數天甚至數十天的時間,才慢慢將釘子弄得鬆動,最後起開了釘子。
從行為模式上看,那鬆動釘子之人十分小心謹慎,很能耐得下心來;而那釘窗子之人卻比較粗心,連原先的釘眼都沒注意到,只匆匆將窗子重又釘牢了。
傅珺由是斷定,這是兩個人分別所為。她估且推斷,那個翻窗而入的神祕女子,便是鬆動釘子之人;而重新釘牢窗子的則另有其人。
那麼,先按下這釘窗之人不論,那女子翻窗而來,又是所為何事?
在「拍」下的場景「照片」中,傅珺又發現了另外的兩處疑點。
其一,便是那株灑金秋海棠。
那株花原先長得十分茂盛,枝葉形狀亦很豐美。而在傅珺於王氏出事那天進行現場勘察時,卻發現那花少了半邊枝葉,兩不對稱,呈傾斜之勢。事後傅珺仔細搜檢了自己的記憶,終於發現,在被她「拍」下的畫面裡,那秋海棠枝葉上的斷痕沒有錯齒,而是十分平整。此外,落雪之後,旁的花草上均堆著雪,唯有秋海棠上的雪被碰掉了。
傅珺由此推斷,這株秋海棠是被人用剪刀剪斷的。因是人為所致,連帶著花上的雪也被碰掉了,所以留在傅珺記憶裡的才會是那種畫面。
其二,則是滴落在花壇邊的一小灘油跡。
當傅珺勘察現場時,她聞到了一股極其淺淡的油脂味道。當時她頭腦混亂,並未在意。然而,這味道卻清晰地印入了她的腦海,留在了記憶之中。過後回想時,她便記起,那花壇前的地面上,混雜著一小灘凍硬了的油跡。
這油跡便藏在散落的煤灰之下,十分隱蔽,若非傅珺有著超強的記憶力,清晰地記下了當天的一切情景,只怕便會忽略掉。
眾所周知,煤灰雖能止滑,卻也僅限於對雪或水起作用,對於油漬,尤其是凍硬了的油漬,其作用卻是微乎其微。而王氏滑的那一下,以傅珺推測,想必是這灘油跡在作祟。
由這兩個疑點以及那串腳印,傅珺得出了一個結論:
那個神祕女人從小書房翻窗而入,偷偷在花壇邊灑下了一灘油,又剪去了王氏最喜歡的秋海棠的花枝。
懷素曾回憶說,王氏在滑倒前輕「咦」了一聲。此際想來,應是王氏散步至此,見花枝不對,上前察看,而那灘油便在彼時起到了作用。王氏踩上了凍硬的油漬,險些滑倒,幸好被沈媽媽與懷素扶住了。
至此,傅珺得出了一個結論與一個疑點。
結論是:那個神祕的女人,對王氏的喜好十分熟悉,知道王氏飯後喜歡在東角的花壇邊散步,對那株灑金秋海棠十分重視,所以才會故意去破壞花枝引王氏踏上油跡。
然而,疑點亦是由此而來:這女人費盡心思,冒著極大的風險,便是為了讓王氏有驚無險地滑上一下麼?
需知王氏散步那可是有一堆丫鬟僕婦隨侍的,又有人攙扶,怎麼可能輕易滑倒?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那麼,她的目的是什麼?
王氏先是滑倒,不久後便宣告病重,很快即告不治。由病發至亡故,時間十分短暫,這難道是巧合?
傅珺清楚地記得,那醫術了得的魯醫正曾說,王氏只是身子虛了些,只需待次年開春便可無礙。而由王氏病逝的那日至開春,也不過就十來天光景。而王氏偏偏就在開春之前病至危重,難道這又是巧合?
不。這絕對不可能是巧合。
那神祕女子甘冒奇險,翻窗而入的目的,絕對不會僅僅是讓王氏滑一下這麼簡單。尤其是,那女子對王氏的生活作息十分熟悉,必定知道沈媽媽等人對王氏護得很緊,那灑油的舉動怎麼看都帶著盲目性,與她之前處心積慮弄鬆窗子的舉動很不相符。
至此,答案幾乎呼之欲出。
那神祕女子翻窗而入的目的,一定是為了更大的圖謀,比如:置王氏與死地。
然而,置王氏於死地,和費盡心機引王氏滑倒,這兩者間又有怎樣的連繫?
傅珺再度回憶起,懷素與沈媽媽都說,王氏滑了一下之後,便被扶進房中。隨後喝了藥,不久後便說睏倦,便上了床休息。待她們聞到血腥味時,王氏已經昏倒在了血泊中。
據傅珺所知。魯醫正開的藥裡的確有些安神的成分,王氏有時也會睡上一會。只是,在懷素與沈媽媽的描述中,王氏那一天的睏倦程度卻是比往常都要重一些,喝了藥沒一會便睏了。
傅珺的直覺是:那天的藥一定有問題。
可是,那藥渣事後魯醫正曾細查過,未發現任何疑點。而與熬藥之事相關的所有人與物,傅庚亦曾派人查過,亦是毫無問題。
由此傅珺只能推斷出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結論:
毒是直接下在藥湯裡的。而那只喝藥的碗在王氏用過之後,便即交下去洗淨了,上頭的痕跡已然湮滅。
這是用排除法得出的結論。
而根據這個推論,便又衍生出了另外一個疑點:那女子是如何將毒直接放進藥湯裡的?
王氏的藥在熬製過程中,全程都由沈媽媽等人看管,除非有人配合,否則那女子不可能將藥放入碗中。
但是,若真有內應,那女子便不必耗費那麼長的時間去鬆動小書房院牆的窗子,還翻窗進來剪去花枝並灑上油漬了。此等事由內應來做不是更穩妥麼?
由此可知,至少在王氏的房中,這女子並無內應。甚至就連那個釘窗子之人,傅珺也認為此人被人利用的可能性遠高於內應的可能性。
那麼,這毒便一定是那女子親手放進湯藥裡的,只是放的時機非常巧妙,未令人察覺而已。
依據所知的事實,傅珺有了一個大致的推斷,而這個推斷亦是由那神祕女子看似毫無理由的行徑中得出的:那神祕女人讓王氏滑了一下的主要目的,應是想要引起混亂。
據沈媽媽後來回憶,王氏滑了那一下,所有人都嚇壞了,她與懷素皆驚叫了起來,秋夕居裡發生了一場不小的混亂。而彼時王氏的藥剛熬好,據熬藥的蘭澤回憶說,她把藥放在桌上後,便聽見外頭一陣叫嚷聲,說是太太滑倒了,她嚇得連忙跑了出去。
那個神祕女人要的,恐怕便是這樣的效果。
在那場混亂出現時,所有人都跑去了王氏身邊,屋中無人,藥在桌上,這是最好的下藥時機。
傅珺甚至認為,只要能下毒,無論是將毒放在碗中還是放在熬煮藥劑的瓦罐裡,那女子並不在意。
她的目的就是下毒,至於事後會不會被人查出來,她應該沒想那麼多。從她剪斷花枝滴灑油漬的舉動來看,她已經完全不計後果了,就算事後被發現她也不在乎。
此外,傅珺還相信,那藥一定是無色無味,且十分難於查找的。這個設想,是在沈媽媽將王氏的那個藥匣交給她後,她才想到的。
既然這世上有南山國的祕藥,那便必定會有其他祕藥。那下藥之人熟悉王氏的生活習慣,熟悉王氏的病情,只要選對了藥物,讓王氏的下紅之症重上十分,王氏本就虛弱的身體,必會因失血過多而承受不住。
然而,以上種種,終究只是傅珺的推斷而已。缺乏證據,又無法從王氏的屍體上獲取更多的信息。傅珺的推論再精密,也無法被證實。
而若這個推論成立,則第二個疑點又出現了:那女子既非秋夕居之人,還要尋機下毒,便只有時刻觀察秋夕居的情況,才能找到機會。
那麼,她是在何處觀察秋夕居的動靜的?傅珺相信,一個面生的丫鬟或僕婦,不可能長時間暴露在沈媽媽與懷素她們的眼皮子底下,這樣被發現的機率太高了,那女人不可能在冒險翻窗而入之後,行如此草率之事。
那麼,她便必須找到一個地方,不僅能藏身,還能時刻觀察秋夕居的動靜,這個地方究竟在何處?
關於這個問題,傅珺想了好幾天,直到她忽然想起了傅庚小書房裡那間上著鎖的房間時,才猛地豁然開朗。
她尋了一個借口,讓傅庚打開了那個房間,又尋機支走傅庚,在那個房間裡做了簡單的勘察,結果,在房間的窗屜邊,她找到了一根女人的長髮。而那個房間的窗子亦如傅珺所料,插銷並未插上,只是閉緊了而已。
能夠進入這個房間的女人,全侯府也只有王氏一人。而王氏此前因有孕,很長時間都未曾進去過,因此傅珺能夠肯定,這根長髮是那個神祕女子落下的。
而由這根頭髮以及那扇拔去插銷的窗子,傅珺推論,那神祕女子一定是事先用鑰匙打開了小房間,進去後再拔下窗上的插銷,翻窗出去後從外面繞進來,將房門從外鎖好。然後,她便可循原路翻窗回到這間密室,再從內關好窗扇,熬過由午夜至天明的這段時間。
而後傅庚帶著傅珺進宮,將行舟留在秋夕居聽用。而小書房因出入皆要鎖門關戶,十分不便,因此,行舟便守在了秋夕居外頭的那道角門裡。
這樣的情形,無疑為那神祕女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她甚至可以從密室中出來,直接守在書房院牆的窗邊等待時機。
其後,王氏於散步時滑到,秋夕居如期出現了一場混亂。那神祕女子便趁亂翻窗而入,跑進王氏的房間下毒。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為何那窗下的腳印後來會亂成了一團,其中有兩個腳印指向正房的方向。傅珺此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在這個推論中全都得到了解釋。
至於那女子的脫逃之法,則十分簡單。傅珺相信,在那樣的一場混亂之下,沒有人會注意到那些下等丫鬟僕婦們的動靜。就連沈媽媽事後回憶時,亦說當時只顧著招呼一眾人等過來,將王氏抬進屋中,旁的便沒注意到,更沒人會去注意有誰進出了秋夕居。那女子完全可以趁此機會逃脫。
將這個女子的行為過程推理完畢之後,傅珺便又回到了此前的另一個疑點:那個釘窗子的人。
傅珺相信,能夠拿到小書房密室的鑰匙,還能夠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將釘死的窗戶弄鬆,那神祕女人所為,絕非憑一己之力,而是有人配合。
這配合之人,便是那個重新釘牢窗戶之人,亦一定是能夠隨意出入小書房,且配有那間密室鑰匙的人。
符合以上所有條件的人。除了傅庚與王氏之外,便只有二人:行舟與汲泉。
結合王氏出事當天的狀況,那天是行舟留守家中,而汲泉隨傅庚出行。因此,從表面看來,行舟與人勾結的嫌疑最大。
可是,在其後的走訪詢問以及多方打探之下,疑點卻漸漸集中到了汲泉的身上。
據守著小書房連接前院夾道的角門的李婆子曾說,有好幾次她早上來接班兒時。前頭值夜的馬婆子都睡得極死。她隱約聽馬婆子說過,汲泉給她送的酒酒勁兒很大,每回喝完了酒都會睡得特別沉。
再如,秋夕居的一個灑掃媽媽回憶說,出事那天的傍晚,大家正忙著布置靈堂的時候,她看見汲泉手裡拿著像是錘子的事物,從小書房院牆那邊走了過去,行色匆匆,表情十分惶急。
還有,在王氏病危那天的午後,便在傅珺心思慌亂地勘察花壇現場之時,她清楚地回憶起,等在院門外頭的汲泉,臉上有著不自然的憂懼之色。當時她以為汲泉是憂心王氏,但後來細想之下,那時的汲泉雖表情憂慮,可前額緊皺、嘴角緊繃,顯得十分不自然。
前額緊皺、嘴角緊繃,這兩樣都是表示憤怒的微表情。
主母病危,一個下僕可能會焦慮,也可能會擔憂,卻絕對不可能憤怒。除非,他發現或者是意識到自己被人利用,成了棋子,於是才會產生憤怒的情緒。
這些,都是傅珺後來才想到的。那時已經是事發後兩個月了,她是通過回憶,才確定了這一點。
而事情查到汲泉的身上,傅珺便已再無施展的餘地。
汲泉是傅庚的人,傅珺只要稍有動作,傅庚必會查知。傅珺無法繞過傅庚去繼續查案,她只能將這件事交予傅庚,由他繼續往下查。
在那封信的末尾,傅珺這樣寫道:
「在許多事件中,小人物往往能起到關鍵的作用,娘親之逝,從根本上說,便在於不曾防及這些小人物。汲泉是父親的長隨,女兒查到他的身上,已屬對父親不敬。然此人乃本案破點所在,須得細查。故女兒寫下此信,將所知悉數相告。女兒相信,父親一定能給女兒一個圓滿的答覆。」
而傅珺沒有寫在信裡的是,對於汲泉,她曾經有過動手的念頭。
她打開了王氏留下的祕匣,對著那一排排的藥瓶,想像著將其中的某種藥物,灑在汲泉的飲食中的情景。
而最終,她卻沒有這樣做。
她掌握的證據不夠充分。她所掌握的全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人親眼看見汲泉釘窗子,也沒有人看見汲泉將密室的鑰匙交給了旁人,更沒有人能夠證明汲泉與哪個女子過從甚密。
傅珺所擁有的,大部分僅僅只是她的推論。雖然她有九成的把握可以斷定,她的推論與事實十分接近,但是,那畢竟只是推斷,而並非事實。
更何況,就算證據充分,她應該也必須將之交由本地的司法機關,依律法處置,而非私下行刑。否則,她又與那些犯罪分子何異?
所以,她只有將所知的一切寫在信中,告知傅庚,並請求由這個比她更有能力、也更便於行動的成年人,來完成對此案的偵查工作。
傅珺深知,能夠查到汲泉的身上,於她而言已是極致。她的年齡、身分與性別,注定了她在此事上能夠施為的空間,只有這麼一點點。她甚至應該慶幸,至少她還有可以委託的對象,而這個人又恰巧是她的父親。她的直覺告訴她,傅庚一定能夠將此事徹查到底。
因此,那封信與其說是請求,不如說是委託。雖然傅珺明知道,為人子女者,在大漢朝這樣的時代,寫了這樣一封冰冷且毫無感情的信給父親,是極為不妥的。可是,她只能寫出這樣的信來。
她的怨與恨,還有不甘和委屈,只能通過這樣一封沒有抬頭亦無落款的信,傳達給她的父親。
在潛意識裡,她希望傅庚能懂得她的心情,也隱隱地希望著,能夠得到傅庚的寬慰與安撫,還有諒解和許諾。
然而,在來到姑蘇後的整整一個月間,她並未等到期待中的回信。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庶庶得正(卷三)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05 |
穿越文 |
$ 221 |
古代小說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庶庶得正(卷三)
母親王氏的驟逝,令傅珺父女猝不及防。
她知道母親的死,絕非偶然,
可她年紀還太小,就算有著成人的靈魂,
還是什麼都做不到。
只能被父親送到姑蘇的外家,
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幸而,她還有超強的記憶力。
就如同現代的證物照片一般,
終有一天,她會找到凶手,令之伏法!
只是在這之前,她卻萬萬沒有想到,
身為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侯府千金,
她居然有機會,憑自己的能力協助辦案。
傅珺體內那顆屬於警察的心,
按捺不住地跳動了起來!
本書特色
微表情能破案,但,能宅鬥嗎?
她是現代獨立自主的警察,一朝穿越,變成小女孩也就罷了,
居然還要應付接連而來的宅鬥考驗!
作者簡介:
姚霽珊,金陵人士,坐望六朝煙水間,汲泉煮字、搗文成衣,文字細膩優美,擅寫景抒情,散文及小說見諸各雜誌報刊,曾出版作品《至媚紅顏》、《一花盛開一世界,一生相思為一人》、《世間女子最相思》、《願你已放下、常駐光陰中》,現為閱文集團簽約寫手,著有長篇小說《庶庶得正》、《折錦春》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五月的天光明亮鮮麗,這一路行來,綠樹森森、花香渺渺,微斜的日影將傅珺與涉江的影子拉得很長。
傅珺緩步而行,不多時便來到小石橋邊。卻見清溪之上,水波蕩蕩,偶爾一隻蝴蝶飛過,停落在溪邊的野草上,那絢麗的蝶翅一張一合,似是在和著微風舞蹈。待歇了一歇,便又振起雙翼,翩翩地跳著舞,飛得遠了。
傅珺立在橋邊,信手攀住橋邊垂下的柳條,心緒亦跟著那蝴蝶一同,飛去了極遠的地方。
三年前,亦是這樣一個明媚而溫暖的季節裡,在那個離別的渡口邊,她將一封信悄悄交給了傅庚。
在那封既無抬頭、亦無落款的信中,傅珺那稚...
五月的天光明亮鮮麗,這一路行來,綠樹森森、花香渺渺,微斜的日影將傅珺與涉江的影子拉得很長。
傅珺緩步而行,不多時便來到小石橋邊。卻見清溪之上,水波蕩蕩,偶爾一隻蝴蝶飛過,停落在溪邊的野草上,那絢麗的蝶翅一張一合,似是在和著微風舞蹈。待歇了一歇,便又振起雙翼,翩翩地跳著舞,飛得遠了。
傅珺立在橋邊,信手攀住橋邊垂下的柳條,心緒亦跟著那蝴蝶一同,飛去了極遠的地方。
三年前,亦是這樣一個明媚而溫暖的季節裡,在那個離別的渡口邊,她將一封信悄悄交給了傅庚。
在那封既無抬頭、亦無落款的信中,傅珺那稚...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姚霽珊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7-09-04 ISBN/ISSN:97898694481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