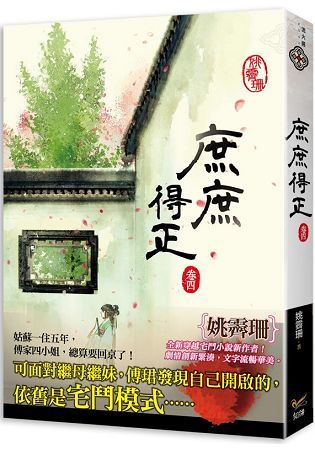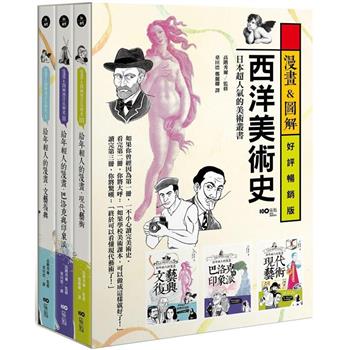第一章
傅珺並沒有回府,而是打算先去賞心樓。她想要早些見到王襄,將李念兒的事情徹底解決好。
因此,馬車離了小酒樓之後,便循著原路彎上了寶帶橋的橋口,再沿臥龍大街往回走。
因今日乃是節日,街上車來人往的,頗不易走,馬車也是走走停停,耽擱了好些時候才到達賞心樓。
待馬車停穩之後,傅珺便在沈媽媽等人的尾隨下步下了馬車,正打算由側門進去,忽聽身後傳來一道溫和的聲音道:「前頭的可是四表妹?」
傅珺驀然回首,卻見唐修穿著一襲竹青色長衫,負了兩隻手立在離她不遠的地方,端秀的面上帶著一絲笑意,正含笑看著傅珺。
「修表哥。」傅珺微有些吃驚地道:「怎麼這樣巧?」
唐修溫和地笑道:「我也是才趕過來的。看著前頭的人像是妳,便喚了一聲。」
傅珺對這位唐家大少爺印象頗佳,只覺得唯有他這般行止風度,才能當得起「公子」二字。故此時相見也是心下歡喜,便含笑上前跟他見禮,又向他身後略掃了一眼,卻沒發現唐俊的身影。
唐修便和聲問道:「四表妹是來見滄浪先生的麼?」
傅珺淺笑道:「正是呢。」
唐修便笑道:「既是如此,我們便一起進去吧。我也要尋父親說幾句話。」
傅珺點頭應是,便隨在唐修身後一同跨進了側門。
踏上了那條幽靜的迴廊。傅珺看了看走在前頭幾步遠的唐修,不由又想到了負氣而去的唐俊。她終是忍不住,便輕聲問道:「修表哥,請問您知道俊表哥去了哪裡麼?」
唐修聞言便停了下來,轉首望著傅珺,端正的面容上掛著一絲淺笑,溫和地道:「勞四表妹動問,我二弟先回家去了。」
原來居然把唐俊氣得先回家去了,傅珺心中微覺不安。
她問的那個問題會讓唐俊產生這麼強烈的反應,這是她始料未及的。
傅珺甚至在想。是不是她讓唐俊受到了傷害?會不會這唐俊也和她那次落水一樣。得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她的症狀是遺忘,而唐俊的症狀是憤怒?
她沉默地跟在唐修身後走了一會,越想便想覺得,這事不好就此便罷。若她無意間傷害了唐俊,至少她也應該表示下歉意才是。
思及此,傅珺便停下了腳步,轉首對沈媽媽做了個手勢。
沈媽媽微覺訝異,卻也沒多說什麼,只帶著丫鬟們站在原地不動了。
傅珺便上前兩步,輕聲地道:「修表哥,可否借一步說話?」
唐修停住腳步,回首看了看傅珺,隨後便向身旁的小廝示意了一下,那小廝忙帶了人退後了好幾步。唐俊便面含微笑地道:「四表妹請說。」
傅珺的面上露出幾分赧然來,低聲道:「好教修表哥知道,方纔我怕是惹俊表哥生氣了,我心裡很過意不去。這會子俊表哥又沒在,只好請您代為轉達我的歉意。」
對於傅珺的道歉,唐修沒有一點吃驚的表現,面上的神情依舊是溫和淡然,聲音低緩地道:「四表妹言重了,阿俊便是有些小孩子脾氣,不妨事的。」說至此他頓了一頓,又問道:「既是四表妹說起來了,我且猜一猜,四表妹是不是問了阿俊四年前的事情,他才負氣走了?」
傅珺不由睜大了眼睛,微有些訝然地道:「正是如此。修表哥真是一猜即中。」
唐修聽了這話,面上便浮現出一絲笑來,似是忍俊不禁的樣子。他將一隻手握成拳頭抵在唇邊,咳了一聲方道:「四表妹約莫是不知道,阿俊四年前那件事,卻是不能向他提的。」
傅珺見了他這表情,再聽了他的話,心裡便有些糊塗起來,臉上便也帶了出來。
唐修便將聲音壓低了一些,輕聲道:「四表妹於阿俊有救命之恩,這事說予妳知亦是該當的。其實,四年前,阿俊不是被人拐走的,而是他自己非要跟著人家走的。」
傅珺的眼睛一下子睜大了。
唐俊居然不是被拐走的,而是自己跟人跑了的?這怎麼可能呢?
卻見唐修一臉忍笑的表情,繼續道:「那年上元節,我們一家子皆去了朱雀大街看燈,阿俊因貪玩便跟家人走散了,跑進了一條偏巷裡。便是在那巷子裡,他聽見有人跟另一個小孩說他那裡有糖吃,阿俊就纏上去跟人要糖,人家不給他就發脾氣把帽子扔在了地上,還一直跟著那人不肯走。那人最後沒辦法,只得將他一併帶上了。」
「噗哧」一聲,傅珺忍不住笑了出來。
真是沒想到啊,唐俊七歲的時候竟是個熊孩子。難怪一聽傅珺的問題就氣成那樣,大約這是他此生的黑歷史了吧,熊孩子的黑歷史可不是那麼好翻的。
傅珺越想越覺得好笑,掩了唇直笑得眉眼皆彎。
唐修此時倒是不笑了,而是一臉的淡定。只是在傅珺看來,這位修表哥的淡定表情怎麼看都有種「天哪終於把這事說出來了真是太爽了」的感覺。這也讓他一向溫和知禮的形象有點坍塌了起來。
待傅珺笑夠了,唐修方才溫聲道:「是故,四表妹不必心有罣礙,阿俊過兩日便無事了。我這個做哥哥的可以擔保。」
傅珺便斂衽道:「多謝修表哥解惑。」
唐修溫和地道:「不妨事。四表妹但放寬心便是。」
傅珺點了點頭,心中的不安早隨著唐修的解釋而消弭於無形。心情也立刻放鬆了下來,二人便一同進了垂花門,往「醉扶歸」而去。
此時在「醉扶歸」中,王襄正與曹同知說著話,說的卻是姑蘇府中的一樁案子。
這案子本身並不出奇,然而動靜卻鬧得不小,在市井之中流傳頗廣。
這案子說的是有一戶姓陳的肉鋪掌櫃之子陳水寬,聘了李子巷箍桶匠李雙喜長女李念兒為妻,兩戶人家門當戶對,原是一樁好事。誰料洞房次日驗元帕時,陳水寬卻發現那李念兒已非完璧之身。
那陳掌櫃最是個好面子的,如何忍得下這口氣,當下便將事情鬧了出來,一大清早便帶著人去了李家,直叫著要退婚並索回聘禮。
那李雙喜自是不幹。自家女兒好端端地嫁過去,一夜過後便成了破鞋還要退婚,這換誰也不會同意的。李雙喜堅稱自家女兒冤枉,不允退婚更不會退聘禮。
那李家在李子巷裡熟人多,此時那些鄉鄰們自是皆出來幫李雙喜說話,只道李念兒可憐。
原來這李念兒的親生父親在她六歲時便病逝了,一年後,她的母親便帶著三個女兒改嫁給了現在的這個丈夫——李雙喜。
誰想李念兒的母親也是個福薄的,幾年前也因病故去了,這家裡便只李雙喜一人含辛茹苦地拉扯三個女兒,也沒再續娶。人皆道他是個好心人。
因此,那李子巷的鄉鄰便都偏幫著李雙喜說話,只說陳家欺負老實人,倒讓陳掌櫃討了個沒趣。陳掌櫃回家之後越想越氣,沒的叫自家寶貝兒子一來就戴個綠帽子。於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便一紙狀書告上了公堂,訴李家騙婚,又將那李念兒趕出了家門。
那李念兒孤身一人,既沒臉回李子巷,婆家又不見容,她便生了尋死的念頭,哭哭啼啼地往澹臺湖投了水。
巧的是,那一日曹同知的老母胡氏正好從湖邊路過,便叫人救了李念兒下來,又問她姓甚名誰,為何輕生。
這李念兒除報了自己的姓名之外,旁的一概未說,只垂淚不已。胡氏見她孤零零的十分可憐,便收留了她在府中。
其後不久,這案子恰落在曹同知手上,看到了狀書上李念兒的名字,曹同知才知道自家老母救的便是此案的事主之一。
升堂那日,兩戶人家各執一詞,都說自己冤枉。陳掌櫃便呈上了元帕為證,李雙喜則抹著眼淚說陳家因見自己家窮想要退婚。又怕自家不允。這才想出了這個辦法。
只可憐李念兒一個小姑娘,被拉上公堂拋頭露面不算,還被問及許多難以啟齒的問題,當堂便昏了過去。
這件事經此一鬧。便在市井裡傳開了。各種說法都有。有說李家不厚道的。也有說陳家使陰招的。
因那李念兒是在洞房之後方被陳家人指為不貞的,雖陳家呈上了元帕,但也不能說這元帕便真實無誤。如何證明李念兒是婚前失的貞還是婚後失的貞,此卻為難事。便找了穩婆來,得出的結論也是各執一詞。
其實,要解此案並不難,關鍵之處便在於李念兒的供詞。可是,這李念兒不管你問什麼她都不開口,問急了她便哭。曹同知憐她年幼,不願對她動刑,案子便此僵住了。
此刻,曹同知與王襄說起本案,一面說一面便長吁短嘆的,很是一籌莫展。
而曹同知不知道的是,在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後,他的母親胡氏其實是十分後悔的。
胡氏萬沒想到,她出於好心救了李念兒,這李念兒卻是個名聲不潔之人。胡氏有心將李念兒趕出去,卻又怕落個「不慈不憫」的指摘;可若是將李念兒留下來,這塊燙手山芋卻也不好處置。
眼見著胡氏這幾日為著李念兒的事情愁眉不展、整日憂心,身為長房長女的曹敷便想著,要為祖母分一分憂。
曹敷自出生後便一直很受寵,一則她人頗聰明,為人處事圓滑知禮,二則她嘴甜人乖、又生得一副討喜的面相,因此很得胡氏看重。
見祖母如此心憂,曹敷便自覺有必要將此事解決掉,以解祖母心頭之患。她想著,將李念兒悄悄送回李家不啻為一個好辦法,只是該幾時送、如何送,卻是需要細細思量的。
就在她為此苦思冥想之時,可巧便得了個信兒,知道先師誕日那天要跟著父親出門與傅四姑娘見面。曹敷便覺得這是個極好的機會。
一來有知府車駕隨行,又有高門貴女傅四姑娘作陪,可以最大程度地減輕她與個聲名不潔的女子同出同入的尷尬。就算最後被人指摘,還有侯府嫡女傅四在前頭擋著呢,人們自是不會注意到她一個小小同知之女了。
二來這李念兒原就舉止不妥,一臉的小家子氣,若能被傅四姑娘見棄,則其後將之丟在路上便也有了說辭,到時候就是曹同知也不會認為她是故意丟棄李念兒的。再加上李念兒已經自己回到家中,曹同知自是不會怪罪曹敷了。
因此,曹敷便對曹同知說因實在可憐李念兒,便想要帶她出門散散心,再讓她與家人見一面。又說在家人的開解之下,也許李念兒會說實話,這樣於案情也有益等等,理由給得相當之美好。
曹同知見女兒如此懂事乖巧,心下自是歡喜,便也應允了,還派人去通知了李家人,又約了見面的地點。
那曹敷得了父親的允可,今日出門時便光明正大地將李念兒帶了出來,不僅帶著她上了傅珺的馬車,還特意將話說得遮遮掩掩的,為的便是引起傅珺的不滿,好為其之後的舉動砌詞。
自眾人來到茶樓之後,曹敷除了關注唐修之外,亦在苦思如何能不著痕跡地將李念兒丟下。
可巧的是,傅珺因王宓一事獨自離開,曹敷實在是樂見其成的。這樣她就更有理由置李念兒於不顧了,屆時只消說事出突然,她只能跟著任氏先回了府,傅珺的馬車接或不接李念兒,便皆與曹敷無關了。
所以,傅珺從茶樓走後不久,曹敷便直接跟著任氏的馬車去了知府府邸,到王宓那裡喫茶說話去了,卻是完全將李念兒丟在了腦後。
自然,這位曹家大姑娘的種種心思,不僅曹同知一無所知,傅珺更是全不知情的。
不過,就算傅珺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也不會放著李念兒不去管。
這樣一個受害者,傅珺是絕對不會棄之不顧的。哪怕插手此事很可能會累及聲名,她也做不到視而不見。
更何況,那些所謂的名聲,以及這個時空所謂的道德規範,傅珺從來就沒真正在乎過。
她已經驚世駭俗過很多次了,多一次少一次又能如何?
李念兒的事傅珺不僅要管,而且還要將真正的罪犯繩之於法,還李念兒一個公道,再予這可憐的姑娘一段全新的人生。
因此,在抵達了賞心樓之後,傅珺便叫人將李念兒先行送回了知府府邸。雖明知這般先斬後奏固為不妥,可傅珺卻是顧不得了。
她不希望當著李念兒的面說起她的案子,同時也是想要第一時間向王襄直陳此事。
此時,當傅珺與唐修跨進「醉扶歸」那精巧的月亮門時,曹同知與王襄的話也說完了。唐寂一抬眼,卻見只他們兩個人回來了,便肅了容問唐修:「怎麼就只你們兩個回來了?你弟弟他們呢?」
唐修忙上前一步,將在寶帶橋上偶遇任氏一行人之事說了,最後又恭敬地道:「在寶帶橋那裡的茶樓喝過茶後便分了兩路,曹家的兩位公子便陪著姑母她們去澹臺湖觀景去了,四表妹因身子不適,我與二弟便先護著四表妹去了寄放馬車的酒樓,二弟有事先回去了,我便跟著四表妹過來了。」
傅珺一聽此言,不由在心裡給唐修大大地點了個讚。
這位修表哥著實是會說話。本來是鬧得不歡而散的一件事,被他這樣一說,便成了幾位公子自覺擔起責任分作了兩撥,一撥護著任氏等人觀景,一撥便陪著身體不適的表妹回來。真是無一人的不是,更沒得罪任何人。
唐寂聽聞唐俊自己先回去了,眉頭便蹙了起來。
雖然唐修的話說得並無不妥,但以唐寂對自家二兒子的瞭解,自是知道唐俊不知又出了什麼夭蛾子。只是當著這麼些人的面,唐寂也不好再多說什麼,便只咳了一聲道了一句:「知道了。」
至於曹同知,一聽自家三個孩子皆與任氏在一起,他自是更未覺出什麼不妥來,還含笑對唐寂讚道:「令郎果真穩重。」
唐寂忙笑謙道:「過獎了,犬子不過虛長了兩歲年紀。」
王襄的注意力卻是一直在傅珺身上的。此時便關切地問道:「四丫頭,妳怎麼不舒服了?」
傅珺瞥了唐修一眼,卻見這位修表哥端正穩重地坐在椅子上,連眼風都不帶往這裡歪的。
傅珺只得微垂著頭,輕聲道:「回外祖父的話,也沒什麼,就是方才覺著有些頭暈,現下已經好了許多了。」
王襄便撫鬚點了點頭。叮囑涉江等人好生服侍著,便又與唐寂說起話來。
唐寂今日本就是來辭行的。
這幾天他一直在忙錢寶一案,直到今天才算告一段落。而此事又需得盡早上達天聽。故他今天午前就得離開姑蘇。就在唐寂與王襄他們說話之時,外頭的車馬船隻等皆已齊備,只等出發了。
幾個人又說了幾句話,由王襄以茶代酒向唐寂話別,唐寂便帶著唐修匆匆離開了。觀其形色表情,傅珺猜測那錢寶一案定是有了結果。只是王襄片言都不肯漏出來,傅珺也只能在心裡猜想一番罷了。
唐寂一走,王襄便也與曹同知分開了。曹同知自回府去。傅珺便與王襄一同坐上了馬車。
一到車上,傅珺便將沈媽媽等人皆遣了出去。
她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可不能讓太多人聽到,事關李念兒今後的人生,傅珺必須謹慎對待。
見外孫女兒煞有介事地將下人都遣了出去,王襄自是知道傅珺這是有話要說,便也未做阻止,只靠坐在錦褥上喝茶。
傅珺在王襄的對面端正坐好,抬頭看了看王襄。
王襄的臉上帶著慈藹的笑容,溫和地問傅珺道:「四丫頭是有話說麼?」
傅珺點了點頭。看著王襄那滿頭花白的頭髮,不知何故,她的心裡忽然泛起一陣不忍。
直陳李念兒一案的真相,會不會給外祖父帶來困擾?讓他憂心?
在這個時空待了這麼久,傅珺深知名聲對一個女子的重要性。她涉足此案,若是被外人知曉了,名聲定會受損。她自己當然是不怕的,可是親人說不定便會受牽累,她這樣做真的妥當麼?
傅珺掙扎了幾秒鐘後,便又定下了心神。
無論如何她也必須要救下李念兒。就算不是以警察的身分活在這世上,她也不能迷失自我、忘卻初心,該怎樣便怎樣,她是她自己,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能改變。
傅珺暗自吸了口氣,隨後便微微垂首,低聲道:「外祖父,請您見諒,孫女兒未經您的允可,便將那跟著曹大姑娘一起來的李念兒接回府裡去了。」
「李念兒?」王襄問道,眉頭旋即便蹙了起來,道:「妳說的是那個住在李子巷的李念兒麼?」
傅珺點頭道:「正是她。孫女兒想要救她,還請外祖父應允。」
「救她?」王襄重複地問了一句,隨後便肅起了面容道:「真是胡鬧!妳一個女孩子家,如何救她?妳可知她沾上的是何事?」
傅珺早就料到王襄會如此說,她也不急,依舊細聲道:「孫女自知此舉不妥,但那李念兒若孫女不去救,怕是只有死路一條了,孫女兒於心何忍?更何況,此案真正的罪犯還逍遙法外,就算是為了不讓旁人再受傷害,孫女兒也要救下李念兒,抓住真正的罪犯。」
王襄聽了這話,眸中露出訝然之色,問道:「妳是說,這個案子還真有凶犯不成?」
傅珺點頭道:「是,此案確有凶犯。」
王襄怔了一刻,將李念兒一案的案情又在腦中回想了一遍,便即怫然道:「四丫頭妳莫要胡說。妳可知李念兒的案子是什麼情況麼?不過是訴騙婚案罷了,算不得刑案,又哪來的凶犯可言?」
傅珺堅定地道:「此案明為騙婚,實乃惡案。那李念兒是被人強行毀了清白,這才引得陳家要退婚的。」
「四丫頭!」王襄沉聲喝道,面色已經變得十分難看,肅聲道:「這話妳一個女孩子怎好說出口?莫忘了妳的身分!莫忘了妳是何人!」
傅珺驀地抬起頭來,那宛若青空一般澄澈的雙眸直視著王襄,一字一句地道:「外祖父,您當知曉孫女是怎樣的人。」
王襄愣住了。
此時的傅珺,不再是往昔那個平淡內斂的小姑娘。她的身上流露出了一種氣勢,那樣的堅定、勇決與自信,如同刀鋒一般銳利,帶著一種無法言喻的力量。
那一刻,王襄忽然便想起許多事來。
那個在自己的書房裡侃侃而談,令田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小姑娘;那個在陰暗的牢房中不懼不怕,一點點撬開棋考的嘴的小姑娘;還有那個在落單的情況下鎮定如恆,機警地跟著阿淵回到府邸的小姑娘。
是啊,他的這個外孫女是怎樣的人,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王襄面上的肅然之色,一點一點地化了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說不上是震動還是嘆息的表情。
看著這鬚髮花白、滿面滄桑的老者,在自己的眼前流露出這般的神情,傅珺心中驀地滾過了一股熱流。
她就知道,她的外祖父絕非常人。一代大儒自有名士風骨,更兼那一身開明通達的闊朗大氣,這才是真正的智者。若是別人傅珺不敢說,但若是王襄,傅珺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終會得到他的理解乃至支持的。
於是,傅珺便又加重了語氣,懇切地道:「在外祖父眼中,孫女兒與那普通的深宅女子是一樣的麼?在外祖父心裡,還依舊當孫女兒如其他女子那般看待的麼?」
望著傅珺那雙清亮的眸子,王襄的眼前驀地幻化出另一個女子的形象來。
那個女子亦如此刻的傅珺一般,身上洋溢著自信與堅定的光彩,宛若夏日裡的驕陽,燦爛奪目,令人不敢逼視。當時的她亦曾問過:「在你眼中,我便是那般普通的女子麼?」
此刻,那清越的話語聲穿渡時空而來,在王襄的耳畔久久迴響著。他緩緩闔上雙目,無聲地嘆了口氣。
罷了,這原就是他虧欠了她的,而今便算是他報還於她的骨肉身上吧。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庶庶得正(卷四)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05 |
穿越文 |
$ 221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古代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庶庶得正(卷四)
傅珺在姑蘇居住五年,
替外祖父解決一些案件之後,
意外收到父親傅庚的來信,
她,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可以回京了。
長久以來被忽視的侯門身分突然熱門起來,
輕視小看她的一干姊妹們,
為了一個隨她回京的位置勾心鬥角,各出奇招!
傅珺雖覺得「宅鬥」實在浪費生命,
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她不奮起反抗,就註定要被吃乾抹淨,
只是在這當中,她卻萬萬沒有想到,
自己除了侯門庶房之女的出身外,
竟還有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身世!?
本書特色
微表情能破案,但,能宅鬥嗎?
她是現代獨立自主的警察,一朝穿越,變成小女孩也就罷了,
居然還要應付接連而來的宅鬥考驗!
作者簡介:
姚霽珊,金陵人士,坐望六朝煙水間,汲泉煮字、搗文成衣,文字細膩優美,擅寫景抒情,散文及小說見諸各雜誌報刊,曾出版作品《至媚紅顏》、《一花盛開一世界,一生相思為一人》、《世間女子最相思》、《願你已放下、常駐光陰中》,現為閱文集團簽約寫手,著有長篇小說《庶庶得正》、《折錦春》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傅珺並沒有回府,而是打算先去賞心樓。她想要早些見到王襄,將李念兒的事情徹底解決好。
因此,馬車離了小酒樓之後,便循著原路彎上了寶帶橋的橋口,再沿臥龍大街往回走。
因今日乃是節日,街上車來人往的,頗不易走,馬車也是走走停停,耽擱了好些時候才到達賞心樓。
待馬車停穩之後,傅珺便在沈媽媽等人的尾隨下步下了馬車,正打算由側門進去,忽聽身後傳來一道溫和的聲音道:「前頭的可是四表妹?」
傅珺驀然回首,卻見唐修穿著一襲竹青色長衫,負了兩隻手立在離她不遠的地方,端秀的面上帶著一絲笑意,正含笑看著傅珺。
...
傅珺並沒有回府,而是打算先去賞心樓。她想要早些見到王襄,將李念兒的事情徹底解決好。
因此,馬車離了小酒樓之後,便循著原路彎上了寶帶橋的橋口,再沿臥龍大街往回走。
因今日乃是節日,街上車來人往的,頗不易走,馬車也是走走停停,耽擱了好些時候才到達賞心樓。
待馬車停穩之後,傅珺便在沈媽媽等人的尾隨下步下了馬車,正打算由側門進去,忽聽身後傳來一道溫和的聲音道:「前頭的可是四表妹?」
傅珺驀然回首,卻見唐修穿著一襲竹青色長衫,負了兩隻手立在離她不遠的地方,端秀的面上帶著一絲笑意,正含笑看著傅珺。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姚霽珊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7-10-05 ISBN/ISSN:97898694481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