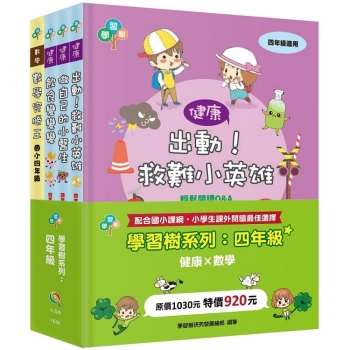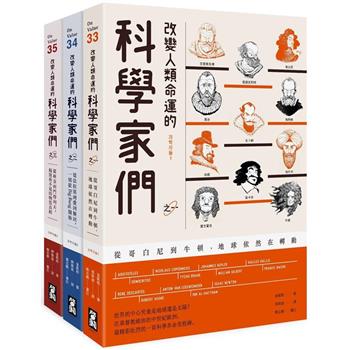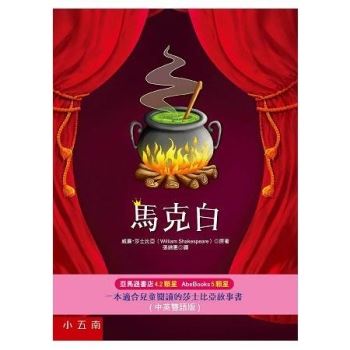不可言喻的心念,是最深沉的黑洞
真實的鬼怪宿於人心之中……
詭異迷離與陰柔耽美交融
妖嬈又悲憫的太宰式怪談
真實的鬼怪宿於人心之中……
詭異迷離與陰柔耽美交融
妖嬈又悲憫的太宰式怪談
《葉櫻與魔笛》收錄二十篇太宰治幽微耽美的短篇,風格有別於他的頹廢「私小說」,充滿迷離、詭譎的氛圍,但字裡行間時不時仍會流露出太宰式的諷刺和幽默。在太宰的心靈深處,妖怪志異一類的文體,保存著日本古典文學的傳統。他早期在《蜃氣樓》發表的短篇作品〈怪談〉,頗為自豪地向讀者宣稱:
「我從小就喜歡怪談。從形形色色的人們口中聽聞各式各樣的怪談。從琳瑯滿目的書籍得知千奇百怪的怪談。說我記得一千則怪談也不誇張,像這樣既神祕,同時又讓人感到嚴肅的話題,除了怪談以外,恐怕在這世上也是絕無僅有。當青色蚊帳外浮現灰色的女子幻影時,或是昏暗的行燈陰影處,一位骨瘦如柴的按摩師弓著背突然咚的一聲坐在那裡時,我藉由這些神祕體驗察覺到神明的存在。」
而這些如夢似幻,似真似假的故事,仍然有著太宰式的細膩與幽寂,其中庶民怪談的靈異奇想,蘊藏著深刻的人生體悟,而其纖細敏銳的視角,更善於描寫女人幽微的心理。他認為:「女性幽靈是日本文學的調味料。是植物性的。」
不論是〈葉櫻與魔笛〉裡相依為命的姊妹,互相愛護和嫉妒的那種暗潮洶湧的心思、<哀蚊>描述著昏暗房間的蚊帳上隱約浮現鬼魂的模樣,那種哀怨神祕的氛圍、<玩具>那個回溯童年記憶的仿若真實的情境、<剪舌麻雀>那種被體制壓迫而無法發聲的弱勢角色、<皮膚與心>自卑卻又對於美醜的價值觀如此纖細敏銳的設計師之妻、<鏗鏗鏘鏘>裡二十六歲的懦弱男子以提問的書信形式討論人生的虛妄性……這些作品深切剖析生而為人的虛無,讀者或許也可以藉由太宰這些怪談的神祕體驗而「察覺到神明的存在」。
「事實往往比小說更為離奇。但是,世上還是會有無人看見的事實存在。
有股衝動想把那樣的事實寫出來,才是身為一個作者存在的價值。」──太宰治
日本文豪太宰治 詭譎幽微的文學世界
【哀蚊】
到秋天還倖存的蚊子稱作哀蚊,那是不需要再點蚊香了,因為實在很可憐。
【葉櫻與魔笛】
在無法言喻的恐怖之下,姊妹倆緊緊地抱在一起,動也不敢動,就在庭院葉櫻林深處傳來不可思議的進行曲。
【懸崖的錯覺】
我談戀愛了。而且是遲來的初戀。沒想到我惡作劇在稿紙上擬好的小說題目,如今竟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出現在我的眼前。
【磷光】
我,在這世間活著。但僅僅只是一小部分的「我」而已。大部分的「我」,肯定是活在一個其他人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玩具】
我安靜地看著死人的臉。人死的時候,皺紋遽然冒出來,還會動,不停地動……
【怪談】
我臉色變得蒼白,心懷恐懼地窺看著那個小水窪。水窪上映著蔚藍的天空,呈現無限深邃的暗藍色……裡頭也許住著某個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