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參加了學生運動以後,被判刑四年,先後關押在秦城監獄和北京市第二監獄。在服刑的期間,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如何反思我們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第二,出獄之後,要做哪些事情?第三,要怎樣把八九民運這一筆中國歷史上的寶貴遺產保存下來?關於第三個問題,作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一個口述歷史,要讓當年發生的事情,用文字保存下來,讓後人知道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3年2月我獲得釋放,一直到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其間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在獄中,我戲稱為“放假”。在這段時間,除了重新聯絡當年的同學,談論如何繼續做一些推進中國民主化的事情以外,我也開始按照原來在獄中的構想,陸續地進行了一些口述歷史的工作。當時,對於如何做口述歷史,我完全沒有專業知識,因此沒有一個完整系統的規劃。基本上就是遇到願意公開談論這個問題的人,就跟他們聊一下,在得到他們同意的前提下,用錄音機錄下來。兩年的時間,前前後後也積累了幾十盤錄音帶。而且,完全沒有進行文字的整理。
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我的房間裡面的東西全部被抄走,包括部分的錄音帶。幸好,還有一部分我是放在父母的房間。當時,抄家的人還想搜查我父母的房間。我母親十分勇敢,她守在門口,說什麼要不讓公安局的人進去。她說,王丹有什麼問題,你們抄他的房間去;我們沒有問題,你們憑什麼搜查我的房間?!就這樣,保護了不少我放在他們房間的資料,也包括我做的一些口述歷史的錄音帶。在我第二次坐牢的期間,我母親和家人一邊要為我的事情向國際社會呼籲,一邊積極地整理我留下來的資料。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我的家人根據錄音帶整理出來的。應當說,這些珍貴的口述史料能夠問世,應當也有我母親和其他家人的功勞。
1998年4月我被流放到美國,開始進入哈佛大學讀書。之後,我父母和家人幾乎每年都來美國跟我團聚,並陸陸續續地把很多我留在北京家裡的文字資料帶了出來,其中就包括這些口述歷史的文字整理稿。從1998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我都沒有碰過這些材料。原因是:當初我開始做口述歷史的時候,曾經想採訪一百個“六四”的親歷者,出版一本《“六四”百人談》,我本來還希望能夠繼續這樣的工作,完成100個人的採訪。但是出國以後,學業和社會事務繁重,無暇進行採訪,100個人的目標顯然是無法達到了。因此我放棄了整理出書的計劃。
但是現在我想,未來,我也會有太多其他的工作。也許現在是時候了,應當把當年那些口述歷史整理出來,編輯成書了。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讓那一段歷史保存下來。這,就是這本小書的緣起。
關於這本《“六四”口述歷史》,還有一些需要說明的地方:
非常感謝當年的主要學生負責人之一王超華,特別為本書撰寫了一篇帶有反思性質的文章,對於外界關於“六四”問題的一些看法進行了釐清和分析,為本書增添了濃厚的理論色彩;1993年我開始採訪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清晰的設想,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不是一場精英運動,而是一場全民民主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普通的參與者、那些學生、市民、機關幹部。他們,才是運動的主體。因此,我採訪的對象,當然包括一些知名的任務,例如許良英夫婦,李佩珊老師等,但更多的,主要是一些不那麼為外界所知的普通的“六四”參與者。我希望未來的歷史,不僅僅記住幾個廣為媒體報導的名字,更應當知道這些普通的參與者。是他們,推動了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我的採訪原則之一,就是只記錄,不做評判;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夠記錄下不同的聲音。在本書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對於當年那場學生運動的不同意見,例如冒先生的很多看法。但是我還是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希望呈現給外界的,是完全的歷史畫面。我相信讀者自己,會從不同意見中作出自己的判斷。此外,除了因為錄音過程中的技術問題導致一些語句不通暢的地方,我做了必要的校正之外,我盡量保持了當時採訪現場的對話原貌,因此有些採訪內容在文字上看起來比較口語化,這也是為了尊重當事人,請讀者體諒。
我卸下教職之後,應當會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樣口述歷史的工作,我希望我還能繼續下去,我希望最終還是能找到100個人,完成我《百人談》的心願。這是一個宏大的工程,也許很難完成,但是一件事情不能因為它困難就放棄。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幾十年來堅持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基本心態嗎?
我要感謝書中那些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同意我把採訪內容公開的八九參與者,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母親的支持,感謝長期以來支援民運工作的很多朋友,感謝美國的“夏星歷史研究基金”的支持。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
最後,謹以此書,作為紀念“六四”28週年的內容,獻給那些在1989年,為了中國的未來而付出青春與生命的代價的人們,也送給那些現在仍然致力於推動中國進步的人們。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六四百人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 253 |
社會人文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中國歷史 |
$ 288 |
中國歷史 |
$ 288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
$ 288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六四百人談
「謹以此書,作為紀念“六四”28週年的內容,獻給那些在1989年,為了中國的未來而付出青春與生命的代價的人們,也送給那些現在仍然致力於推動中國進步的人們。」――王丹
「八九六四」的記憶從當下向歷史移轉,在喧囂之中,我們需要更緊貼土地的真實紀載。本書從「口述歷史」的型態出發,透過採訪紀錄的忠實呈現,帶給讀者更多面向的「八九六四」。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不是一場精英運動,而是一場全民民主運動。它留下了不能被遺忘的傷痕;或許我們未曾參與歷史,但都可以作為一個真相的傳承者。
作者簡介:
王丹
中國民運領袖,六四天安門事件首號政治犯。
近年於台灣清大、政大、東吳與成大任教。
三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並獲美國民主基金會人權獎,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等。
2011年5月,集結台灣、香港與中國海外的一群學術、社運與民主人士共同創辦華人民主書院,擔任講師及董事會主席。
現任《公共知識份子雜誌社》社長
著有《六四獄中回憶錄》、《六四備忘錄》、《王丹Facebook精選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等專書二十餘冊。
TOP
作者序
1989年我參加了學生運動以後,被判刑四年,先後關押在秦城監獄和北京市第二監獄。在服刑的期間,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如何反思我們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第二,出獄之後,要做哪些事情?第三,要怎樣把八九民運這一筆中國歷史上的寶貴遺產保存下來?關於第三個問題,作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一個口述歷史,要讓當年發生的事情,用文字保存下來,讓後人知道那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3年2月我獲得釋放,一直到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其間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在獄中,我戲稱為“放假”。在這段時間...
1993年2月我獲得釋放,一直到1995年5月我第二次被捕,其間有兩年的時間我沒有在獄中,我戲稱為“放假”。在這段時間...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王丹)-《“ 六四” 口述歷史》
歷史的重力-紀念“ 八九六四” 二十八週年(王超華)
與原北大青年教師陳育國的對談
冒舒湮先生口述
某青年教師的回憶
對機關幹部朱紅的採訪
八九參與者的回憶
韓燕明
孔險峰
劉文
知識份子的回憶
李佩珊
許良英
王來棣
某工程師的回憶
同三位北大在校學生的座談記錄稿
當事人的歷史見證:馬少方的六四回憶
歷史的重力-紀念“ 八九六四” 二十八週年(王超華)
與原北大青年教師陳育國的對談
冒舒湮先生口述
某青年教師的回憶
對機關幹部朱紅的採訪
八九參與者的回憶
韓燕明
孔險峰
劉文
知識份子的回憶
李佩珊
許良英
王來棣
某工程師的回憶
同三位北大在校學生的座談記錄稿
當事人的歷史見證:馬少方的六四回憶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丹
- 出版社: 渠成文化 出版日期:2017-06-06 ISBN/ISSN:978986946535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開數:25開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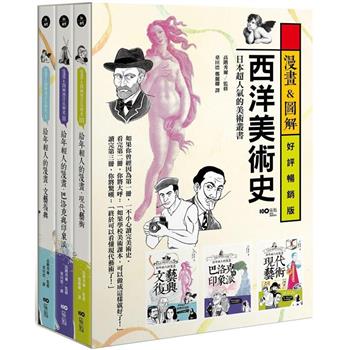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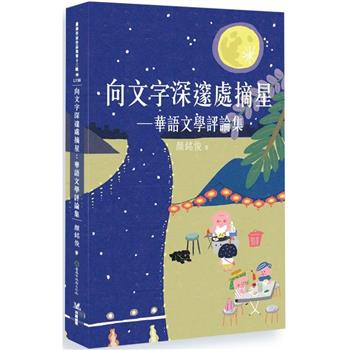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