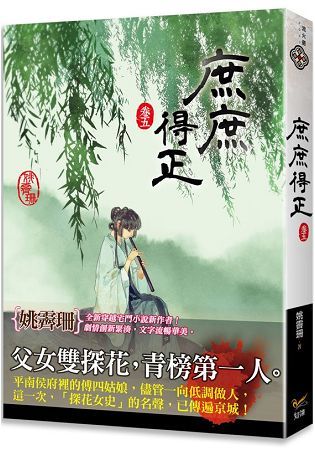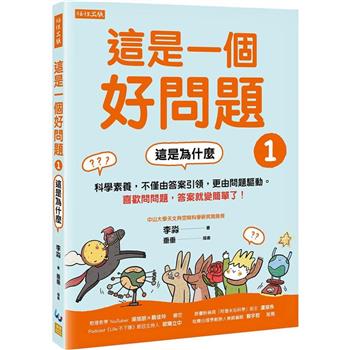第一章
眾人凝目看去,卻見眼前的傅四姑娘戴著帷帽,那天青色的紗幔重重疊疊,直垂至裙腳處,將她的容顏盡數掩於其間,只能隱約瞧見她雪白的膚色。
再看這傅四姑娘的行止,明明也是普通的行禮屈身,可是由她做出來,這蹲身行禮卻又不是蹲身行禮,卻似有著一種舞蹈般的韻律,直若修竹亭荷一般,說不出的端正雅致。
一時間,眾人便皆斂了聲息,場面倒是安靜了下來。
王晉與袁恪皆算是傅珺的長輩,一個是舅父,一個是姨父。此時便由他二人打頭,當先道了「不敢」,袁恪便勉勵了傅珺幾句,王晉亦溫聲叮囑傅珺:「好生考,莫想太多。」
剩餘的幾人與傅珺便算是平輩,有兩個還是陌生人,因此便都是含笑不語。唐俊倒是想說些什麼來著,卻是被唐修以眼神止住了。
見禮完畢,傅珺便自回了小隔間兒,將帷帽取了下來,長長地出了口氣。
總算能安生吃頓飯了。雖然這群美少年可謂品類齊全、秀色可餐,可是傅珺還是覺得他們挺礙眼的。便因有了他們在,傅珺現在連喝口湯都得特別小心,生怕響動大一點便損了她「閨秀女夫子」的名聲。
此外,還有一點也讓傅珺頗為鬱悶。
方才去見禮的時候,也不知那阿淵是怎麼回事,居然選了個角落坐,恰好便在傅珺視線的死角。結果傅珺只瞧見了他半邊肩膀,還是沒瞧見他的臉。
據傅珺所知。本朝有明文規定,身有殘疾、面貌醜陋者皆是不能為官的。而今天這一群人個個都是精英,往後絕對是要走上仕途的。阿淵面有殘疾,與這些人混在一處難道不會自卑麼?
這也是傅珺對阿淵特別關注的原因。
她就是不明白,阿淵這個明顯走野路子的傢伙,為何會跟這群精英學子們混跡一處?
拋開這些事情不談,這上元館酒樓的菜色倒是頗為不錯,有幾味十分合傅珺的口味。
吃過飯後,那大隔間兒裡便熱鬧了起來。儒家學子坐而論道,此乃本朝風習。又有謝玄、袁恪等才俊在座。這番清談便是傅珺亦覺得頗為受益。
此時,便聽那袁恪問道:「傅大人,在下聽聞那白石書院出的題目向來千奇百怪,在下很是好奇,卻不知今日上午的入學試考題為何?」
傅庚微微一頓,方才道:「這個本官卻也是不知。」
唐俊便接口道:「在下記著,兩年前在下參加入學試時,那考題是一塊石頭上放了個雞蛋,實不好答。」
眾人一聽便皆笑了起來,謝玄溫潤的聲音亦響了起來。道:「我與仲明同在一年入學,試題卻不相同。我那年的試題是有人擊鼓奏了一曲。」
他說的仲明乃是唐俊的字。
此時那阿淵的聲音便響了起來,道:「在下斗膽相問,卻不知傅四姑娘今日的試題是什麼?」
他說話的聲音一如往昔,尾音微沉、低柔悅耳。比起謝玄那琴箏般的清越音色來,阿淵的聲音便有若斜陽簫鼓,入耳微涼。
眾人便皆不語,視線卻都集中到了屏風上。
阿淵問出了所有人都好奇的問題,因此大家便都等著傅珺作答。傅庚與謝玄卻是同時向阿淵望了一眼,傅庚面無表情,謝玄的眸中卻是含著幾許責備。
此時,便聞一道清清淡淡的聲音從旁邊的小隔間兒裡傳了過來,不急不緩地道:「上午的試題乃是一張著色寫意,畫中有樹,樹下有影,影中有一叢衰草。」
眾人聞言皆靜了一靜,隨後袁恪便當先道:「這題目倒有意趣。」
王晉亦道:「榮枯相依,明暗為伴。這題目麼,若說易卻也易,說難卻也難。」
唐修便道:「子鶴兄說得極是。這題若要答並不難,但若要答好卻頗為不易了。」
傅庚對方才阿淵的那一問是頗為不滿的,可是,待聽到傅珺今天的題目之後,他的注意力便也轉移到了考試上頭,卻是對傅珺的應答有些擔心起來。
他微闔雙目想了一想,只覺得這題出得刁鑽,極易引人入了歧途。
眾人討論了一小會後,一致覺得這種題目若是女子回答的話,還是以詩為上,最易發揮,而字、畫次之,文則最難。
唐俊終是忍不住心下好奇,便提聲問道:「卻不知傅四姑娘是如何答題的?」
傅珺想了一想,便簡短地道:「小女子寫了一篇文並一幅字。文為《論律法》,字卻是借了前人之語,便是『高樹遏雲,庶草抵履,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十六字。」
她清淡平靜的聲音傳至隔間兒,卻是叫眾人皆安靜了下來。
所有人都不曾想到,這位傅四姑娘居然寫了這樣一篇文並一幅字。
然而再一細想,卻又覺得,傅珺這題破得極巧妙,角度亦是迥異於常人,倒是走出了一條新路來。
那袁恪便問道:「那樹與草之語倒是與題目相合。只那畫中的明暗之意,卻又是從何處論起?」
他這問題問罷,那小隔間兒便又靜了一會,旋即那清清淡淡的聲音便又響了起來,語聲清晰地道:「小女子以為,人性之中,善惡共存。善如高樹承陽,明亮燦爛;惡便於樹下陰暗,如影隨形。人有惡念不可免,但卻不可有惡行。律法之意義,便在於約束惡行,劃定底線,凡有越線者則懲。那畫中明暗涇渭分明,一如善惡絕不相融。善不抵惡,有惡必懲。小女子文中大意,便是如此。」
聽罷此言,傅庚微蹙的雙眉驀地便是一鬆,唇角早已勾了起來,眼中的讚許之意更是毫不掩飾。
這答卷答得極好。且不論這論點好壞,只看這關於人性及善惡的一番分析,便可知為文者絕非人云亦云之輩,而是充滿思辨意味。這與本朝坐而論道的風習十分吻合。
那謝玄此時便即問道:「難道傅四姑娘信奉法家之言麼?」
傅珺答道:「法家所言並非盡善。便如其言人之生而為惡之語,小女子便不敢苟同。小女子以為,人之初,既非善、亦非惡,而是如白紙一張,其所看、所學、所歷,便如紙上作畫。有向善之心,那畫上便光明多些,陰暗少些;而若一心思惡則反之。小女子以為,人之善惡全在一念之間。這世間絕大多數人,亦是善惡並存的。故需以律法約束,再以向善之說加以教化。」
謝玄聞言微微點頭,凝思不語。一旁的孟淵眸中卻是閃過一抹光亮來。
此時,便聽傅庚朗笑一聲,客氣地道:「小女本是一家之言,諸君皆為一時才俊,萬勿見笑。」
王晉便正色道:「傅大人此言卻是偏了。我看傅四姑娘卻是發前人之所未想,思路新奇、論述清晰,卻是頗有可借鑒之處。」
謝玄那琴箏般的悅耳聲音亦隨後響了起來,道:「在下雖未敢盡數認同傅四姑娘所言,然其所言極盡思辨之意,讓在下茅塞頓開。傅四姑娘以仁禮存心,又才智出眾,實叫人欽佩。」
傅庚此時真是極為歡喜。
傅珺的那篇文只聽一聽便可知極好,除非那判卷的夫子眼睛瞎了,否則這分兒絕低不了。而謝玄與王晉的讚揚之語,更是讓傅庚心懷大暢。
傅珺也不知道自己這答卷是否算得上好。不過聽傅庚那話裡的語氣,倒是挺高興的。
只要自家老爹高興就好。傅珺想,以傅庚這探花郎的水平,他若是說好,那自己今天的這個答卷就應該不算差。
此時那隔間兒裡又是一陣低低的討論之聲,卻是就傅珺方纔的論述又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傅珺聽了一會便覺得有些倦意。
她下午還得考一場呢,且還是面試。她若是不養足了精神,下午又如何給面試官一個好印象呢。
如此想罷,傅珺便請許娘子替她向傅庚告了罪。便自去了傅庚替她備好的一間雅間兒小憩不提。
卻說那傅庚那裡,傅珺的離開並未讓這群少年才俊們談興稍減。傅珺提出的那套「人之初如白紙」以及後期成長「如紙上作畫」的言論,讓這群學子們耳目一新。其中既有贊同的,亦有反對的,雙方還小小地辯論了一番,皆是引經據典、文采出眾。
傅庚也不多言,只叫一旁的行舟備下紙筆,將在座眾人所言盡皆記述了下來,自成了一文。
然而,令傅庚不曾想到的是,這篇文不知怎麼便流傳了開來。後世史學家更是將這篇《上元館秋論律法記》與其他名篇美文集結成冊,成書《後漢藝文志略》,成為歷史文學寶庫中的典籍,千古傳誦。
這一場清談加辯論會持續了半個時辰左右,那王晉卻是擔心傅珺下午的面試,怕眾人在此誤了傅庚陪考一事,便提議眾人換至「姑蘇會館」繼續討論。
眾人欣然應允,便一一向傅庚作辭。
步出上元館酒樓時,謝玄終是忍不住,趁著無人在意便輕聲地責備孟淵道:「阿淵,你方才莽撞了。」
孟淵那濃墨般的長眉微微一軒,淡聲道:「我自有我的道理。」
謝玄便又語聲溫和地道:「便是你自有道理,也不該這般唐突。那傅四姑娘究是女子。」
孟淵聽了這話,亮若星晨般的眸子裡便生出了幾許思索之色,沉聲道:「微之,我對一事心中存疑了許久。方纔那番舉動,也是為了印證心中所疑罷了。」
謝玄便向他面上瞧了一眼,清清朗朗的眸中仍是蘊著責備,道:「你所疑為何?又與傅四姑娘有何干係?」
孟淵不由看了他一眼,低笑道:「便是你家母親與妹子皆與傅四交好,你這般幫著她卻也有些過了啊。」
謝玄的面上便露出一絲無奈來,搖頭道:「你啊,還是如幼時一般,不想說的便要岔開話題。」
此時他們的馬已經被人牽了過來,孟淵便利索地上了馬,向謝玄道:「我還有事,先走一步。」說罷也不待謝玄答話,便扯著韁繩將馬頭一攏。那馬兒便滴溜溜轉了個方向,隨後便是躂躂躂的馬蹄聲一路脆響,卻是載著孟淵揚長而去。
望著孟淵遠去的身影,謝玄無奈地搖了搖頭,隨後亦上了馬,追著王晉等人而去。
樓下的這一番動靜雖不算大,然那馬蹄得得脆響,卻是頗擾人清夢的。
傅珺本就淺眠,此刻便被這聲音吵醒了。她睜開眼,拿出小金錶來看了看。見指針已經指向了「壹」字,離下午的考試時間卻也不遠了。
涉江她們便上前替傅珺重新收拾了一遍,此時傅庚也回來了,父女兩個便又回到了白石書院的大門前。
下午的面試被安排在白石書院的一幢兩層小樓裡,卻是按序進行的。所有考生都需先在一處叫做群玉堂的敞軒裡坐著,等候學監夫子叫號。
來到群玉堂後,傅珺向四周掃了一眼,發覺上午那個緊張得手都抖了的小姑娘,亦在此處候著。此刻這小姑娘還是緊張,坐在那裡一臉的不安,兩手更似是沒處放似的。
除她之外,坐中還有一個身量中等的女孩子,也比較顯眼。
那女孩子穿著一身竹青色繡纏枝蓮的天淨紗衣裙,髮上簪著一對梅花簪,眼神清亮、神態平靜,只坐在那裡便很與眾不同。
傅珺不由向她多看了兩眼,那女孩子也看了看傅珺,又向她笑了笑。傅珺便回了一笑,二人卻是未曾說話。
考試是嚴禁私語的,旁邊還站著四個學監夫子盯著,因此傅珺便也只向旁看了兩眼,便耐心地等著叫號。
那學生考試的小樓裡時常有音樂聲渺渺傳來,雖聽不真切,卻仍能聽出考生選擇的樂器中有琴、箏,還有個學子奏了胡笳。
傅珺一時間倒有些好奇,那些選了騎射的考生,卻不知又是在何處考的?
時間緩緩流逝,一個時辰之後,群玉堂裡便只剩下了七、八個人,那個青衣女孩子亦在其中。
兩個人便對視一眼,那青衣女孩子便有些無奈地笑了笑,意思約莫是覺得她們號頭靠後,所以等的時間便格外地長,傅珺便回了她一個淺笑。
到得後來,連那青衣女孩子亦被夫子叫了去,整個群玉堂便只剩下了傅珺並另兩個人,旁邊另有兩個學監夫子。
偌大的廳堂之中,只幾人在座,那兩個女孩子或多或少有些不安,坐在椅子上東張西望,神情緊張。
傅珺卻是未覺出任何不妥來,甚至還覺得理所當然。
這種獨坐於某處的感覺,自她來到這大漢朝之後,其實是每天都在體驗著的。
所謂孤獨,便是街頭人潮洶湧,卻無一相識。
於這整個時空而言,傅珺不正是那唯一的一個麼?這現世裡的人與事,在她卻是全然陌生的。哪怕她的人在這裡,可她的心與靈魂,卻永遠不在此處。
「三十八號。」學監夫子的聲音終於響了起來,也將神遊於物外的傅珺拉回了現實。
傅珺站起身來,十分自然地理了理衣襟,便步履從容地跟在學監夫子身後,走進了那座小樓。
從一開始傅珺就覺得,這些夫子將面試地點定在樓上,又安排了敞軒供考生休息,只怕是從頭到尾這些考生的行止便是處在監視之中的。
所謂禮儀,不僅指的是人前那一套,亦包含了在無人處的教養、規矩與儀態。
所以,從進入白石書院的大門起,傅珺全身每個細胞都是處在備戰狀態中的。她每一回提步、每一次轉首,乃至於跟那個青衣女孩的對視及微笑,都是嚴格按照社交場合的那一套來的。
此刻,她款步隨在那學監的夫子身後,姿態輕盈地走進樓中,再在學監夫子的示意之下,以最優雅的動作提起裙襬,拾級而上。那姿態端莊雅致,全無一絲刻板,舉手投足間的那番禮儀宛若自然天成。甫一上樓,幾個面試官的眸中便皆露出了一絲滿意來。
傅珺依著禮儀向面試官見了禮,又十分自然地抬起視線掃了一眼。
在她的前方端坐著四位夫子,兩男兩女,皆穿著統一的白石書院夫子服飾,青衣玄襟、大帶垂紳。男夫子的頭上戴著文生巾,女夫子則皆戴著小冠。
此時,那最左面一個蓄著短鬚的夫子便從桌前拿起兩頁紙來,展示給傅珺看了看,隨後便和聲問道:「這便是妳上午的答卷吧?」
傅珺見狀,心下卻是微有些吃驚的。
這夫子居然就已經看過她的試卷了?這合不合規定啊?難道不應該是統一判卷給分的嗎?
傅珺自是不知,她那篇《論律法》並那十六個字一交上去,便立刻成為了此次入學試的焦點。
在今年參加考試的學子中,傅珺是唯一一個以律法為題進行答卷的考生。更何況這《論律法》一文還是出自女子之手,且這文章居然寫得極妙,觀點新穎,充滿思辨意味。
因此,在下午的面試環節中,夫子們便將傅珺的試卷也帶了過來,便是想以此為題進行提問。一是想看看這位「藍三十八號」的真正水平,再來麼,也未必便沒有二度測試之意。
畢竟,一個女孩子能寫出這麼篇文章來,實在很難叫人相信。萬一這女孩子只是先期做好了準備,背下了數篇文章,再根據試題擇而錄之呢?所以他們才要通過面試進一步加以確證。
傅珺自是不知這其中的意思的。
此刻,見那短鬚夫子拿出了自己的試卷。她微怔之後便即答道:「是,先生,此乃學生的試卷。」
短鬚夫子便問道:「妳這文中所書之字的字意,與妳這幅字裡的字意頗為不同,是何道理?」
傅珺清清淡淡地道:「學生寫下此文之時。因心有所感、思緒奔湧,更兼此文乃一氣呵成,因此字意略有激揚。而待到寫這幅字時,借的卻是前頭的餘勢。此時學生心情已經平靜了下來,自然那字意亦跟著有所變化。」
短鬚夫子沉吟了片刻,便又問道:「那妳以為,律法為何物?」
傅珺聞言靜了一靜,方才語聲平靜地道:「學生以為,律法者,既嚴且酷。法本無情,亦不容情。法理之下唯分善惡,不以高低貴賤論處。以酷厲之法,震懾為惡之人,護佑良善之輩。此乃學生對律法的見解。」
那短鬚夫子聞言不語,旁邊一個面容白淨的女夫子便怫然道:「我儒家只講以善養人,得服天下。妳卻在這裡大言酷刑嚴律,卻是與我儒家教化之本意背道而馳麼?」
傅珺沉靜地道:「學生對儒家學說並無詆毀之意。學生以為,以儒家思想教化,以嚴明律法震懾,相輔相成,互為補遺。人制不足,以法制之。方為治國教民之理。」
那短鬚夫子不由撫鬚笑道:「好一個『人制不足,以法制之』。」
此時,便見另一個面容清瘦的夫子問道:「那依妳之言,這律法卻是治國的根本麼?」
傅珺端然道:「學生確是如此認為。且學生以為,法理大於人情,法制應高於人制。人生於天地間,便應對天地常懷敬畏;同理,人活於塵世之上,亦應有所畏懼,否則這世間秩序全憑一心,無外力約束,豈非太過輕率?」
那清瘦的夫子聞言便微微點頭。
看他的表情,傅珺清楚,他並不是認同自己的觀點,而是表示明白了她的想法與思路而已。
此時,便見旁邊那個始終未曾言聲的女夫子向傅珺含笑溫言道:「六藝之中,妳選哪一個?」
傅珺便向這女夫子看了一眼,卻見她年約三十許,容顏頗為秀麗。傅珺便態度恭謹地答道:「學生選的是琴。」
那秀麗的女夫子便又問道:「師從何人?」
傅珺答道:「清湘居士乃是學生的先生。」
那秀麗女子的眼睛便是一亮,像是想要說些什麼,卻又終是忍住了,只點了點頭道:「奏來。」
傅珺又躬了躬身後,便即向一旁的琴臺邊坐了,略靜了靜神,又將琴弦「仙翁,仙翁」地調試了幾聲,便緩緩抬手,按弦而奏。
傅珺的考試曲目乃是《聶政刺韓王曲》。
此曲乃是上古之曲,取自《琴操》,說的是一個叫聶政的人,因父親被韓王殺死而苦心報仇,潛入山中修練琴技十載,最後混進王宮刺死韓王的故事。
據說,那著名的《廣陵散》便是據此曲演變而來的。
傅珺之所以選擇這個曲子,原因無他,只因此曲為殘曲,篇幅短不說,指法亦較為複雜。
傅珺是個天生的音癡,雖在柳夫子多年教導之下有所改善,但對於那種指法簡單卻講究意境的曲子,傅珺始終掌握得不太好。反倒是那種指法繁複、曲調濃烈的曲子,她還能應付得下來。
且這《聶政刺韓王曲》所知者極少,那柳夫子浸淫琴之一道多年,所學甚富,這才能將此殘篇教予傅珺。傅珺此刻彈來,卻也是有些討巧的意思。
一曲彈罷,傅珺給自己打了個八十分。
剛才與那幾位夫子的一番問答,倒是將她的心氣又激起來了一些,因此她撫琴之時倒也有些飛揚絕烈之意,與此曲應有之意相去不遠。
果然,那幾個夫子聽罷此曲,面上的神情又是微有訝然。
那秀麗的女夫子看來是專門教樂器的,此時依舊是由她發問道:「為何選擇《聶政刺韓王曲》?」
傅珺便道:「學生天賦平平、才能有限,此曲恰能揚長避短,故選此曲。」
那秀麗夫子聽了這話,面上便露出笑容來。一旁那面色白淨的女夫子卻是淡淡一哂,微有譏意地道:「妳方才口口聲聲說的是律法,如今卻偏又選了一首殺人害命之曲,卻是為何?」
傅珺微微一愣。
這個女夫子的問題倒是不大好回答。
雖是心中犯難,但傅珺卻也不曾慌張。她從容地思索了一會,方才恭聲道:「學生方才論及律法之語,乃是學生對於法家學說的一些感悟。至於撫琴一曲,卻是為了將學生所學盡可能地發揮出來。這兩者間並不矛盾。且此曲最初,便是因那韓王濫殺無辜,方導致聶政復仇。設若那韓王守法遵紀、依法行事,不輕易奪人性命,則此悲劇亦可避免。」
那白淨的夫子聞言又是一哂,卻是沒再說話了。
短鬚夫子便道:「好了,妳先下去吧。」
傅珺便又依禮向夫子們拜辭。
那幾個夫子凝神看去,卻見這位「三十八號」學生行止從容,不見半分被人逼問的慌張與頹色,仍是有若修竹亭荷一般端正雅致、風度翩翩,向著幾人施了一禮,這才不急不緩地離開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庶庶得正(卷五)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05 |
古代羅曼史 |
$ 221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古代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庶庶得正(卷五)
由於傅珺將白石書院的免試名額相讓出去,
想要上學,就只能靠自己考了。
傅珺受了長年閨閣禮教的訓練,
加上前世對「法」的理解,
傅珺不只考中了,而且還考出了個前無古人的好成績!
甚至還得了一個「探花女史」的好名聲。
可她身為傅庚的女兒就已經夠打眼了,
這成績一出,更是受到萬眾矚目,
一連串大大小小的嫉恨陷害接踵而來,
她亦只能見招拆招,不叫那些小人逮著機會了。
只是,她卻怎麼也沒有料到,
打小便在她身邊照顧她的許管事許慧,
竟重新回宮了!?
本書特色
微表情能破案,但,能宅鬥嗎?
她是現代獨立自主的警察,一朝穿越,變成小女孩也就罷了,
居然還要應付接連而來的宅鬥考驗!
作者簡介:
姚霽珊,金陵人士,坐望六朝煙水間,汲泉煮字、搗文成衣,文字細膩優美,擅寫景抒情,散文及小說見諸各雜誌報刊,曾出版作品《至媚紅顏》、《一花盛開一世界,一生相思為一人》、《世間女子最相思》、《願你已放下、常駐光陰中》,現為閱文集團簽約寫手,著有長篇小說《庶庶得正》、《折錦春》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眾人凝目看去,卻見眼前的傅四姑娘戴著帷帽,那天青色的紗幔重重疊疊,直垂至裙腳處,將她的容顏盡數掩於其間,只能隱約瞧見她雪白的膚色。
再看這傅四姑娘的行止,明明也是普通的行禮屈身,可是由她做出來,這蹲身行禮卻又不是蹲身行禮,卻似有著一種舞蹈般的韻律,直若修竹亭荷一般,說不出的端正雅致。
一時間,眾人便皆斂了聲息,場面倒是安靜了下來。
王晉與袁恪皆算是傅珺的長輩,一個是舅父,一個是姨父。此時便由他二人打頭,當先道了「不敢」,袁恪便勉勵了傅珺幾句,王晉亦溫聲叮囑傅珺:「好生考,莫想太多。」
剩...
眾人凝目看去,卻見眼前的傅四姑娘戴著帷帽,那天青色的紗幔重重疊疊,直垂至裙腳處,將她的容顏盡數掩於其間,只能隱約瞧見她雪白的膚色。
再看這傅四姑娘的行止,明明也是普通的行禮屈身,可是由她做出來,這蹲身行禮卻又不是蹲身行禮,卻似有著一種舞蹈般的韻律,直若修竹亭荷一般,說不出的端正雅致。
一時間,眾人便皆斂了聲息,場面倒是安靜了下來。
王晉與袁恪皆算是傅珺的長輩,一個是舅父,一個是姨父。此時便由他二人打頭,當先道了「不敢」,袁恪便勉勵了傅珺幾句,王晉亦溫聲叮囑傅珺:「好生考,莫想太多。」
剩...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姚霽珊
- 出版社: 知翎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02 ISBN/ISSN:97898694672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