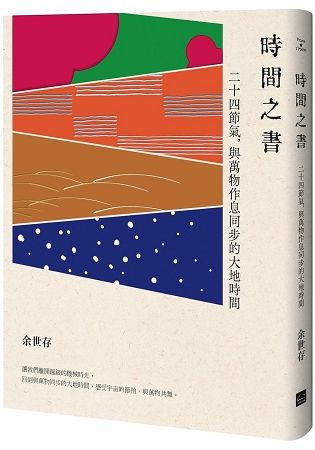自序
行夏之時——關於二十四節氣
借助於技術的加持,人類知識正在大規模地下移。孔子沒注意到技術、文明平臺演進的意義,他的「唯上智下愚不移」看似有理,其實則誤。在權力獨大之前,知識也曾散布於人類每一個個體那裡,由其自信自覺地發明、發現,「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即言此象;後來,權力絕地天通,民眾既不能看天,也無在大地上自由遷徙行走的權利,知識由權威發布,萬眾只有深入學習的義務了。
關於節氣、天文曆法等的知識也是這樣為權力、少數人壟斷。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知道時間,懂得天時、農時、子時、午時及其意義的人並不多。直到民國年間,「教育部中央觀象臺」還要每年制訂曆書。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掛曆、檯曆等市場化力量打破了權力的壟斷。今天,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問時、調時、定時了。
我們的知識史帶來的負面作用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對很多現象、習俗、知識,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有而不知其萬有。節氣,這一傳統中國最廣為人知的生活和文明現象,不僅民眾日用而不知,就是才子學者也少有知道其功能意義。今天的人們在0和1組成的移動互聯網上已經往而難返,收視而無知無識,很少有人深入到時和空組成的座標上認清自己的位置,更少有人去辨析時和空各種切己的意義。
時空並非均勻。一旦時分兩儀四象,如春夏秋冬,我們必然知道自己在春天生發、走出戶外,在冬天宅藏,在秋天收斂,在夏天成長。儘管聖賢對時間有著平等心,在「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能以等身布施,但朝乾夕惕仍有分別。王陽明甚至發現了時間與世界的關聯:「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的世界。」
在傳統社會那樣一個以農立國的時代,時間遠非生長、收藏那樣簡單,更非王公貴族、精英大人、遊手好閒者那樣「優遊卒歲」。先民在勞作中,漸漸明白時間的重要,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傳統農民沒有時間觀念,尤其沒有現代的時間意識,但他們不僅隨著四季的歌喉作息,而且分辨得出一年中七十二種以上的物候遷移。「我看見好的雨落在秧田裡,我就讚美,看見石頭無知無識,我就默默流淚。」這樣的詩不是農民的。農民對自然、鳥獸蟲魚有著天然的一體緣分感,如東風、溫風、涼風、天寒地凍、雷電虹霓;如草木、群島、桃樹、桐樹、桑樹、菊花、苦菜;如鴻雁、燕子、喜鵲、野雞、老虎、豺狼、寒號鳥、布穀鳥、伯勞鳥、反舌鳥、蒼鷹、螢火蟲、蟋蟀、螳螂、蠶、鹿、蟬等等,農民是其中的一員。
農民明白粗放與精細勞動之間的區別,明白農作物有收成多少之別,播種也並非簡單地栽下,而分選種、育種和栽種等步驟。農民中國的意義在今天仍難完全為人理解,中國農民參與生成了對人類農業影響極為深遠的水稻土。一百畝小麥可以承載的人口是多少呢?二十五人左右。一百畝玉米可以承載的人口大概是五十人,一百畝水稻可以承載的人口則是兩百人左右。在農民這個職業上,中國(包括東亞)農民做到了極致。一個英國農學家在十九世紀初寫的調查報告中認為,東方農民對土地的利用達到藝術級,一英畝土地可以養活比在英國多六倍的人口,套種、燃料、食物利用、施肥迴圈、土壤保護,都非常了不起……所有這些,與農民對時間的認知精細有關係。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文明的獨特貢獻。農民借助於節氣,將一年定格到耕種、施肥、灌溉、收割等農作物生長,收藏的循環體系之中,將時間和生產、生活定格到人與天道相印相應乃至合一的狀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生產、生活有時,人生社會有節,人身人性有氣,節氣不僅自成時間座標,也演化成氣節,提醒人生百年,需要有精神,有守有為。孔子像農民那樣觀察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他為此引申:「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可以說,中國源遠流長的精神氣節,源頭正是時間中的節氣。從節氣到氣節,仍是今天人們生存的重要問題:我們是否把握了時間的節氣?我們是否把握了人生的節點?是否在回望來路時無愧於自己守住了天地人生的氣節?如果誠實地面對自己,我們應該承認,我們跟天地自然隔絕了,當代人為社會、技術一類的事物裹挾,對生物世界、天時地利等失去了感覺,幾乎無知於道法自然的本質,從而也失去了先人那樣的精神,更不用說氣節了。
但在傳統社會,人們對天地時空的感受是細膩的。時間從農民那裡轉移,抽象昇華,為聖賢才士深究研思,既是獲得人生社會幸福的源泉,也是獲得意義的泉源。時間有得時、順時、逆時、失時之別,人需要順時、得時,也可以逆時而動,但不能失時。先哲們一旦理解了時間的多維類型,他們對時間的認知不免帶有強烈的感情,讀先哲書,處處可見他們對天人相印的感歎:「豫之時義大矣哉!」「隨之時義大矣哉!」「遁之時義大矣哉!」這就是順時。「革之時大矣哉!」「解之時大矣哉!」「頤之時大矣哉!」這就是得時。人們的時間感出現了紊亂,社會的時間意識發生了混亂,聖賢或帝王們就會改元、改年號,以調時定時,統一思想意識。而在這所有的時間種類裡,跟天地自然合拍的時間最宜於人。今天的城裡人雖然作息無節制規律,但他們到鄉野休整一兩天,其生物時鐘即調回自然時間,重獲時間的節律和精氣神。自然,歷代的詩人學者都在節氣裡吟詩作賦,他們以天地節氣豐富了漢語的表達空間,也以漢語印證了天地節氣的真實不虛和不可思議。
一個太陽週期若分為春夏秋冬四象,一年就有四象時空,如分成八卦八節,一年就有八種時空,我們能夠理解,太極生分得越細,每一時空的功能就越具體,意義就越明確。這也是二十四節氣不僅與農民有關,也與城裡人有關,更與精英大人有關的原因。在二十四維時間裡,每一維時間都對其中的生命和人提出了要求。一個人瞭解太陽到了南半球再北返回來,就知道此時北半球的生命一陽來復,不能任意妄為,才能「出入無疾」;一個人若能深入體悟這一時空的邏輯,就明白天地之心的深長意味。而我們如果瞭解到雨水來臨,就知道農民和生物界不僅「遇雨則吉」,而且都在思患預防。我們瞭解到大暑期間河水、井水渾濁,天熱防暑,需要有人有公益心,此一時空要義不僅在於消夏和獲得降溫納涼防暑一類的物資,更在於提高公共認同,「勞民勸相」。二十四節氣時間,每一時間都是人的行動指南,冬至來臨,君子以見天地之心;雨水來臨,君子以思患預防;大暑來臨,君子以勞民勸相。
我當初寫節氣由一開始的「不明覺厲」到後來逐漸明白時空意義,經歷了對歷史敘事、審美敘事乃至良善敘事的溫習。節氣不僅跟農民、農有關,不僅跟養生有關,也跟我們每個人對生命、自然、人生、宇宙的感受、認知有關。普通人只有瞭解節氣的諸多含意,才能理解天人關係,才能提醒自己在人生百年中的地位。在小寒節氣時需要有經綸意識,在大寒節氣時需要修省自己,在立秋時需要有謀畫意識,在秋分時要理解遁世無悶……古人把五天稱為微,把十五天稱為著,又把五天稱為一候,十五天則是一節氣,見微知著,跟觀候知節一樣,是先民立身處世的生活,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參照。
我意識到,時空的本質一直在那裡,只不過,歷史故事也好,詩人的才思也好,只是從各方面來說明它們,來強化它們。有些時空的本質仍需要我們不斷地溫故知新。在寫作這篇小文時,重讀書稿,發現仍有若干材料沒有加入。如六月芒種節氣,時間要求人們以非禮勿履,我對此的解釋過於直硬,其實如果附會農村人生活,當讓人驚歎其中的巧合。芒種節氣裡農作物成熟了,一些見鄰起意的人,尤其是那些不勞想獲的二流子們,經過麥田時,會低頭假裝倒一下鞋子裡的渣土,實則順手偷幾把麥子。因此,正派人經過別人家的農田,都不會低頭整理鞋子,以免引起誤會,這就是「非禮勿履」了。這樣的現象,今人固然可以理解成傳統農村社會的短缺所致,但是,經過瓜果農田,今人順手牽羊的行為並不少。西哲奧古斯丁少年時就偷過鄰居家的梨,奧古斯丁沒有放過自己,他一生思考的起點即是這一事件,他的結論不是現象層面的非禮勿履,而是深刻地檢討人的罪性。可見,時間給予人們豐富的意義,由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組成的意義仍在不斷地生成之中。
在事物成熟的時間裡展示了人性的原罪,這樣的現象在我們的文化中也可思可考。例如,「氣人有,笑人無」、「見不得別人好」、「圍堵某個經濟起飛的國家」等等。本書裡收錄了中國人「至於八月有凶」、「南征吉」的說法,都是夏秋之際作物成熟引來鄰人鄰村鄰國的覬覦,例如鄭國軍隊到天子眼皮底下搶割周天子糧食的事件。事實上,人與時間的關係確實可以觀察人的性情道理,也可以看出一人、一個族群的狀態。真正有操守氣節的態度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作為「聖之時者」,孔子深刻地理解到時間之於國家、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回答為邦之道時就說過:「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夏時指的是夏朝曆法,也就是陰陽合曆的農曆。夏時的重要,在於它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孔子自己的話是:「吾得夏時而悅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意思是說節氣時間不僅正確,它對人間、人身、人生的規定性也是善意的。有些王朝不以夏時為準,而從十一月、甚至十月為時間起點,「時間開始了」,事實上不僅擾亂了天時、農時,也使人暈頭轉向,失時而失去人生的座標。孔子看到了,正確地調時、定時,能夠使天下欽若昊天,因為時各有憲。每一維度的時間都有其憲法,有其至高無上的規定性。在全球化時代,孔子的「行夏之時」一說,就是採用西曆時間,享用各國產品,保留中國元素,懷抱人類情懷。
遺憾的是,如前所述,關於節氣一類的知識曾經為少數人所壟斷,包括巫師、王室、日者、傳天數者、欽天監、占天象者、各種卜日卜時的先生們等等,他們在下傳時是否無私,他們是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一個問題。知識在一步步下移,但至今文明社會仍未實現藏富於民、分權於眾、生慧於人。就像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闡明的,必須破除主體性思維和科技時空觀,人才能真正成為「時間性」的。海氏為此預告了現代人的異化:「人的存在是時間性的,而時間又因人的感覺而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論是多麼浪漫,然而它又是殘酷的……既然可以通過感覺改變時間軸,那麼欺騙自己、欺騙別人、欺騙世界也就沒什麼不可能的了。」
這也是我極為看重本書的原因。蔡友平先生曾告訴我,對他們釀酒人來說,採集藥草釀酒雖然重要,但時間才是最重要的參數,只有時間到了,酒才能盪氣迴腸。在這方面,節氣堪稱中國文明的智慧,是中國人千百年來實證的「存在與時間」。在知識下移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時代,回到節氣或時間本身,有利於人們反觀自身的氣節或精氣神,有利於自我的生長,有利於人們在時間的長河或時間的幽暗中打撈更多的成果。知識大規模下移也產生了一個問題,是使得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了知識的壓力和誘惑,人們迷失其中,但回到時間或節氣應是在知識海洋中漂移的可靠座標。像曾經的農民一樣,去感受時間和生命的輪轉循環;像詩人那樣,去欣賞「時間的玫瑰」,去收穫「時間即糧食」:「年輕人,你的職責是平整土地,而非焦慮時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我在渺無人跡的山谷,不受污染,聽從一隻鳥的教導,採花釀蜜,作成我的詩歌。美的口糧、精神的祭品,就像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獨生長,凋落。我在內心裡等待日出,像老人的初戀……」
海德格曾引用過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in)的名言:「生命充滿了勞績,但還要詩意地棲居在這塊土地上。」在對時間的感受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過天人相印、自然與人心相合的美好經驗。去感受吧,去參悟吧,去歌哭吧:「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知識的富有、智力的優越在節氣面前無足稱道,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得面對自身。釋迦牟尼有歎:「善哉善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未證得。」
這是信言的語!
二○一六年八月廿三日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