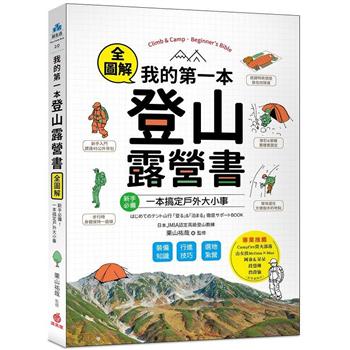我的竹馬是男配,所以主角會是誰?
程微爹不寵娘不愛,姐妹才情容貌個個比她強,而從小親近的止表哥,她心裡仰慕的對象,她選在自己生辰那日向他表白,卻被生生打了臉,從此淪為全城笑柄。
程微不懂,出身外貌都不是她的錯,如果連表哥都疏遠她了,誰又能與她同心結髮一輩子呢?
一場小成年禮的意外讓程微的天地從此變色,偶得的鐲子竟能令她看穿未來,周遭之人的慘況一幕幕在眼前上演。她心中驚懼,不得不向腦海中的聲音妥協,學習符術,誓必改變將來,不讓那些真心待她的親人遭遇大難!
符醫之路的第一步,便是從最基本的「美白符」開始。閉關的半月過去,程微再次出現在眾人面前時,竟讓所有人目瞪口呆……
卷一 誰來弄青梅
卷二 兩小無嫌猜
卷三 問君何所思
卷四 曖曖內含光
卷五 雲開見月明(完)
本書特色
☆《妙偶天成》冬天的柳葉 全新甜寵力作!
☆網路好評推薦不斷!故事構思奇特、引人入勝,不同於一般穿越重生套路,讀者狂推:「這本書和你想的不一樣!」
☆一重又一重的迷霧圍繞在程微身邊,能預見未來的她要如何一邊追尋真愛一邊解開謎團?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我的竹馬是男配-套書<1-5卷>(完)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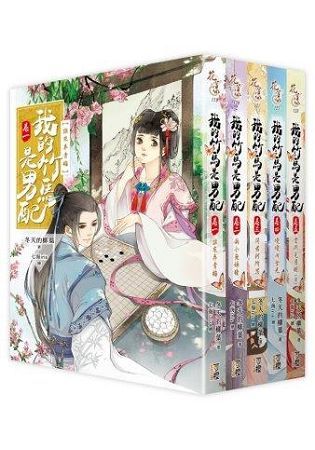 |
我的竹馬是男配-套書<1-5卷>(完) 作者:冬天的柳葉 出版社:可橙文化 出版日期:2018-03-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840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875 |
華文羅曼史 |
$ 875 |
古代小說 |
$ 988 |
言情小說 |
$ 1100 |
中文書 |
$ 1125 |
古代小說 |
$ 11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竹馬是男配-套書<1-5卷>(完)
|